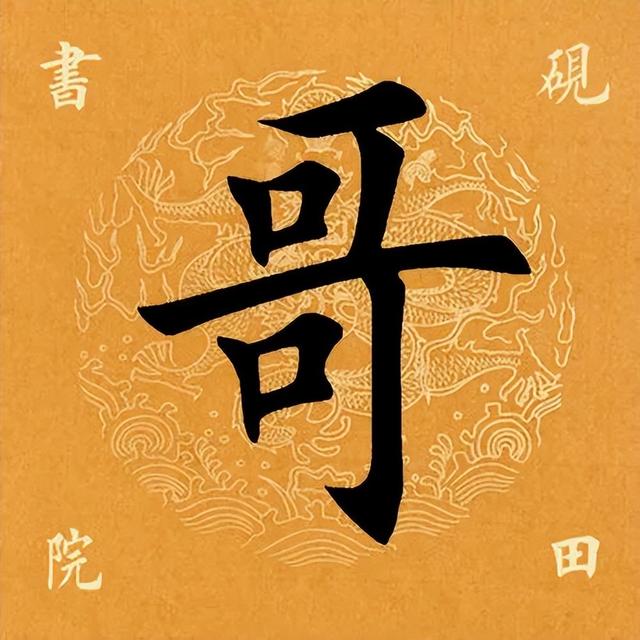李清照。少年时第一次读到这个名字,我的脑际里就莫名地出现了一轮清冷独照的明月。如今一晃,我已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进入“不惑”,但每每读到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诗句时,我的头顶依然冷月高悬,即便是在酷暑熏蒸的炎热夏夜,也会有一股浸透肌肤的凉意袭来。我断没想到,少年偶得的一个意象,竟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使我不敢在冬夜的月光下寻寻觅觅,去轻叩那个冰雕玉琢的女才子的门扉。此刻正值暑热熏熏弥漫,我恰需捕捉那一丝凉意消暑,不妨伴随着知了的欢唱,去接近那个伟大天才的灵魂。

一
这无疑是个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上天似乎也格外垂青和钟爱她,将她投生到一个官宦之家,温柔富贵乡。名门出闺秀,如同寒门出孝子一样顺理成章。我不知道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某一天,当朝进士出身,后升任礼部员外郎的李格非家是否祥云笼罩,有凤来袭;我也无从知道,清照之母身怀六甲时是否梦见星月入怀,但就在那一天,李清照,这个似乎被前世注定要彪炳中国文学史册的女子降生了。就在清照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一阵百灵鸟婉约清脆的叫声,后来这只百灵鸟又幻化成一只啼血杜鹃飞走了……
是的,这样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才女子应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不然上天也忒不珍惜他的钟灵毓秀,良苦用心了。虽说锦衣玉食,纨绔膏粱多会造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浪荡子弟,但对于一个似脂如玉的锦绣女子来说,倘若落草在一个食糠咽菜,衣不蔽体的荒野寒门里,那无疑如珠入泥淖,花落粪坑,可谓天之作孽。所以,以卑之怜香惜玉,爱才弃义之小见,清照投生这样的人家,在琼闺秀阁之中,濡染芝兰书香之气,当不负天意。而事实上李清照之所以后来成为一代词宗,确实和家庭的良好教养如鱼得水一样难能可贵。我们知道清照之父李格非先生,乃进士出身,饱读诗书,博通经文,其才学连苏东坡也颇为赏识,有“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之称谓,且其仕途生涯所任之职多为教育类官职,如,他曾经做过山东郓周教授,太学录、太学正,还做过太学博士,这对李清照的启蒙与深造都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否则,即使女文曲星下凡,在一个女子不能进科入仕,甚至不能入学堂的封建时代,居有比天之才,也不一定能够成就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况且清照之母也工词翰,善文章,颇有文采。当然,历史上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子并非李清照一人,也并非独书香门第方能造就奇男俊女、旷世之才,但就李清照而言,她的先天过人禀赋之遇后天优越环境,无异于天造地设。
李清照少女时期属于北宋晚期,政治上相对比较太平,加之身为官宦之家的女子,生活优裕,无忧无虑。这一时期,也就是她的早期词作,绝非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病态之作,而恰恰就像清纯少女一样健康阳光,天真烂漫,令人心生爱慕和艳羡,如: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
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画面,画面上那个天真活泼、含羞娇宠的少女,如天使一般人见人爱,而那个能够得到少女“倚门回首”的“人”无疑有福了,即使作为一个晚生千年的文学看客,小子我每每读到此处,也禁不住怦然心动,妄加非分之想了,那是怎样的一个娇羞而俏皮的女子哟!
我们通常在一些历史题材戏剧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待字闺中的官宦家小姐往往是或因寂寞而苦闷幽怨的、或为情伤而以泪洗面的,但李清照的少女生活,绝然不同于那些追求“有病三分俏”的戏剧和电影中的少女形象,同样作为待字闺中的官宦家小姐,李清照不仅闺中有史书陪伴,斗草弄诗,而且户外生活也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且看这首《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种时我两忘、无所顾忌、兴尽醉归、甚而不知归路,搅得鸥鹭惊飞的美妙图景,即使在今天身心得到解放,崇尚个性自由的现代女子眼里,恐怕也要啧啧称羡,自愧弗如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女子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待字深闺,专攻女红才对,怎么还可以带着酒划着船尽兴晚游,且天都快黑了还喝得个醉而忘归呢?由此可见,李清照的少女生活是健康的,甚至可以说是自由的、没有被封建礼教所扭曲的,这在当时来说,简直可谓奇迹。也许正是这种没有被扭曲的天性,才成就了词人的个性和她独树一帜,明净自然、不落流俗的词风。
的确,我们很难在李清照的早期作品中,看到家庭,乃至社会对她天性和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其实,李清照少女时期不仅天真烂漫,健康活泼,能够怀咏春风秋雨,抒写青春朝气,还有常人不可想象的思想。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及其平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历来被史家文人津津乐道。唐代诗人元结为此歌功颂德写下了名重一时的《大唐中兴颂》,并请大书法家颜真卿勒碑铭记。比李清照年长,与清照之父李格非同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张文潜对此诗尤为称颂感叹,已然写下一首极具颂扬之能事的《读中兴颂碑》,其中有:“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目开”之句,被时人与《大唐中兴颂》并称为“双绝”,广为传颂。而当此诗传入闺中年仅十六岁的少女李清照的耳朵时,清照对“双绝”颇不以为然,即兴写出《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二首》,其中之一写道: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俸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记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一个弱不禁风,待字闺中的女子,吟花诗草,歌风泣雨倒也罢了,竟然不让须眉,指点江山,品评历史是非功过,指责皇权政治不思安危,非议后宫奢靡无度,直指战乱祸根要害,劝诫世人以史为鉴,鄙夷阿谀之徒歌功颂德……这些思想出自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着实令人不可思议。但当其父李格非和当时的文人骚客们看到李清照的诗后,除了为之惊讶和感叹外,对李清照的“狂放”甚至有些“犯上”的思想并没有产生过多的非议和责难。可见当时的思想环境,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还算比较开明和宽松,这对李清照的成长不能不说是得天独厚了。在有着焚书坑儒悠久传统的古代中国,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在她(或他)的思想初露锋芒时而不遭受打击,这无疑等于打了一个擦遍球,甚至可以说是撞了大运。试想,李清照的才华和思想初露端倪时,便被家庭和社会视为异端横加指责,使梅花初放便惨遭风吹雨打,“零落成泥,碾作尘”,过早的夭折,那么我们今天也许就无缘领略易安风韵了,李清照这位中国杰出女性的名字也就不可能在宇宙苍穹中闪烁了。因此说,李清照的少女时期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即便是在今天,对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文人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

二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李清照的第一首词写于何时,芳龄几岁,但在李清照尚未出阁的二八年华,已经名满京城,尤其在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之间,她的词作更是广为流传,声誉不小。这便不能不被一些同样出自官宦之家的风流才子和公子哥儿所倾慕,并心生爱意。中国婚配文化讲究郎才女貌,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事实上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更容易得到儒雅风流男士的倾心。虽然作为后世之人,我们无缘目睹李清照的芳容,但从她的词作中,我们不难窥见,那一定是一个具有闭月羞花之貌的绝色女子。且看这首《浣溪沙》: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
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她“约”的究竟是何人,就这首词的上半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李清照少女时期的自画像,从那传神的“绣面”、“香腮”和“眼波”的白描中,一个美人坯子不正跃然纸上吗?这样一个才貌出众的绝代佳人,不知引起过多少分流公子的暗恋和相思。史书上没有记载李清照当时的粉丝和爱慕者究竟有多少,单就后来成为李清照之夫的赵明诚追求李清照的煞费苦心,也可见一斑。据元人伊士珍所著《琅嬛记》中记载,赵明诚在其父赵挺之考虑为其择偶时,有一天睡午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去见父亲,要父亲帮他解梦,说:“我在梦中读到一本书,其他内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三句话,叫做:‘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这是什么意思?”。时任当朝吏部侍郎的赵挺之,略加思索后,以拆字法替儿子解道:“言与司合”,是个“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乃“之夫”二字,合起来不就是“词女之夫”嘛!并朗然说道,“我儿需得一个能文擅词的女子为妻”。
这个故事无论是小说家言,还是文人杜撰,我想我们都没必要去作过多的探究,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即赵明诚对李清照是多么的钟爱和痴情。因此,我们也可以猜想到,赵明诚早就对李清照产生爱慕之情了,但面对当时的男女婚姻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明诚不便对父母道明自己的爱情,又唯恐他的心思不被父母所知,只好假托以梦,向父亲暗示出他的隐情是有可能的。如此说来,赵明诚无疑是一个相当聪明和智慧的人,他知道,在当时配称“词女”的非李清照莫属,而父亲对李清照的词名也早有耳闻,故编造出这么一番离奇梦境,让父亲破译,乃意思好像是他的姻缘天注定,以博得父亲的成全。可见赵明诚对能够追求到李清照,并得到家人的同意,着实是挖空了心思,费尽了心机,真可谓别出心裁,绞尽脑汁。
赵明诚爱上李清照,或者说赵明诚与李清照相爱,也许还不仅仅因为李清照的才名,极有可能他们在相爱之前,就互相认识,由相识到相爱的。笔者前文引用的《点绛唇》里“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里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赵明诚,因为若非赵明诚,那么“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是否显得有点过于轻浮了呢?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女子,对陌生人做出如此撩人之姿,显然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是一个倚门卖笑的青楼女子,才会如此挑逗陌生客的。这也难怪,有人因此怀疑这首词非李清照所作,而出自娼妓笔下。我们当然不能小瞧了娼妓,简单地以为娼妓写不出如此生动优美的词,其实,历史上的娼妓,特别是唐宋时期,的确有才高八斗、能文善舞的娼妓,如薛涛、李史史、严蕊者流。但就这首词的风格而言,与李清照善于白描,用朴素清新地语言描绘刻画她对周围事物的感触和表现细腻心理的词风一脉相承,不出其右。所以仅以“倚门回首”四字就判此词为伪作,显然失之草率和鲁莽。我们不妨回头再看看同样被前文引用过的《浣溪沙》下半阙:“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再将这首词里的这个“约”字,和“倚门回首”联系起来看,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李清照和赵明诚偶有相“约”见面,可这天早晨赵明诚过于性急了一些,来的太早了一点,以致人家还在晨练,尚未梳洗换装,赵明诚就到了,为了淑女的“形象”问题,甚至连鞋袜都顾不上穿了,赶紧害羞而走,但又恐赵明诚误解为不理他,故而“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极俏皮地挑逗一下赵明诚。拙作的旨意当然不是在这里勘甄《点绛唇》一词的真伪,我只想从中管窥一下李清照和赵明诚爱情生活的自由度。对此,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爱情是大胆的,尤其在礼教灾难极为深重的宋代,能够在婚前偶尔一会,已属罕事,何况约见于花前月下呢?因此,针对当时的环境,说李赵二人是自由恋爱也不为过,而且这对有情人最终成为眷属,而没有惨遭棒打鸳鸯,真可谓幸运之极。呵呵,好事怎么全降临到李清照的头上了。其实,李清照的幸运还远未至此,她婚后的生活,无论是在东京汴梁时的新婚燕尔时,还是在青州老家筑成的爱巢里,都是相当甜蜜和幸福的。

三
李清照嫁于赵明诚不仅门当户对,而且堪称鸾凤之配。赵明诚同样出于名门官宦之家,其父赵挺之乃当朝吏部侍郎,后任宰相重职。尽管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赵明诚之父赵挺之的政见相左,前者属于保守派维护旧党,后者是新党的追随者倡导变法,但他们对儿女的婚事并没有因政见不同而横加干涉。这当然不能轻率地归功于赵明诚编造的那个“词女之夫”的离奇梦境,而极有可能是两家都相互看中了对方的才学和人品。赵明诚出生在高官贵戚之家,但却并非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他自幼亦喜爱诗文,并对金石碑刻的收藏与鉴赏情有独钟,十七八岁之年,还是一名太学生时,就以金石收藏在上流社会的文人士大夫中间享有一定声誉。这两位金童玉女的结合,可谓金玉良缘,天作之合,谁又能忍心轻易拆散他们呢。
婚后的李清照与赵明诚两情相悦,如胶似漆,志趣相投,比翼双飞。李清照有一首《减字木兰花》的词写的便是她与赵明诚喜结良缘之后的甜蜜和幸福: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比看。
词人借花映人,与鲜花比美斗艳,在情郎面前撒娇争宠,真个是新婚燕尔情浓娇嗔,幸福美满溢于言表,好不令人生羡。
如果说这种蜜罐里的耳鬓厮磨,卿卿我我,还只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化的甜蜜和幸福的话,那么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志趣相投以及在事业上的志同道合,则体现出他们婚姻生活有别于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美满。在《金石录·后序》里,李清照记录了她与赵明诚共同从事书画金石研究的片断,读来饶有情趣:
每获一书,即同共(与赵明诚)勘校,整集题签。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这种互为知己、夫唱妇和的志趣,已不仅仅是一种闺中乐事,而体现出了他们甜蜜幸福生活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因此说这种幸福是上档次,高质量的,非一般意义上的世俗化的甜蜜和幸福,而这种甜蜜和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自古以来,古玩字画无不为文人所好,作为才女,李清照似乎也没有不好的道理。而相对于一般的文人好家而言,赵明诚可谓专业好家,甚至不能简单的以“好”论之,他是把收藏与鉴赏当作事业来做的。因此,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合后,很快就投夫君所好,喜欢上了赵明诚的事业,这正应了“珠联璧合”四字。然而收藏古玩文物,并非有雅兴、有所好就能如愿以偿,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赵明诚出身于高官厚禄之家,经济上无疑有坚实的后盾。尽管如此,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还说他们夫妻二人在文物市场上看到所喜爱的古今名人书画和奇器,经常不惜把衣服典当了以购得,足见他们对文物的收藏非一个“好”字了得。赵明诚与李清照终身所收藏的文物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当然不是仅靠典当衣物所能斩获,但他们夫妻二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到舍衣忘食的程度却也是毋庸置疑的。不难想象,当别的官宦家公子娇娘出入绫络绸缎的大卖场时,赵李夫妻二人却留恋往返于文物市场,将一大堆泛黄的古旧之物源源不断地运回家中,这在当时的市民眼中大概也不失为一道独特怪异的景观吧。
李清照与赵明诚当然不可能天天厮守在一起摆弄古玩,或日日携手淘取文物,赵明诚有自己的仕途前程,所以离别是在所难免的。“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便意味着难舍难分,意味着绵绵不尽的思念,尤其对这对如胶似漆挚爱多情的夫妻来说则更胜一筹。因此当夫君太学毕业,踏上宦游之旅时,李清照的词风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少了一些少女时期的那种无忧无虑和轻快活泼,多了一丝相思带来的淡淡的忧伤和愁绪: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
秋天,大雁南飞之时,最容易引发人的相思和伤感之情。这首词巧借红藕开败,香气渐残的清秋季节,词人独自一人驾着一叶小舟飘荡在湖面上,表达首度与丈夫分别后的相思之情。作为才气超拔而又多情的一代词人,李清照表达相思,也有别于一般的愁妇怨女凭窗叹息,感物伤怀,而是营造出这样一种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浓郁孤独伤感的氛围,来怀想和思念往日与丈夫朝夕相处,出双入对的情景,而有了这样一种氛围,盼望丈夫来信的心情,就显得格外迫切了。从这首词开始,“愁”字便在李清照的作品中频频出现,同时,这一个“愁”字将李清照前后期的词风截然区分开了。词人从最初的表达夫妻离别的相思之愁,到后来的忧国忧民之愁和国破离乱之愁,都无不倾注了一汪浓清。“清月独照几多愁” 。一个愁字,暗含了词人的命运转机,也昭示了李清照后半生的颠沛流离,可以说正是这一个“愁”,消瘦了李清照,也丰满了李清照,甚至可以说成全、成就了李清照,真可谓“一个愁字了得”。
与丈夫分别后,“愁”,便像一颗美人痣一样,点在了李清照两叶弯月柳眉的眉心,以致使今天的我们这些文学看客穿越历史的“薄雾浓云”,依然清晰可见那颗美人痣闪烁出的璀璨光芒。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这首《醉花阴》,千百年来不知“醉”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反正余每读之,都会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如痴似醉。一首小词竟能使人如此“销魂”,甚至如此“失态”,这在我读其他古今中外名著典籍时是很少有过的,尤见其艺术魅力对小可而言已然有了“摇头丸”的性质,也就只能用一个“毒”字来乱喻了。据传,当时宦游他乡的赵明诚收到清照寄来的这首词时品读再三,叹赏不已,且心生妒意,竟闭门谢客,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作词五十首,并将李清照的这首夹杂其中,拿给友人去看。友人赏玩了半天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急不可耐,忙问是哪三句,友人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语出后令赵明诚既惊讶,又自愧弗如,不得不甘拜下风了。诗贵含蓄,词贵雅,一首既含蓄又高雅的词,必为上品,乃至精品,这首《醉花阴》无疑是精品中的精品,她不写思亲写失眠,不写人愁写人瘦。这正如唐司空图所议诗品之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及,若不堪忧。”了
四
然而,“愁”是有轻重的,“愁”是有级别的。如果李清照的一生只一味地写一些儿女情长,闺怨闲愁,那么这样的“愁”就恐怕显得过于轻飘了,也恐怕将难以载入浩繁跌宕的中国文学史册了。因此,对这样一位出众的才女,上苍似乎不会轻易放过她,不会让她总是轻歌曼舞,“学诗漫有惊人句”了,而要对她进行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考验,也似乎只有如此,方能成就“一代词尊”的英名。所以,当李清照的“愁”由夫妻之间的离情别绪,上升到因“物是人非”巨变引起的国恨家愁时,其重量,已非往日结伴或独自出游消愁的“舴艋小舟 ”所能承载的了。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
如果说夫妻间的离别愁绪是薄雾浓云,尚可作一番“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的逍遥游,使之“花自飘零水自流”般的消除,那么国耻家羞之“愁”,就是泰山压顶,这种“愁”的重量岂堪以载?因此当友人提出在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金华双溪尚有一丝残春可泛舟轻游一解愁闷忧苦时,本有此打算的李清照也只能绝望地摇摇头,不去也罢。因为她知道此“愁”,非彼“愁”,是舴艋般的小舟载不动的,也是游山玩水不能驱散消解的,只能用心独自承受。寥寥数语,将词人在遭遇国破山河碎,家徒爱情泯境况下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上苍有时候显得是那样的仁慈,有时候又显得是那样的残酷;命运有时候是那样的温顺,有时候却又是那样的狰狞。建炎三年(公元1127年),当金人挥戈南下,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灰飞烟灭,南宋危在旦夕时,李清照这个一直被上苍护爱有加,被命运垂怜倍至的女子,开始了一生的艰难苦痛和颠沛流离。上苍和命运仿佛不惜以一个朝廷的分崩离析为代价,要来锻造和考验这个曾经在甜蜜和幸福中吟诗斗草的女子了。这莫非正应了那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定律?随着国家的离乱,无论爱情、家庭还是事业,都一损俱损地纷至沓来。先说爱情。本来作别青州的爱巢,南下新京建康与夫君团聚,殊不知昔日如胶似漆的爱情,已成昨日黄花,身为建康知府的赵明诚已移情歌姬,眷养侍妾,“词女之夫”已非知音,“弦断有谁听”?而尤其令李清照蒙羞的是南渡第二年,建康城内发生叛乱,尚未卸任的赵明诚竟绳系城头,结索为梯,不顾妻子百姓,连夜弃城,落荒而逃,后被朝廷撤职查办。李清照对此虽无可稽考证的文字指责,但从她生性仗义和她的一首刚烈不让须眉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五言律诗来推测,丈夫此举对她造成的情感伤害,恐怕是她一生都难以释怀、羞于道及的“耻辱”;次说家庭。感情上出现的巨大裂痕尚未愈合,次年当赵明诚与李清照打算告别江湖,隐居赣水时,途中,那位惯于投降和逃命的高宗赵构,又诏赵明诚官复原职,出任湖州知府。心有不甘的赵明诚冒着酷暑,星夜兼程,奔赴京城建康谢恩,途中不幸染疾,一命呜呼。从此这对一度令人生羡的恩爱伉俪,阴阳两界,这个二十九年夫妻,却连一男半女都不曾有过的家庭彻底破裂。再说事业。赵明诚“殊无分香卖履之意”(《金石录.后序》)般地撒手而去,独留清照长歌当哭,那么他们共同经营的文物事业又将如何呢?据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记载,赵明诚去世后,留在青州老家的“十余屋”文物,在青州沦陷时,化为灰烬;南渡时运往建康的十五车文物,在无计可施时,托赵明诚的两位故吏运往洪州任兵部侍郎的赵明诚妹夫处,又在金兵攻破洪州时不幸失散;“岿然独存”在自己身边把玩的部分珍品,为了一起无中生有的“玉壶事件”(谣传赵明诚将一把玉壶赠于金人),不惜千辛万苦、车船劳顿,走扬州,转杭州,停江宁,复临安,下明州,到温州,进越州……一路追随逃命皇帝,欲交付朝廷,来洗刷所谓的“颁金之语”的妄言,证明赵明诚和自己的清白,但皇帝连社稷都保不住了,岂顾眷你区区文物和屑小名誉,结果十有五六落入他人之手;而在越州,她随身携带的五大箱文物竟被贼人破墙盗走。夫妻二人大半辈子(对赵明诚来说其实是一辈子)舍衣忘食收藏的文物就这样一错再错,一而再,再而三的流失殆尽,与原有文物相比,最终留存身边的不过“一二残零”尔……
一代才女李清照就这样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处境下,雪上加霜,落得个物是人非,人死财散,辗转流徙,流离失所的境地。由此可见这“愁”又怎么可能用“舴艋小舟”来承载呢?那么形单影只,身心憔悴的李清照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呢?
悲夫上苍!难矣命运!
在无路可走贫病交加的情况下,生性刚烈的李清照,不顾封建礼教,不顾流言蜚语,第一次将心撕裂,改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这个道貌岸然的张汝舟,原本是个小人,他不光以娶李清照为妻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还觊觎着她所剩无几的文物。如今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从字号上就可觑视出这“女人之贼船”的张汝舟,一开始,尚对李清照彬彬有礼,一幅君子相,但很快,小人之心便原形毕现。在他企图独占李清照身边尚存的“爱惜如护头目”的文物被识破时,竟不顾脸皮,恼羞成怒,对李清照拳脚相加,大打出手。视独立人格为生命的李清照,面对这个“驵侩”,痛心疾首,不得不再一次将心撕裂,在再婚不到三个月时,断然提出与张汝舟离婚,来摆脱“贼船”。但在当时,离婚谈何容易。为达此目的,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鱼死网破的不归路——她要告发张汝舟科举考试中靠作弊获取功名的欺君之罪(张汝舟在骗娶李清照后,曾得意忘形地将其“妄增举数入官”的事抖搂出来)。说“鱼死网破”是因为按照大宋律法,妻子状告丈夫,不论青红皂白、对错输赢,都要无一例外地坐牢两年。也许牢狱之灾和皮肉之苦比之精神上的摧残更让她好受一些。此事的结果是,张汝舟获罪,被发配柳州,李清照离婚成功了,却也怅然入狱。当那双写诗填词的妙手,屈辱而又无奈地伸向无情的枷锁时,无不令人感到悲怆和心寒。好在李清照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她的冤情即刻引起世人的关注,并在朝中友人的倾力相帮下,坐牢九天后被获释。虽说人身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心灵上的枷锁,却不是那么容易卸去的;况且在封建宋代,再婚是不守妇道,离婚是背信弃义,告夫更是大逆不道的,而这些陈词滥调、清规戒律一旦到了那些同样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伪君子的毒舌和刀笔下,就更成了荼毒心灵,杀人不见血的利刃,什么“晚节流荡无依”、“传者无不笑之”云云,不一而论。可想而知李清照背负的精神压力和人格歧视是多么的惨重。难道说这又是上苍和命运所设的一局,还要对这个终将载入史册,彪炳春秋的奇女子进行锻造吗?呵,如此摧残一个弱女子,即便“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是不是也忒过了点呢?
嗨,其实我们大不必发牢骚,责怪上苍和命运,抱怨李清照的不幸了。今天当我们能够领略易安风韵,读到清照那些饱含忧郁之美,又脍炙人口的绝词妙句时,难道不觉得李清照所饱受的这些磨难都是值得的吗?如今,多少帝王将相被历史的尘埃湮没,而李清照的名字依然像我们头顶的那轮万年独照的明月,闪耀在宇宙苍穹,这不正是她的大幸吗?既如此,那么还是让我们借着这轮月光,穿越历史的云烟,再向这位冷女神靠近一点,去窥探和体验一下她晚年的孤独和忧伤吧。
五
国破家亡的现实处境和凄惨悲哀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的晚年陷入极度的痛苦和忧伤之中。这个失去丈夫,没有儿女,又因再嫁婚变遭人诟病的老人,就像一支寂然的残烛,在无边的黑夜里,发出一缕惆怅幽冥的清光,觑之令人颤栗,近之令人心酸。今天,除了借助她的词作,我们没有谁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她内心深处的悲凉和郁积心头的种种凄情:悼亡、怀乡、亿旧、伤春、悲秋……欲说还休的情感宿怨和难以言尽的忧思愁虑如同凄风苦雨一般,交织而来,又趋之不散。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
天与秋光,转转情伤,探金英知近重阳。薄衣初试,绿蚁新尝,渐一番风,一番雨,一番凉。 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砧声捣,蛩声细,漏声长。(《行香子》)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
这些读之令人心碎的词作,倘不经历人间的凄风历雨,饱尝世道的辛酸苦辣,领略生命的无常无奈,是怎么可能吟哦得出来的呢?常言道“人生最叹老来悲”, 悲之由因人而异,各有不同,难以历数,但共通的老来悲、也最最令人感叹的老来悲,恐怕要数老来之孤独了。一个无人陪伴,守着一盏青灯,渡过漫漫长夜的老人,想一想,都让人心寒和绝望。走进人生暮年的李清照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但所幸的是,李清照除了那盏青灯,还有一支如椽巨笔陪伴着她,使她能够在漫漫长夜中将她那超越时空的孤独心境,依然不失婉约地描画在历史的天幕上,供后人去仰望。
我们说李清照的孤独是超越时空的,是因为这种孤独在历代文人骚客的笔下是无人堪比的,也是不容世俗侵犯的,纵使“酒朋诗侣”出于同情怜悯,“香车宝马”来召唤,试图打破这种孤独,也是被谢绝的。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永遇乐》)
好一个“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想象一下这凄楚难堪的画面,我们不禁要问李清照,这又是何苦呢?孤独像毒蛇一样噬咬着她,而她又如护独子一般地守护着孤独,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矛盾的心态呢?难道仅仅因为“如今憔悴”,人老珠黄,怕见人了吗?不,她怕的恰恰是遭人怜悯和同情,她怕的是自己的孤苦伶仃破坏了他人的天伦之乐。由此,我们不难窥视出李清照那柔肠千缕处刚毅和自尊的一面。然而,又有谁有资格、配同情和怜悯这位伟大的词人呢?
孤独摧残着李清照的晚年,但孤独也使李清照的晚年再度璀璨,一首堪称千古绝唱的《声声慢》,凝结了她晚年的全部孤独和痛楚,同时也将她凝结成了一轮清冷独照的明月,难怪少年时我读到这首词会产生这一意象,莫非广寒宫里从此居住的不再是嫦娥,而是清照了吗?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无须再铺成笔墨,对这首词妄加言说了,其实一个字的注解都显多余,你只要在深秋季节那清冷独照的明月下,默默诵读,就会体会到她的全部意蕴和那“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滋味了。不过,你得添件衣服,小心着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