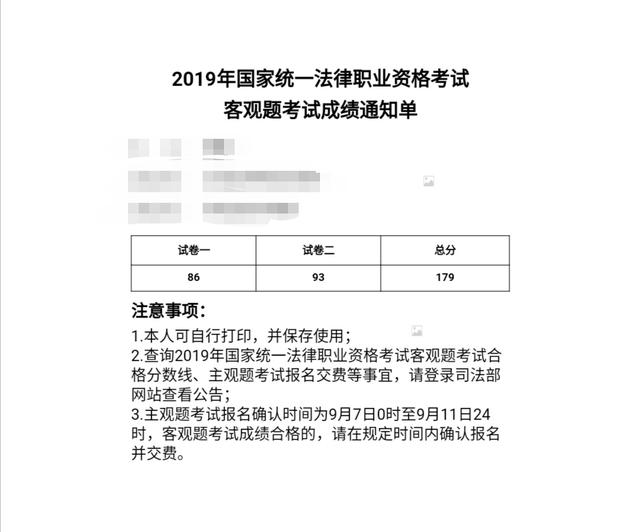这两年养成了个习惯,边运动,边听书,也听完了不少评书和相声,效率提高不少。最近刚听完曾朴的《孽海花》,有人按照原著朗读那种,还听了两遍。
《孽海花》主线讲状元金雯青和名妓傅彩云之间的爱恨纠葛,另外书中也穿插了不少其它人物的奇闻轶事,多是影射晚晴时期的名流。虽说未必都是史实,但对于爱好稗官野史的我来说,着实很对胃口。今天我们就聊聊书中金雯青及其朋友们的历史原型,方便阅读时参照。

先说“海天四友”,书中有交代。
… … 原来雯青和曹以表号公坊的,是十年前患难之交,连着唐卿、珏斋,当时号称“海天四友”。
你道这个名称因何而起?当咸丰末年,庚申之变,和议新成,廷臣合请回銮的时代,要安抚人心,就有举行顺天乡试之议。那时苏、常一带,虽还在太平军掌握,正和大清死力战争,各处缙绅士族,还是流离奔避。然科名是读书人的第二生命,一听见了开考的消息,不管多垒四郊,总想及锋一试。雯青也是其中的一个,其时正避居上海,奉了赵老太太的命,进京赴试。但最为难的,是陆路固然阻梗,轮船尚未通行,只有一种洋行运货的船,名叫甲板船,可以附带载客。雯青不知道费了多少事,才定妥了一只船。上得船来,不想就遇见了唐卿、珏斋、公坊三人。谈起来,既是同乡,又是同志,少年英俊,意气相投,一路上辛苦艰难,互相扶助,自然益发亲密,就在船上订了金兰之契。

洪钧
金雯青 --> 洪钧(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苏州)。
咸丰七年(1857),18岁,考中生员;同治三年(1864),25岁,参加南京乡试中举,那年曾国荃刚克复南京;同治七年(1868),29岁,殿试一甲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据说,清代共有114位状元,平均年龄31.9虚岁,而进士的平均年龄是34虚岁。洪钧科举之路还是很顺的,29周岁这个年纪中状元,算得上年轻了。
同治九年(1870),提督湖北学政,31岁由中央下派到地方锻炼,任湖北省的教育厅厅长。
光绪时年(1884),45岁,老母病故,回家服丧期间结识时年14岁的傅彩云(比自己儿子洪洛还小),即赛金花。

赛金花
光绪十三年(1887),3年丁忧期满,48岁的洪钧擢升为俄德奥荷四国外交大臣,是第一个状元外交官;傅彩云跟随洪钧出使海外。洪钧在海外出使期间的最大成就竟然是编撰了三十卷《元史译文证补》。
光绪十六年(1890),51岁,回国后,晋升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这个目前没有对应的机构,主要是晚清总管外交,外贸,海关,海军,军工,铁路,邮电等的一个超级大部门)。
光绪十八年(1892),53岁,发生帕米尔中俄争界案,洪钧因在俄国重金购买并刊印了一份错误的中俄边界地图,引起外交纠纷,遭到弹劾,抑郁成疾。
光绪十九年(1893年),54岁,病逝于北京。
钱端敏,号唐卿 --> 汪鸣銮(1839~1907年)字柳门,号郋亭,钱塘(今杭州)人,但住在苏州。
同治三年(1864),25岁,以杭州商籍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同治四年(1865),26岁时中进士,比洪钧早一科,暨3年;历官编修、陕甘学政、山东、江西、广东学政,内阁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五城团防大臣、吏部右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禄大夫。
光绪二十年(1894),55岁,任吏部右侍郎;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因反对后党干政,主张巩固帝位,被慈禧太后以“离间两宫”之罪革职,永不叙用。
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自然是帝党骨干,当时的“翁门六子”之首,其他五人是,文廷式、志锐、张謇、沈鹏、徐致靖;我只知道《孽海花》书中的章直蜚指的就是张謇,还没搞清其余四子在书中对应哪个人物。
汪鸣銮娶的是吴大澂的胞妹,而其小女儿汪圆珊嫁了曾朴--也就是《孽海花》的作者。书中诸多京中大佬的逸事,估计都是岳父大人讲给女婿听的。

吴大澂
何太真,号珏斋 --> 吴大澂(cheng)(1835年-1902年),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人(苏州)。
前面说过吴大澂的亲妹妹嫁给了汪鸣銮,其实吴与汪还是姨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有同一个外公--韩崇,算近亲结婚吗?清代估计不讲究这个,相当于薛蟠的亲妹妹薛宝钗嫁给贾宝玉。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率淮军及戈登洋枪队克复苏州,重开乡试,29岁的吴大澂以第六名中举,他的兄弟吴大衡也在同榜;同治七年(1868),33岁时进士,和洪钧同榜;历任陕甘学政,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使,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
光绪十一年(1885),50岁的吴大澂奉旨重勘东部边界,与沙俄据理力争,不仅收回黑顶子地区,还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难得的一次晚清外交胜利。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郑州十堡黄河决口,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礼部尚书李鸿藻先后督修都没有办法;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皇帝命吴大澂署河道总督,最终堵河抗灾成功。
本来凭借东北抗俄,河南治水这两次功绩,足以使吴大澂名垂青史。然而甲午战争中的田庄台一役,却令他丢官罢职,沦为笑谈,就如同他的翰林院前辈同僚张佩纶(书中的庄仑樵兵败马尾海战)的遭遇一样,令人唏嘘书生的“纸上谈兵”。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59岁的吴大澂时任湖南巡抚,“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不久,获允“带勇北上”,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然而到了山海关后,吴大澂虽然畏缩不前,却还大言不惭地对日军发布“劝降书”,最终在田庄台指挥失当,全军覆没。光绪以吴大澂“徒托空言,疏于调度”,将他革职留任;戊戌政变后,慈禧又降旨革职,永不叙用。
曹以表,号公坊 --> 曾之撰(1842—1897),字圣舆、一字铨仲,号君表,江苏常熟人(清代,常熟也归苏州府管)。
曾之撰并不出名,所以网上资料很有限,百度百科介绍“同治庚午科(1870年)顺天副贡,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举人,丙子(1873年)、已丑(1889年)会试堂备,刑部郎中,河南司行走,加二级,晋恩诰授中宪大夫。”
曾之撰的科举道路不顺利,33岁才中举人,前面提的三个人在这个年纪都已经中进士了。当初洪钧,汪鸣銮,吴大澂和曾之撰之所以结识,是因为咸丰末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为了庆祝,在北京重开乡试。当时太平天国占据了苏州和常熟,因此他们都避居在上海。为了参加乡试,他们不约而同地一起乘船穿越火线去京城赶考。四位弱冠之年的翩翩公子,最大的吴大澂25岁,最小的曾之撰采18岁,既是同乡,又是同龄,更是“同志”,意气相投,经过这次冒险之旅,顺理成章的结下深厚友谊。虽然这次乡试他们都没中,(洪、汪、吴三人都是1864年中举,曾更是又等了十五年),四人友谊却依然很牢固,不因为曾的不举而有所嫌边。
其实曾之撰就是《孽海花》作者曾朴之父,后来帮曾朴娶了好友汪鸣銮的女儿。曾朴对公坊着墨不多,只是坦然地描写了公坊和“相公”朱爱云的亲密交往,毫不避讳;后来公坊虽然捐了个刑部郎中(相当于司法部的司长吧),但不适应官场生活,索性辞官回常熟隐居去了。
除了“海天三友”,金雯青还有个同乡挚交,就是陆菶如。

陆润庠
陆仁祥,号菶(beng)如 --> 陆润庠(xiang)(1841-1915),字凤石,号云洒、固叟,江苏元和县人(也是苏州),清代苏州府城(现在的苏州老城区)被分成三县而治(吴县,元和县,长洲县)。
陆润庠是洪钧在苏州城里的同乡小老弟,同治十二年(1873),32岁,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33岁,和洪钧隔了一届,也高中了状元,是苏州第51位,也是最后一位状元郎,和洪钧并称为“红绿”两状元。另外陆润庠的七世祖陆肯堂,是康熙朝的状元。
陆和洪两人还是儿女亲家,陆润庠的长女就是嫁的洪钧独子洪洛,可惜洪洛在洪钧死后不久也病故了。百度百科上说,洪钧的二姨太娶得陆润庠的女儿,想想就不可能。他的故居在苏州下塘街,离悬桥巷洪钧故居才两公里,两处现在都还在,有机会可以一起参观下。
陆润庠为慈禧所赏识,仕途比较顺利,历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官至太保、东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后来还当上溥仪的老师,最后被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端",不过其实没干什么大事,也就在苏州办了两爿纱厂值得一提。
另外,金状元还有两位上司、老师兼好友,也都是苏州府人,分别影射翁同龢和潘祖荫,比较有名,我就只列百度百科上的介绍,不多说了。
潘八瀛 --> “潘祖荫(1830~1890年),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内阁侍读潘曾绶之子,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
龚和甫 --> “翁同龢(1830年~1904年),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洪钧能当上俄德奥荷四国外交大臣,就是靠了两人的举荐。其实两人也就比洪钧大九岁,但是出道早,潘祖荫是1852年中的探花(22岁),而翁同龢是1856年中的状元(26岁)。潘和翁是总角之交,都是名门之后(不是我爷是大学士,就是我爸是尚书),祖籍都是苏州府,但是一起在京城长大,传说两人还都是天阉[嘘]。
这些苏州府的大才子们虽然个个聪明绝半顶,却多被安排在不合适的岗位上。洪钧毫无洋务知识,也无外交经验,就被委了四国大使,在使馆里能做的只有闭门研究元史;吴大澂虽然外交、治水有一套,但军事上是个菜鸟,当了大帅还捧着《孙子兵法》和日本人打仗;翁同龢长期担任户部尚书,不善理财,只知节俭,该省的不省(给慈禧修园子),不该省的乱省(克扣北洋水师拨款)。
你想啊,他们从小钻研四书五经,按现在来说,起码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博导水平,但让这些人出使外国,带兵打仗,或者管理经济,就知道多不靠谱了。《孽海花》表面上讽刺这些官员迂腐无能,实质上也是抨击晚清落后的教育和官僚制度。
借用佛山黄飞鸿的话。“ 所谓勇者无惧,仁者无敌;练武强身,最重要就是要智勇合一。如果不能广开民智,徒得双手双脚,又怎么会国富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