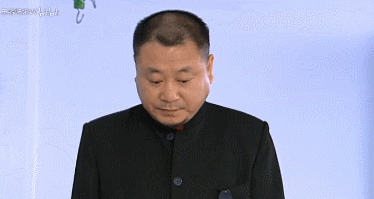根据现有文献来看,萧梁时期歌诗创作中心在以萧氏家族为核心的宫廷,作者群体也呈现出精英化、贵族化的特点。
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例,《乐府诗集》共收梁时歌诗作品五百余首,作家 71 人。其中,可考得曾在本朝出仕的就多达 53 人,此外又有宫廷乐人王金珠、包明月 2 人,官员家眷范静妻、王叔英妻 2 人,以上就占《乐府诗集》所收梁朝全部诗人的 80%以上。

此外,文献中保存歌诗数量最多的是沈约、简文帝萧纲与梁武帝萧衍,可见歌诗的主要创作群体非富即贵的精英化、贵族化特点。
文献保存中所反映出的创作群体构成也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萧梁时期的音乐文学创作往往呈现出华美靡丽、音律严明的风格——只有足够稳定的生活与优渥的条件才能滋养出这样雍容冲淡的审美取向。
主要创作群体阶级的上移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乐府歌诗的性质特点,乐府创作由平民百姓田间地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转而成为贵族、士大夫们的赠答唱和与消闲吟咏。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于 1969 年提出“作者的缺席(absence)”的概念,认为“作家”之所以存在且发挥功能,是因为其成为了一种分类的手段。按照福柯作家观的逻辑,当具体的“作家”之名没有能够起到区别与分类的作用时,“作者”也就是“缺席”的。
如果说曹魏时期乐府的文人化趋向仍保存了乐府歌诗“诗言志”的传统追求的话,那么梁朝的歌诗所反映出的则是一个作者“缺席”的时代。
所谓“作者的缺席”是指创作群体不再以文学作品作为个人性情与志向的表达,读者在作品的阅读过程中既无法从中获取作者的个性特征与身份信息,又无法发挥“作家”署名的区分作用。

在文论上,以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主张为代表:“立身与为文异,立身且需谨慎,为文且须放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将“立身”与“为文”相互分离的做法标志着作家与作品之间存在着一条实与虚的界限。
作品与个人情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而是机动的、不确定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和接受无疑赋予了创作更大的空间,可以看做是对创作自由的一种赋权,为现实中受到的拘束与限制在文字中找到了很好的安置。
首先,由于作者与作品之间距离的扩大,作品中鲜少有作者个人情志的表达与个人信息的透露,取而代之的是对女色、器物的欣赏、描摹以及对前代作品的步趋。

类似的创作内容广泛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当中,审美对象的单一以及写作技法的趋同导致作品的个性化程度锐减,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品甚至到了“如出一手”的地步。
其次,创作自由度地扩大所带来的结果是歌诗作品在风格发展上越来越朝着宫体的方向靠近,格调宕丽华靡。
作者主体从作品中的消失同时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歌诗创作娱乐化的性质。正是因为歌诗作品不再具备功利的目的与政治教化的功能,而专为消闲愉悦所用,所以诗歌原有的严肃性与讽谏怨刺的性质也被这样的创作目的消解殆尽,文学创作领域呈现出一派“兴寄都绝”的景象。
此外,娱乐化的创作性质还体现在作家在拟写人、物时相对抽离的态度。这种创作的描写与所包含的情感并不是源自于作家的“性灵摇荡”,也并不需要调动作家的个人情感,而是为了对其所观照的推向进行描写而进行的遣词造句、为文造情。

从一方面来说,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写作是不调动也不体现个人情感与个性的,另一方面来看,赋题法将作家群体的写作对象限定在固定的乐府古题之中,相同的写作手法加之相同的描写对象,自然便带来了作品之间区分度的下降。
当然,这种娱乐化追求趋向不是梁朝始有的。这种倾向是中古时期文学与文论中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程度有所区别。

尽管作者的主体性不再在作品中直接地表露,但作者及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因素仍以潜在的形式决定了作品的写作内容与风格。
其所描写器物的华贵、情感的雍容都使这一部分创作与传统的乐府民歌相区分,民歌风味至此已大大被冲淡,不得不说这是创作群体转移所带来的直接表现。

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看,梁朝时期乐府创作群体精英化既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这是由文献编纂与流传的特殊性决定的。写作群体的确定取决于文献的呈现,而文献的保存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未必反映历史真实的全貌。
因此,尽管此一时期文献中呈现出的作者群体以贵族、士大夫为主,但这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文献流传中民间文本的缺失,而不能依此百分之百的断定民间已不存在音乐文学的创作行为,此外也不能确证贵族、士大夫的创作在此时已占据更重要的主导地位。
相反的,梁武帝萧衍与沈约等人还积极地学习和模仿吴歌西曲的风格和内容,恰恰是这种模拟的行为体现出了民间音乐文艺的存在及其对此时歌诗创作的影响。

但这些民间歌诗的创作年代大多以晋宋时期的作品为主,极少有能够确切断代至萧梁时期的民间乐府作品。
从客观上来说,这一点是由于曹魏时期后采诗制度的衰微,民间乐府“无由而上闻”。从更深层次的思想层面来看,这实际上是士族阶级对“采诗以观风俗”的观念的否定。
除此之外,与劳动人民相比,贵族、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也决定了这种文献保存情况的必然。
首先,与平民百姓不同,南朝世族文人往往“家家有制,人人有集”,这类人群更具有将个人创作进行记录和编集的意识。而民歌往往是通过口头、以音乐的形式在田间地头传播,因此往往难以留下纸面的记录、指认确切的作者。

为创作留下文本记录或刊刻印行这种行为本身就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一定的物质条件,而这些都是非富达显贵而不能为的、较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自然为平民阶层所无法触及。
此外,诗文的保存有时往往依靠的是总集或全集的收录,而这类文献的编纂往往也以宫廷为中心。相近的生活轨迹与共同的审美偏好更有助于贵族、士大夫彼此之间获得认可,因此也比民间创作拥有着更多被收录和流传的可能。
谢谢观赏,关注我,了解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