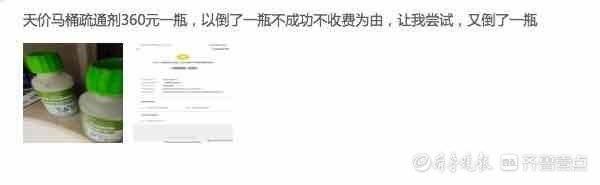十一假期的尾牙,我去看了《缝纫机乐队》,因为听说口碑比《羞羞的铁拳》好一些。
作为大鹏的第二部院线作品,《缝纫机》继承了《煎饼侠》“青春梦想”的风格,却没能继承票房奇迹。
和自己比,煎饼侠最终票房11.59亿,缝纫机票房2.42亿(截至10月8日,上映10天);和别人比,同期沈腾团队的羞羞上映9天已经突破14亿元——不是一个级别。

煎饼侠讲得是一个圆屌丝电影梦的故事,缝纫机讲的则是一个圆乐队梦的故事。
巧的是,这两个梦,我都有,或者有过。很多文艺青年也都有,或者有过。
影史上总有一些借鉴或者巧合,或者抄袭。
我只能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一部叫做《海岛七号》的电影,《缝纫机乐队》也许不会拍成这样。
《海岛七号》是2008年的一部台湾电影,当年在台湾叫座又叫好。不仅登上台湾电影票房史上排行第二名(仅次于《泰坦尼克号》),而且获得了当年金马奖年度杰出电影等六个奖项。
如果把这两部电影概括成一句话,缝纫机和七号完全一样,也讲了一个临时组建的乐队如何大获成功的故事。
细节上的雷同之处也不少:
第一 男女老幼组成的杂牌乐队。七号中的弹月琴的老邮递员茂伯和缝纫机里吉他手老中医杨双树;两个乐队中的键盘手都是未成年的小女孩,七号里的叫大大,缝纫机里的叫希希(希希的饰演者叫曲隽希,生于2008年)。
有趣的是,两部电影里的乐队成员演员都曾与金马奖最佳新人奖发生过关系:茂伯的饰演者林宗仁出生于1947年,凭在七号中的演出获四十五届金马奖最佳新人提名;缝纫机里鼓手炸药的饰演者叫李鸿其,生于1990年,凭《醉·生梦死》获第五十二届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可见,不论你的理想是乐队还是电影,多晚都不晚,多早也不算早。
第二 乐队成员和经纪人之间的恋情。缝纫机里的女团员富二代丁建国(古力娜扎饰)爱上了经纪人程宫(大鹏饰)。七号里则反过来,乐队灵魂阿嘉(范逸臣饰)则爱上了日本女经纪人友子。
第三 不着调的植入广告主。这一点实在像得太奇怪了,两支杂牌乐队都穿过带有LOGO的制服,七号里是乐队成员推销的小米酒品牌马拉桑,缝纫机里则是乐队粉丝孙大力(于谦饰)的“连锁小卖部”品牌邦佳维。
如果说前两点相似是因为戏剧矛盾设置的需要,英雄所见略同,不得不做出的唯一的最佳选择,那么这一点的借鉴则完全没有必要。
两部影片最大的不同,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气质层面的。
七号就像一幅中国水墨画,气定神闲,徐徐道来。虽然“老友子的爱情”那条故事线在有些人看来显得略有些矫情,但其叙事仍然显得非常娴熟,又不留痕迹。比如乐队成员的出场,是通过主角阿嘉返乡后的临时邮递员工作,非常简洁地勾勒出来的。最后演唱会的拍摄也采用了比较纪实的拍摄方法,没有过分通过技术手段强调戏剧性。
反观缝纫机,全片就显得太“满”,像那种小商品市场里随处可见的印刷装饰画。缝纫机里充满了刻意的隆重、说得太清楚的理想和喧哗的幽默。
片中有很多枝蔓占据了观众的注意力,比如片名和乐队名的出处,那个关于缝纫机的故事给人印象不深,既不是核心线索,也没有复沓提及,让人觉得可有可无,中文片名还不如英文片名《City of Rock》贴切。
刻意的隆重,有时会让观众觉得尴尬。比如演唱会的高潮部分,大鹏在台上《不再犹豫》唱得好好的,突然台下变出了千人敲鼓,万人弹吉他……场面实在太失控了。这,也是太满了。

我本来以为魏德圣是科班出身,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在海岛七号后拍出《赛德克巴莱》《KANO》的导演和大鹏一样,开始也是在台湾文艺界里打打短工,然后半路出家的。
两片的时长都是140分钟左右,但魏德圣讲故事的效率似乎更高,所以有时间去从容。
我很喜欢大鹏,因为他曾经和我一样是个屌丝,活生生把梦想过成了现实。他的电影内核是他一天一天过出来的体验,但他电影的形态太过商业和刻意。我担心他将来会后悔自己对那些过出来的体验的挥霍。
海岛七号的故事是“讲”出来的,缝纫机乐队的故事是“喊”出来的。
电影院本来就是个帮你做梦的大床房。屌丝男士大鹏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虽然没有创造票房奇迹,但缝纫机仍值得一看。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