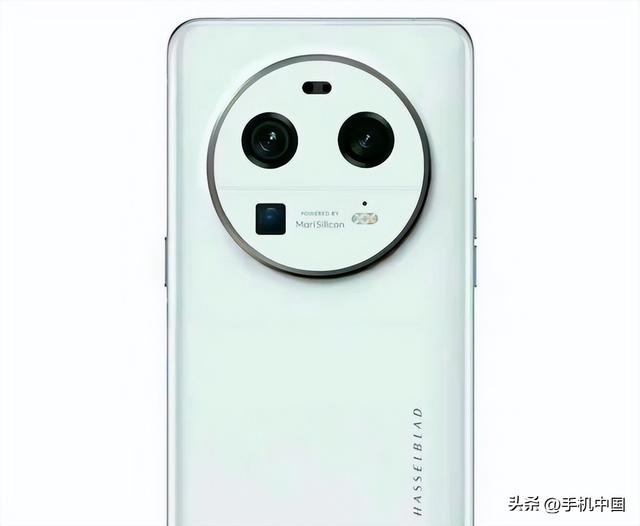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高文瑞
提起牛栏山,京城中无人不知。但是,与牛栏山隔潮白河相望的狐奴山,却鲜有人知。
狐奴山位于木林、北小营两镇交界处,海拔92.8米。顺义并无高山,狐奴山知名度不高,听起来还有些费解,但在古时却比牛栏山出名。西汉初年置狐奴县,属渔阳郡,狐奴县址在今顺义区北小营镇北府村前、狐奴山下。狐奴县遗址在当地俗呼城坡,曾出土有陶井、汉瓦、青铜剑、五铢钱等汉代器物。

顺义出土的大陶仓(又称口粮囤) 摄影:高文瑞
狐奴山与牛栏山隔河相望,令人产生美妙联想。天上银河一边是牛郎挑担子,一边是织女执牛轭。潮白河恰似天上的银河,而狐奴山的历史故事一点不比织女的少。

远望狐奴山
汉时山前稻米香
狐奴山上原有座小石城,还有座寺庙,庙前的松树有几百年树龄,三个人都抱不过来。当地人讲,石城很早就没了,土地庙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拆了。
东汉时期,张堪在狐奴山的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曾担任渔阳郡太守,狐奴县在他管辖之内。张堪是南阳宛县人,《三国演义》中典韦战宛城救过曹操,宛城即今河南南阳。张堪能文能武,他任渔阳太守期间,上万匈奴骑兵来势汹汹,张堪仅率几千人马迎战,大获全胜,自此匈奴多年不敢来犯。
古时狐奴山周边涌出的泉水异乎寻常之多,仿佛压着一池水,愈想护住,溢出愈烈,有明泉、双狮子泉等。四周片片沼泽,芦苇茂密,野鸭飞过,一幅美丽的图画。地下水位之高也传下句老话:大泉眼九十九,小泉眼遍地有,马蹄踩个坑也能出泉眼。
战国时期的邹衍传播耕种技术,在黍谷山产出了粮食,古人称“黍谷先春”。天寒地冻的山地能长出五谷,平原水地是否也能种植稻子?张堪开始实施设想,选种、育种、种植试验,最终成功地在狐奴山下种出了水稻。张堪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家族中得到传承,发明了地动仪的东汉大科学家张衡便是他的孙子。
在张堪的带领和推动下,村民在狐奴山周围开垦出稻田8000余顷。百姓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人民生活殷实富裕,遂流传下千古传颂的歌谣:“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当地人民感谢张堪造福一方,遂建造庙宇以示怀念。张堪祠庙早已不在,遗址在今顺义区前鲁各庄村。前鲁各庄村新建了纪念馆,展示张堪的生平与贡献。
张堪之后,此地还出现一位促进水稻种植的人物。东汉高密侯邓禹第六子邓训率兵驻扎狐奴山,以防匈奴、乌桓进攻。邓训在狐奴山下西南方建起城堡,有人认为这是汉代狐奴县故城。城堡大小与规制也无从知晓,在时间与征战的消蚀中已无踪迹。邓训继续开垦出稻田两千余顷。明嘉靖初年,李贡到此巡视时作诗:“任邓防胡处,屯兵旧有城。县随陵谷改,名逐代朝更。”
张堪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传授新的生产技术,这是北京地区在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农业开发,不但使狐奴地区成为鱼米之乡,还推动了北京地区的农业发展。有老人讲,这里的自然条件好,稻米产量高,种上一年能吃七年。水好地好,产出的稻米俗称“三伸腰”。“伸”即为蒸,刚出锅的稻米香,再蒸也好,第三天热蒸依然香。如今,狐奴山下种出的大米就被称为“三伸腰”大米,而且是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鲁各庄村种出的水稻 摄影:武亦彬
远观狐奴山,周围良田为衬,稻浪滚滚,一片绿色。田垄尽头,现出青色山形,构成了青山绿水的古典图画,格外美丽。此为“狐奴远眺”,被称为顺义八景之一。
泉水汇聚箭杆河
狐奴山也称为呼奴山,有人理解为喝呼匈奴,这一解释或许有些偏颇。三国时,曹操就曾征伐乌桓,率兵直抵东北渤海边,得胜班师,东临碣石,心潮澎湃,写出了千古名篇《观沧海》。曹操也曾驻军狐奴山,山被称为曹王山。曹操之子曹丕称皇,是为魏文帝,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到此巡视,可见这座不到百米高的小山在当时的争夺之激烈。曹操和曹丕都在狐奴山留下了印记,这里的魏家店村由此得名。
北魏时的郦道元对狐奴山另有解释,认为“水不流曰奴”。山前曾有一潭,古称潴泽,后人称为龙潭。郦道元的解释有一定的科学性,毕竟他是研究水的专家。如今,山前的潭水早已干涸,但山名得以留存。
狐奴山上产青石、石灰,民国时已有几家石厂、灰窑。随着矿产的开掘,本来不高的山也越来越瘦小。山旁的魏家店村西就有狐奴山辟出的平地。狐奴山旁原有座小山,孤峰耸峙,据形而称为鞋山。山形略偏,谐音也写为邪山。传说是二郎神担山赶太阳,觉得硌脚,坐在地上磕打鞋子,掉出一粒石子,即为此山。鞋山上有两个石印,传说是二郎神担山留下的足迹。现在整座鞋山已成平地,了无痕迹。
狐奴山前的潭水丰富,周边多水,以致村民所打的水井常满。当地有口奇异的井,手掬可饮,一日三次涌出,有海潮时溢出更多。古人推测其水源可能与大海相通。溢出的井水疏通为渠,可以灌溉田地百亩,被称为“圣井”,于是有了“圣井三潮”,列为顺义八景之一。
狐奴山下还有多处巨大的泉眼:西南麓、东北以及东面都有泉水喷出。最大的龙尾坑位于东府村,又称东府村泉,面积约有5亩,涓涓泉涌,聚而往西,后人于周边筑起堤坝拦截。上世纪70年代,东府村泉还涌出很高的水。现今东府村东北依然有一大坑,据说是当年泉水的一角。
众多泉水在狐奴山附近汇集相聚,流向西南,合于仇家店,形成河流,曲折南行,称为“窝头河”,俗称“漒漒河”,又称“箭杆河”。至于箭杆河得名,有说因河道窄,有说因河道直,犹如一箭射出。总之,箭杆河之名形象地流传下来。

箭杆河旧河道 摄影:高文瑞
箭杆河岸是南来北往的通道,沿岸村庄众多,路上商旅往来,又是皇家出行御道,沿途河上架起多座石板或石梁桥。圣水桥在东府村西北,为箭杆河源头第一桥,道光二十四年(1844)重修。沿桥左右,绿柳成荫,过路行人多在此休息。河中设有水闸,可调节水灌溉稻田。当地传言,圣水桥的东北曾有皇帝的一亩三分地,春日于此耕种,以示重视,若无时间,由县令代劳。兴隆桥在仇家店西北,为游览狐奴山的必经之路,桥南设有碑碣。高梁桥在圣水桥西、仇家店北,明万历九年(1581)、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均有重修。
箭杆河水澄澈潆洄,两岸树木葱茏,芦苇青青,稻畦云锦,景色宜人。古人有诗《又登圣水桥望上下游》:“登桥四顾色苍茫,万物环生竞秀芳。林静风轻栖翡翠,泉流日暖戏鸳鸯。稻经雨后偏增艳,荷值晨初倍放香。田老渔夫相唱和,清幽疑入水云乡。”名胜“曲水晴涛”为顺义八景之一,既是美景,也是对河水富民的赞叹。
箭杆河自古发源于顺义境内,其流域两千年前既为富足之地,形成深厚的地域文化,延续当代,依然突显于京畿。上世纪60年代初,箭杆河受到多位老一辈作家的关注。邓拓先生写下了《箭杆河边稻米香》;老舍先生在这里创作了快板《陈各庄村养猪多》;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在南彩镇完成创作;刘厚明选定这里为典型环境,创作了话剧《箭杆河边》,此后被改编为电影,以及京剧、曲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影响了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