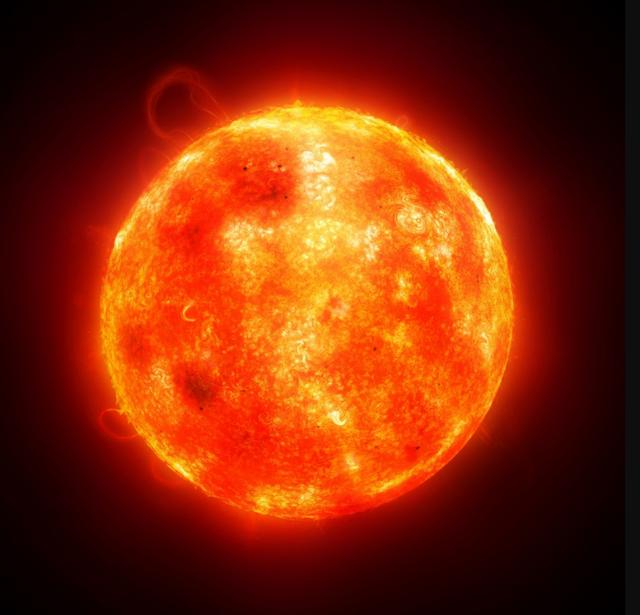马连良先生是一位勇于革新、兼收并蓄而又自辟蹊径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记得那是一九五三年,当我第一次看马先生的演出时,我获得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时我在戏校学习,经常出去看戏,思想里自然而然的有个比较,我觉得当时有些剧团的演出就整体看总有一股陈旧之感,只有主演登台时才露出光彩。
可是看马先生的戏却全然不同了,大幕徐徐拉开后,是一幅湘色绣着车马人图案的装饰幕幛,简洁美观、朴素大方。这一台戏,从主演到配演以至龙套,都很严肃整齐;马先生的嗓子、扮相、身段以及舞台风度,更显得格外出众,唱、念、做也各具特色,成为绿叶中的一朵红花。以前我只是从唱片中常听马先生早期录制的唱段,这次观摩,听其音,见其人,真把我吸引住了。以后我就可能找机会多听马先生的戏,越听越爱,于是就学起来,直到一九六一年,正式拜马先生为师。

马连良与袁世海、冯志孝
谈起马老师的戏,许多评论他的人,都喜欢用美、帅、俏、潇洒自如等形容他的艺术风格。我从艺术实践中,也深深感到:正是他把这些特点恰当而自然地融汇在唱、念、做之中,形成了完整、统一的独特艺术流派:马派艺术。
注重从人物出发,着力研究刻划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心理变化,再运用艺术手段加以表现,贯串于唱、念、做之中,是马派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唱方面看,比如:《淮河营》(《十老安刘》一折)这个戏里共安排了四段【流水板】,但是让人听了并没有雷同感。这是因为马老师在唱腔创造和运用上,总是竭力把握住剧情与人物,四段唱虽用同一板式,由于人物感情不同,唱得就有显著不同。这四段【流水板】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抓住核心段落,根据人物情感,调动艺术手段,加以重点渲染。
这个重点唱段是: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咱!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滑?左手拉住李左车,右手再把栾布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生死二字且由他。

马连良之《淮河营》
这个戏是马老师在一九三八年首创演出,至今四十多年,广为流传,盛行不衰。尤其是这段【流水】的结尾“三人同把鬼门关上爬”的“爬”字,运用了一个多层次而婉转迂回的大腔,它有单、有双,有起、有伏,有停、有连,圆润巧妙,华丽俏皮,通过唱腔把机智老练、为炎汉社稷不畏艰险的老蒯彻,刻戈得淋漓尽致。
常听老一辈艺术家讲,京剧中的【散板】,往往是衡量演员唱工造诣深浅的试金石。马老师对【散板】的演唱,很有独到之处,极见功夫。比如《淮河营》蒯彻见刘长以前对栾布有十七句【西皮散板】(栾布接一句),这是难度较大的唱段。马老师曾对我说:“这段唱要象说话一样自然,有时要拉大幅度,有时又要十分简洁,抑扬顿挫,依情而定。”他还常对我讲:“演戏要把刻划人物贯串始终。”这就是说不仅大段的重点唱要注意刻划人物,即使是几句【散板】也不能不加注意。
比如《借东风》诸葛亮唱完大段【二黄导板、原板】以后,有两句【二黄散板】结尾:“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趁此时返夏口再做主张。”他曾对我讲,这两句【散板】轻视不得,它正是全面深入刻划诸葛亮性格特征的主要环节。孔明知天文,晓地理,他料到甲子日东风必降,这时果然起了东风,他知道大功已然告成,心中悠然自得。前一句就是表达这个感情的。在这里他把前几个字处理得很简洁,后面的“从东而降”,字与字之间用“含韵”的办法相互勾通起来,当“降”字出口以后,很自然地急速归韵,接着一停,这一停气不能换,采用“音断气不断”的方法,巧妙舒展地再把“降”字变为“啊哦”。这样,料事如神、坦然自若、临危不惧、风度翩翩的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马老师这样对【散板】同样重视人物特性,足见他对艺术创造是一丝不苟、独具匠心的。

马连良之《借东风》
当初我向马老师学戏的时候,我曾提出过念白比较难于掌握的问题。他一方面要我多听,多练,掌握规律;一方面又告诉我要掌握窍门。窍门是什么呢?
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我和老师在他家的大核桃树下乘凉,这时老师要我表演一遍蒯彻见刘长这段戏,表演以后,老师说:“念得不够生动……”说着他离开藤椅,给我做了示范,他边念边表演:“……非我发笑,我哇倒无有什么罪名,你今头顶三行大罪,你可知道哇!”他的念白语气特别有生活气息,加上面部表情、身段的相应配合,非常逼真、完美。我受到了启发,使我认识到念白要想念得好,念得生动,富有表现力,除去要练吐字、发音等口齿的基本功以外,在创造角色时,还要重视研究剧本,体会人物,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深厚的基本功,要想达到高水平是不可能的。
马老师的念白,在语调的艺术处理上是既“下得去”,又“上得来”。所谓“上得来,下得去”,全不是人为的、造做的,而是依人而变化,依情而安排。比如蒯彻念:“姓蒯名彻字文通,高皇封过一字不斩舌辩侯, 喏喏喏就是我哇!”他这段念白的声调并不高,目的在于刻划机智、老练的蒯彻,栾布、李左车被囚的情况下,他决定以玩世不恭、傲慢不逊的办法,对待暴虐烈性的刘长,进而说服刘长诛吕扶汉。为此采取了“下得去”的念法。
但在《甘露寺》大佛殿乔玄谏主这场戏中,他就又是另一种念法。乔玄以他的政治远见,主张孙刘结亲,永结盟好,一同出兵共敌曹操,为此他在吴太后面前,竭力争取太后对刘备的赏识,力保孙、刘结亲能够成为现实;这样当刘备对太后讲述自己身世时,乔玄在一旁给予了锦上添花的着重描绘。乔玄这样做,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是有内在根据的。他念时提起调门,激情满怀,绘声绘色,手口相应。对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和诸葛亮竭力称颂,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当然也就能够达到引起吴国太共鸣的目的了。我以为继承马派的表演艺术,如果忽视念白是不足以尽得马派之长的。马派念白是很“吃功夫”的,它是表现人物的一个重要手段。

马连良之《甘露寺》
尽管我和马老师不在一个剧团工作,但我总要尽可能多地观摩他的演出,特别是拜师以后,即使他赴外地巡回演出,有条件的话,组织上也支持我去,这种跟班学习,使我收获不小。我格外欣赏马老师演的《四进士》。那宋士杰三次步入公堂的表演,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这次我排演《四进士》,回忆以往仍记得很清,可惜我却还没有学到好处。“报,宋士杰告进!”三个公堂宋士杰全是用这一句词“报门”,在舞台调度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可是由于剧情的发展,使人物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内容的变化,决定表演形式不同。马老师在头公堂念“报,宋士杰告进!”这句词时,语调长短相宜、柔刚相济,挺拔有力、苍劲浑厚。随着,他用左手摘掉“鸭尾巾”,双手持巾拱手,待念到“宋士杰”时,将白髯自左而右涮到右小臂上,这时略有老人的抖动,再念“告(哇)进”,接着右手抓水袖,左手持巾提褶子,略毛腰低头而进。这一组精彩的表演既有生活、又有艺术,深刻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宋士杰携干女杨素贞击鼓鸣冤是急促中决定的,加上这次抱打不平的对象是异乡人,自己也是刚刚介入未免有些生疏,但是他凭着自己饱经世故的丰富经验,既来之则安之,镇定稳健地去见顾读。可是到了二公堂,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田伦用三百两银子贿赂了顾读,杨素贞的官司眼看要输,宋士杰通过“盗书”完全掌握了田、顾之间的勾结,这时受贿后的顾读拷打杨素贞逼她招供,来了个“原告收监,被告讨保”,宋士杰对此怒不可遏,于是站在堂口高喊“冤枉”,以此惊动顾读,好与之当面辩理。当顾读无可奈何地再传宋士杰上堂时,马老师这次“报门”,运用的是偏高而短促的语气。身段也有了变化,他右手摘下鸭尾巾,左手理一下头上的“发髻”,振作一下老精神,然后在大锣一锤锣上,右手持鸭尾巾一衬,用来表示宋士杰满腔怒火,接着左手提起褶子,用较快的节奏,踩着锣经匆匆而入。
三公堂是宋士杰为了告倒田、顾、刘三个官,舍命去见按院大人。这时,马老师用低而重的语调念那句“报,宋士杰告(哇)进!”接着,双手提起褶子(这次他原就没戴鸭尾巾),大幅度地毛腰低头恭恭敬敬地去见毛朋,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这位按院大人了。从宋士杰三次步入公堂的念法与身段的安排中,可以看到马老师在艺术创造上,注重研究剧中人物性格与思想脉络,注重研究环境对象与人物间的关系,他有深厚的基本功,体现这些复杂而变幻的人物感情,在表演上达到了形意合一的理想境地。马老师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和苦心钻研,以及丰富的舞台实践,不仅继承了传统戏曲表演艺术,而且博采众长,大胆恰当地加以革新、发展,创造了许多深刻、逼真的艺术形象,为丰富京剧表演艺术作出了贡献。

马连良之《四进士》
我认为,马老师的整个表演艺术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重视整个戏的演出效果,务使一台无二戏,唱、念、做并重而又都具有独创成果,善于从生活中广泛汲取创造素材,并选择恰当的艺术手段加以体现,勇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综合一体,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马派艺术。马老师能在艺术上所取得成就的主要方面,就在于他能适应时代和人民对戏曲日益提高的要求。我想今天继承流派艺术不能单纯注意“派”的形式而忽视刻划人物,我们继承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革新,使戏曲事业更加适应今天的观众需要,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现实。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勉、向前!不断把新的艺术成果,贡献给广大人民。
《人民戏剧》198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