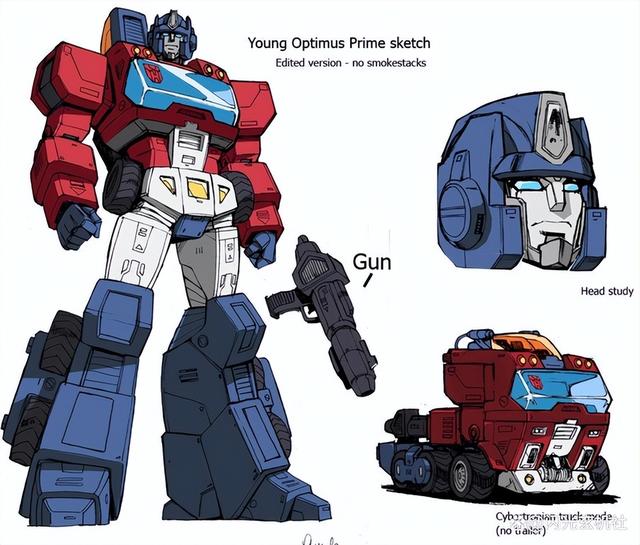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演进向 野,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大禹治水历史和传说的区别?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大禹治水历史和传说的区别
大禹治水传说的历史演进
向 野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其生平和治水联系在一起;他和他的儿子启开创了夏朝,从而为中国几千年的世袭制政权奠定了基础。有关他的记载,零星见于西周以来的各种史料,其中尤以《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所记最为系统,可以说是当时各种资料的一个综合。因此,下文中,我们首先根据《史记》提供的脉络,对禹的整个生平作一概览;然后对其中涉及问题,加以简要分析。
一
按照《史记》的说法,禹和尧、舜一样,都出自黄帝世系,只是所属支系有所不同:尧为青阳一支,而舜、禹则为昌意一支。当尧之时,天下遭遇洪水之害。尧接受四岳的建议,任命鲧来治理洪水。然而9年过去,鲧并没有治水成功。这时,尧的年纪大了,决定找个有贤德的人,把帝位禅让给他。于是众人向尧推荐了舜。这时的舜还是一介平民,但尧仍然决定让舜摄行天子之政。而舜果然不负众望,他发现鲧治水无功,便在羽山将其殛灭。这一举措十分果断,令天下为之叹服。因此,尧死后,舜便继承了尧的帝位。他启用鲧的儿子,也就是禹,命其继续治水;又命皋陶、伯益为其辅佐,以成治水之功。
鲧以息壤治水
禹得到舜的任用,有感于其父无功而受诛,于是劳身焦思,治水13年,路过家门也不入,终于把洪水平抑下去。《国语·周语下》说,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是因为他所用方法和鲧不同。鲧采用的方法是防堵,而禹采用的方法则是疏导:随顺水的自然趋势,将水引入江、河之中,最后注入大海。所以孟子评论禹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又说:“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而禹在治水同时,还下工夫考察沿途各地形势,从而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并详细记录各州的山川和物产情况。禹的功绩如此之大,所以舜年老以后,便把帝位禅让给禹,禹也因此作了“天子”。
到了晚年,禹原本也想仿效尧、舜成例,把帝位禅让给益。但是益的功绩没有舜、禹那样伟大,而禹的儿子启又是个有才能的人,所以天下人不拥戴益而拥戴启,于是启便乘势建立夏王朝,从而开启世袭制时代。
总的来说,禹的一生以治水为其事业的根本。春秋时,刘定公评价禹的功绩,曾这样说道:“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足见禹对于后世的影响,的确十分深远。古人根据崇德
报功的观念,把禹奉为社神,和后稷(传说中周人的始祖,被后世奉为谷神)相并列,称为“社稷”。《史记·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这是对大禹功绩的充分肯定。
以上,我们根据《史记》,简要叙述禹的主要生平和事迹。下文,我们将考察两周时期有关禹的更早记载,并将其与《史记》加以比较,从而探索大禹传说在历史中经历哪些发展,产生何种演变。
二
司马迁创作《史记》,搜集采纳大量的早期史料,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而他采择史料的标准,据其本人自述,乃是“考信于六艺”“不离古文者近是”。因此,在写作《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时,其所采用的史料主要来自《尧典》《皋陶谟》《禹贡》这样的经籍,和《五帝德》《帝系姓》一类的“古文”篇章(用战国文字写成的资料)。在司马迁看来,这些材料来源甚古,因而都是确实可靠的。而他自己则用巧妙笔法,把这些不同来源的史料缀集起来,写成一篇详实的叙述,以供后世学者参考。这是他的功绩所在。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古代的神话传说会随着时代而演变。《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所依据的材料,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而战国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这一时期,人的理性精神取得长足进步,曾经笼罩社会、政治的鬼神思想,这时都受到系统怀疑,从而失去往日权威。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人们对于古史中带有神秘色彩的记述,自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将其摈弃于史料之外。例如,司马迁曾见过一种《禹本纪》,其内容大概类似于《山海经》,充斥着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这一材料今天已经完全失传,而司马迁也没有把它采入《史记》之中。这样的处理方式,放在汉代,固然称得上是一种崇尚理性、不肯轻信的著史态度。但在今天看来,人类历史的开端总是浸没在神秘主义的气氛中,因此越是带有神话气息的材料,其产生的时代反而可能越早,因而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就越可能反映出早期社会的某些特征,从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例如,大禹一生中最具重要地位的治水传说,起初便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诗经·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由这一叙述可知,在古人心目中,大地本是一片汪洋,禹从天上降下,始在茫茫洪水之中布下土地。《楚辞·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从这里的“降省”和“下土”,足以看出禹是从天上降下,和《诗经》所述正是一脉相承。而禹平抑洪水的方式乃是“敷土”。《尚书·禹贡》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何谓“敷土”?
其实就是布设土地。《山海经·海内经》上说“禹、鲧是始布土”,把“敷”训为“布”,可谓达诂。因此,“禹敷土”即禹布设土地。这在古代本是一个神话。《海内经》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见鲧治水,乃是用上帝的“息壤”去填平洪水。根据郭璞注,“息壤”是一种自动生长的土地。鲧因为偷取“息壤”而为上帝所诛灭,但上帝仍授命禹完成布土的功业。《淮南子·墬形训》说:“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这和《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以及《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联系起来,可知世上的山乃是禹用息土“甸”(奠)起来的。而禹也正是由于奠治山川,而被后世尊为社神。
《说文》:“社,地主也。”甲骨文“社”字径写作“土”。所以社神其实就是土地山川的神主。
《尚书·吕刑》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史记·夏本纪》也说:“于是天下皆宗禹……为山川神主。”这些都反映出原始神话中禹的神职所在。
明白了禹治水所采用的方式是“敷土”,是“奠治山川”,则我们对于鲧治水所采用的方法也就能够知其大概了。
历来关于鲧、禹治水的描述,都说鲧和禹治水的方法不同,因而取得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楚辞·天问》说禹继承鲧的事业,是“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因此发问道:“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的话,则说:
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言下之意,鲧之所以被殛,乃是由于效法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把防堵作为平洪水的一种手段。而禹则不然。禹治水,乃是通过疏导的方法,“高高下下,疏川导滞”,所以才能取得成功。但我们前文已经说过,鲧之所以被上帝殛灭,是因为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而不是因为采用错误的治水方法。实际上,早期神话中的鲧、禹都是用息土去填平洪水、奠治山川。譬如《楚辞·天问》上说:“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其中“窴”(填)和“坟”(堆土),都是针对治水方法所发的疑问。我们从这些零星残存的资料中,可以看出,鲧、禹治水的方法在早期传说中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例如铜器“豳公盨”的铭文说:“禹敷土,隓山濬川。”这里的“隓”字,裘锡圭释为“堕”。《禹贡》说:“禹敷土,随山刊木。”《书序》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都是本此铭文而来,唯把“隓”字读成“随”,于是禹堕山的传说遂不为后人所知晓。其实禹不仅要濬川,也还要堕山,这和鲧的“堕高堙庳”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敷土”后整治大地、奠定山川的工作之一。而《周语》之所以把鲧、禹治水的方法对立起来,很明显是受到春秋、战国之际时代风气影响。当时,由于水利技术的进步,列国间越来越多地采取疏导的方法用于防洪;过去盛行一时的防堵政策,这时被看作一种危害邻国的手段。例如《汉书·沟洫志》说:“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孟子》中白圭以治水闻名于世,他采用的方法就是防堵。而孟子评论他,则说:“今吾子以邻国为壑,……仁人之所恶也。”可见当时的人已不赞成采用防堵的方法来治水,因此为适应这种变化,传说中鲧、禹治水的内容也不得不有所改变。于是禹作为上古治水的圣人,就不再以防堵的方法治水,而变为完全采用疏导的方式。
我们现在知道,上古神话中,禹治水的伟业,原是用息土填平洪水,从而奠定大地山川的神话,于是也就可以理解,古代不同部族的人们何以都把大地看成是“禹绩”的一部分。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逸周书·商誓解》:“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这是周人对于“禹绩(迹)”的认识。此外,秦公簋也说:“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责(绩),十又二公,才(在)帝之坏。”(集成4315)齐侯钟、镈亦云:“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所,尃(溥)受天命,剪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集成:钟272—278、镈285)可见齐人、秦人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这些都可证古代殷、周、齐、秦等族都自认为居住在禹所敷布的土地上。
古代神话中,禹敷土乃是受上帝命令。而按照后世的说法,鲧治水乃是奉尧之命,因为功用不成,遭舜殛灭;直到舜起用禹,才终于治水成功。这里,上帝的位置被尧、舜所取代,鲧、禹分别成了尧、舜的臣子。而这和古代神话的原型明显矛盾。《墨子·尚贤中》说:“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据此,鲧原是上帝的长子,因为“废帝之德庸”而受刑,其中并没有尧、舜的踪迹。而禹的情形也是如此,《墨子·非攻下》记禹征三苗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这里的“高阳”即帝颛顼,按照古代传说,乃是建立“星与日辰之位”的天帝。我们看《太平御览》卷882引《随巢子》“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可证禹征三苗,实受天帝所命。此外,《墨子·兼爱下》引逸书《禹誓》,曰:“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观其辞气,也与汤、武征伐桀、纣并无不同,禹在这里乃是一个君王,一点也看不出受命于舜的痕迹。
同样,禹治水也是受天帝命令。《禹贡》记禹“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历来的注释家以为赐禹玄圭的应当是舜。然而《禹贡》中通篇没有尧、舜的影子。我们看《吕刑》记有苗乱作刑政,“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三后……禹平水土”,明确说上帝遏绝了苗民,乃命禹下来平治水土。可见《禹贡》中禹告成功的对象也应是天,而赐其玄圭的则是天帝。《尚书·洪范》说:“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所述内容虽与《禹贡》等书不尽相符,但在上帝殛鲧、天赐洪范这一主题上,则仍保留了早期神话的色彩。而金文“豳公盨”更于开篇之首,即曰“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尤可证禹在西周时期的神话中,乃是由天帝所命,
实际上,尧、舜的传说,最早大概起源于古代的东方,而不为西土夏、周一系的部族所接受。所以《诗经》《尚书》中成书最早的一些篇目,其中虽有很多地方谈到禹,却全无一字提及禹之前的尧、舜,反而把禹看成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人物:大地是由禹所造,各民族都居在他所奠定的土地上。例如豳公盨叙述“禹敷土,堕山濬川”之后,接着便说上帝“降民、监德”,可见民乃是治水后才由上帝降下来。这一点可以从清华简《厚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厚父》这样说:
王若曰:“厚父!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在夏之哲王,乃严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盘于康,以庶民惟政之恭,天则弗斁,永保夏邦。其在时后王之飨国,肆祀三后,永叙在服……”
这里明确提到,上帝建立夏邦,为之降民,乃是在禹平治水土之后。启是夏的第一个君主(“启惟后”),而皋陶则是上帝降下来辅佐启的。因此,夏朝后来的君主,便把禹、启、皋陶奉为上帝所命的“三后”。从这里,我们还看不出禹和启有什么具体关系。启所以在禹之后,只是由于夏是在平治水土以后建立的,而启则是夏的开国之君。在这一版本的传说里,夏确实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而禹则是先于夏而存在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最早的古人。
及至武王伐纣,建立起庞大的西周王朝,周人将自己的支系、盟友、婚姻氏族大量分封到东土,从而控制了广大的东方地区,东、西方两系的地方文化开始逐渐融合,尧、舜的传说也慢慢被西土各族所接受。这时,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顺序久已深入人心,而禹和夏的历史又是前后相承,于是尧、舜的传说只好排在禹的前面。反映在古史系统中,则是如《尧典》《皋陶谟》等书所记载,原本独立的治水神话,现在和尧、舜的传说融合在一起:禹成了帝舜的臣子,其治水也变成是奉了帝舜的命令。
随着这一发展而来的,是禅让传说的扩张。原本,禅让之事完全是发生于尧、舜之间,这是尧舜传说的基础。尧、舜之所以在口耳相传的一系列古帝先王中享有特殊声望,正是和他们的禅让故事分不开。然而到了春秋时期,不仅尧、舜之间存在禅让关系,就连舜和禹之间也产生禅让关系。《论语·尧曰篇》说: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这是出于孔门七十子后学的记录(大概形成于战国早期),已经显示出尧禅舜、舜禅禹的内容。而后,稍晚的各家学说,如《孟子》《庄子》《吕氏春秋》,也都提到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关系。竹简《容成氏》甚至推而广之,把禅让的关系加在上古一切帝王的身上。于是三代以上,几乎无人不禅。然而,假若古史传说一开始便是如此,那么尧、舜相禅,又有什么好值得称颂的特别地方呢?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尧、舜禅让本是一切禅让故事的母题,它在历史上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不一定是按战国诸子所想象的形式发生。这一传说流传到战国时,已发生若干细微的形变(例如舜的身份从有虞氏的乐正变成了一介平民);同时,由于文化的交流,尧舜传说和大禹治水的神话也开始发生融合,于是禅让的美德不再专属于尧、舜,而是一并扩展到舜、禹之上,以致为战国时代的诸子所接受。
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古史传说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一步步演变。到目前为止,尧、舜、禹的传说虽然融合在一起,但这些古帝之间还没有形成相互的血缘关系。禹尽管已经成为舜的臣子,却还没有变成舜的族亲。然而到了战国晚期,统一的趋势已经极为明显,于是产生出《五帝德》《帝系》一类的篇目,把历史上几个有名的古帝王(连同早期神话中的上帝)相互连接起来,赋予其血缘上的联系。《帝系》中以黄帝为始祖的系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帝系》上说: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这是把鲧和禹同黄帝、颛顼的世系连在一起,形成的一个连续的家族关系。《帝系》又说:
据此,则舜也是出自黄帝、颛顼一系。我们正是读了《帝系》,才知道原来舜、禹之间不仅有着君臣关系,还有着更进一步的亲族关系。这种关系,自战国末年产生以后,又掺入到列国各自的“世奠系”中,形成今天所见的《世本》。而司马迁撰作《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正是依据《帝系》《世本》等资料,把古代不同部族的始祖通通归并到黄帝一系。可以说,此后2000年,人们对于上古历史的认知,无不建立在这一历史体系的基础上。
但这一体系毕竟形成于战国晚期,其中不免有自相抵牾的内容。例如,按照《帝系》所云,禹为颛顼之孙,而舜则是颛顼的六世孙;假若《帝系》记载可靠的话,则二者无论如何不能处于同一个时代。大概《帝系》的作者,只是把当时流传的几种谱系拼合在一起,而没有顾及其中的矛盾,所以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地方。反过来,我们也就知道,《帝系》中舜的谱系里,从穷蝉到瞽叟的五代,其形成时间应早于《帝系》成书的年代。因为到《帝系》成书时代,从穷蝉到瞽叟的谱系已经腾于众口,成为战国晚期公认的“史实”,因此《帝系》的作者也只好把它整个嵌入到黄帝的世系中,而无法对其加以更改。我们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传说演变的一些痕迹,但由于史料的欠缺,想要探明其演变的每一个环节,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三
上文中,我们讨论了大禹传说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禹在古史传说中的地位极其特殊。按照传统历史的论述,禹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他因为治水有功而受禅,成为天子;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启建立夏王朝,开创世袭制统治。在这一变化中,禹处于枢纽位置。早于他的尧、舜,不见称于《诗》《书》中最早的篇目,却是《尧典》《皋陶谟》等篇中称颂备至的人物,其历史来源及传说演变的痕迹都已模糊不清、难于详考。我们所能看到的尧、舜传说,基本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版本,其中包含的神话色彩大部分已消褪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唯独禹,由于其“治水传说”内容丰富和富于传奇色彩,在整个先秦时期一直受到人们传颂,以至于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留下充分资料,可供我们研究和探讨。我们能从残存的史料中,挖掘出那些独立于尧舜传说的内容,还原其具有神话色彩的真实面相,并知道这些原始的内容是如何同尧舜传说发生关系,又是如何同禅让产生连接,进而成为大一统的黄帝谱系的一部分,这实在是我们的幸运。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分析方式割裂了史料,滥用了“默证”的手法,导致古史重建的失败。晚近,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更被认为佐证了这一说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正如另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简帛古书的出土,部分证明了前人的某些看法中存在着应当修订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必须完全按照古史体系成熟、定型时期的式样来描述上古的历史。
早期史料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的古史观念和成熟时期的史料所反映的古史观念有所不同。而挖掘这种不同,并从史料和逻辑两方面疏通其联系,正是上古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随着新材料的继续出土,这种任务势必一直进行下去。大禹的研究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
我们相信,有关大禹传说的争论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