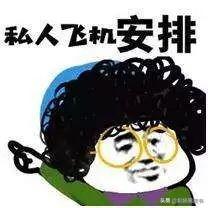“圩”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沿湖沿河低洼区防水护田而筑的堤坝。一种则指村居,同“围子”,围绕村庄用土石筑成障碍物,或挖掘深壕宽沟,围在里面的村庄就叫作“圩”。
从古至今,合肥有不少地方使用“圩”作为地名。如淮军名将的故居刘老圩、张老圩、周老圩、唐五房圩;李鸿章侄女婿张文燕在肥东建起的“花墩圩”;相传为庐江八景之“青帘渔火”所在的杨柳圩;曾是“项羽谋士”范增练兵场和养马场的郭家圩、亚父圩;有着大孔祠堂、打夯歌等灿烂文化的“鱼米之乡”大圩……这些“圩”可不是一个个普通的地名,它们大多承载着合肥这座古城的悠久历史,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千年文脉和珍贵记忆,渗透出浓浓的“文化范儿”。

刘老圩
圩堡群:淮军文化发源地
合肥市肥西县地处巢湖西岸,有派河、丰乐河流经境内。沿湖沿河过去多为低滩洼地,先民为了垦殖田亩,在岸边多修筑圩堤,阻挡洪水。“合肥有圩八十多个。”其中,今属肥西的就有杨家圩、徐家圩、白露圩、莲花圩、临岗圩、沙滩圩、义成圩等30多个,还有众多的小圩口。清末至民国的150年间,沿湖围滩又建成东安、五合、幸福、大兴等圩口。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开展水利建设,组织联圩工程,将众多小圩口连成一体,成为防洪能力大大增强的万亩大圩。
作为居住地的“圩子”,一般始于晚清时期淮军兴起之后。作为淮军故里,肥西地区走出了一大批淮军将士,功成名就之后,这些淮军将领纷纷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在家乡兴土木、建庄园、购田地、置产业。由此,肥西各地建成了众多各式各样、规模不一的庄园、圩堡,从而形成肥西独特的淮军圩堡群。至今仍然保留基本格局、规模较大的圩堡就有刘老圩(刘铭传)、张老圩(张树声)、张新圩(张树屏)、周老圩(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唐五房圩(唐殿魁、唐定奎兄弟)……这些圩堡大多建筑在丘陵地带的两冲之中,或山地的两山夹坳之间,以保证水源充足。圩子一般外环深壕,内砌石墙,四角建有碉堡,与外通行利用吊桥,圩子的防御功能堪称古城池的翻版。也有部分圩堡建在旱地,无外壕,则称为“早圩子”。当然,还有不少并非准军起家的富户豪强,也修建同一类型的圩子。

被称为“刘老圩”的刘铭传故居
圩堡内的建筑形式,则汇集了中国传统建筑学上的精华,体现了江淮民居特色。一般建有正厅、客厅、堂楼,内设书房、小姐楼、起居室,以及花园、菜园、库房和兵勇、仆人住房等上百十间,建造精细,雕梁画栋,花园则仿苏扬园林建筑,少数还有西式建筑设备。位于柿树岗乡的唐五房圩中,就保存有一座“走马转心楼”。

唐五房圩
虽然年代久远,这些圩堡群原先的建筑物有些已毁灭或损坏严重,但基本保持了原先圩子的建筑格局,一些存留建筑物尚能还原原貌。今天我们走进圩堡群,犹如走进历史的深处,抬眼望去,便能发现历史残留的文化遗存:更楼、转心楼、抱鼓石、旗杆石、柱础,还有皂荚、广玉兰、银杏等数株百年古树。这些既富有地方人文特色,又具有自然特色的圩堡群,是对当地旅游资源的重要补充,是一笔有待于切实加以保护和着力开发的珍贵财富。
李鸿章侄女婿建“花墩圩”
在合肥东北角,有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美丽乡村,这个村也因为和李鸿章家族的千丝万缕联系而远近闻名。这就是肥东县众兴乡的花灯村。“花灯”原名“花墩”,李鸿章侄女婿张文燕还曾在此建起“花墩圩”。

花灯村
花灯村民以张姓为主,张家最有名的人物,首推曾为淮军团总的张绍棠。张氏家族曾是花墩村的望族,合肥地区的首富。李鸿章家族原本姓许,明朝时期为躲避战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以耕读为生,生活十分贫困,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此后,李家进士、举人和秀才不断涌现,当官的也越来越多。李鸿章和他哥哥李瀚章都官居一品,位极人臣。由于靠得近,又同是望族,张家与李家世代联姻。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
当时,张家富足,李鸿章兄弟经常依靠张家接济度日,连婚事之需也是靠张家资助,因此李鸿章兄弟对张家非常感激。后来,李鸿章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佽居多。”
于是,当李鸿章为淮军回故乡招募团练时,张绍棠亦是积极响应,由于李鸿章的特别关照,张绍棠获任李鸿章的亲兵营军官,曾因功获“鼓勇巴图鲁”勇号。后来张家后人衣锦还乡,大兴土木,盖了很多圩子。清朝同治年间,李鸿章哥哥李瀚章的长婿张文燕在花墩李元自然村附近建起“洄溪别墅”,四周两道溪水,呈“回”字形,溪内遍种荷花,并广植花木,又称“花墩圩”。
1895年,李鸿章外甥张文宣在中日刘公岛海战中与丁汝昌等一道自杀殉国,为表彰张文宣的英勇就义,皇帝特地赐予“花墩圩”一对大花灯,逢年过节,“花墩圩”都会拿出来挂在大门上,于是久而久之,花墩变为了花灯,花灯村的名字由此而来。当然,这个说法的真伪还无从分辨,却给“花灯”这个名字,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据说,“花墩圩”占地50亩,曾有内外两道护城河,在护城河内有12幢气势恢弘的楼房,圩子内古树参天,其中不乏名贵树木。解放后曾作为花墩中学、小学校舍,当时还有一棵能同时结不同果子的“五果树”。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富丽堂皇的圩子被毁。值得庆幸的是,由李鸿章赏赐的三棵古枣树完好地存留了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在花墩四房组,三棵树龄近130年的古枣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据说,当年因四房组张继涛随李鸿章征战有功,故赏三棵枣树,并自天津运回栽植。据当地人介绍说,这三棵枣树时至今日依然能开花结果,如今已被列为三级古树保护起来,周围人都以此为荣。

李鸿章赠送给“花墩圩”的枣树
“青帘渔火”杨柳圩
素有“四面杨柳沃田地,满圩春风鱼米乡”之美誉的庐江县白湖镇杨柳圩,是一个有着五万亩农田的农业大圩,地处庐江的最东部,军二路贯通全境,与无为市蜀山镇接壤。圩内水系发达、土地肥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其水面近2万亩,盛产水稻、鱼虾、荸荠、芡实……圩内沟渠纵横、水系发达,是一轴微缩的皖江水乡长卷。

杨柳圩
“一丝杨柳千丝恨,三分春色二分休”,杨柳,并非指元代散曲中的杨柳树,而是在无从稽考的年代,圩内居有杨、柳两姓大户,居民以此姓居多。“生态田园诗,动态水墨画”。杨柳,相传为庐江八景之“青帘渔火”所在,历史的痕迹、文化的遗迹犹可触摸。南堤岸边,久远年代,每逢盛夏,南北渔家,泊船滩涂,夜晚掌灯,倒映成趣;举目远眺,光影摇曳,桅杆挥动,水声唱晚,甚为壮观。如今,盛景虽去,古韵犹存,目之所及,令人遐思。

杨柳圩
值得玩味的是,有人把几处地名串成了一个风趣的小故事。
据传,抗战时期,日军企图遣兵进发杨柳,行至圩口东向时,听闻当地百姓方言,告知后有“恶”山、前有“死”屯、再向前还有“扛头”“牌坊”(即当地的岳山、史屯和杭头、牌坊),凶狠肃杀,穷途恶兆,敌军遂闻风丧胆,兵不血刃,不战而退。这只是无以实证的民间趣闻,却彰显了杨柳人民同仇敌忾的民族爱国热情。
庐剧,是当地代表性的地方文化符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帘渔火”所在的一带,有套小戏班子,坊称“青帘班子”,出挑了几个唱腔清亮、扮相清爽的生旦“台柱子”,曾经风靡一时、蜚声乡里。水乡正二月里的农闲时日,就闹腾开了,文臣武将,才子佳人,粉墨登场,咚咚锵锵,咿咿呀呀,那逼仄的小戏台上,唱不完的“爱恨情仇,善田福果”,诉不尽的“公子落难,小姐讨饭”……

“六月六,赛龙舟,千门万户庆丰收”。划龙船、赛龙舟,是水乡杨柳一个盛大的传统民俗。农历六月初六,成了农家人盛装的节日。成千上万的乡亲们从四里八乡赶来,吴家渡、柯家拐一带的大堤上,披红挂彩,人头攒动,河道里,十数条龙舟如同箭般竞发博弈,赛手们力拔洪荒,挥汗如雨,舵手们则铆足精神,吆声如雷,交织着两岸游人的喝彩声、噪闹声,声如鼎沸,热闹非常。如今,水乡的龙舟赛已成常态化,传统民俗得到了传扬与发展。


2017年6月29日(农历六月初六),在白湖镇青帘村青帘河举行青帘渔火龙舟赛,67条龙舟同河竞渡,场面震憾。
杨柳,因为有水,才平添了几分灵动。在这个傍水而居、枕水而栖的水乡,足出户门百步之内,定有渠有水,有船有田。

在他乡人看来,蟹儿、鳝儿和茭白、菱角这些“水八鲜”,却并不是这个水乡的稀罕物;那些枣红色的荸荠们,才是绿色生态的宠儿,这些“宝贝”在松软肥沃的褐泥里,可是酣睡了有30余年了。

荸荠
改革开放以来,水乡农民在党和政府以及当地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下,积极探索产业转型,逐渐改变单一的水稻生产模式,找到了最适合圩区种植的经济作物——荸荠。水乡农民种植荸荠已有几十年历史,如今已成为支柱性经济作物。目前杨柳圩荸荠种植面积已达近2万亩,年产量近4万吨,被誉为全国最大的“荸荠之乡”。如今,杨柳荸荠已获国家地理标志和绿色农产品认证,远销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大中城市,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古圩彰显亚父文化
巢湖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巢北有涂山文化,巢南有巢父文化,巢西有焦姥文化,巢东有亚父文化。而位于巢湖鼓山脚下的郭家圩、亚父圩,便是亚父文化的体现。
司马迁《史记》记述:“亚父者,范增也。”又记:“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索居家,好奇计。”范增,西楚霸王项羽的主要谋士,秦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被项羽尊称为“亚父”。

位于旗山亚父祠内的范增铜像
据典籍和民间传说,范增的故里在现巢城东五里左右的鼓山脚下,秦时,范增在此养精蓄锐。

鼓山脚下的郭家圩、亚父圩曾是范增的练兵场和养马场
据称,鼓山脚下的郭家圩、亚父圩曾是范增的练兵场和养马场,山东面的徐家洼村是范增的扎营地。民间流传范增当年在此扎营练兵,打了七口水井,取意“七星赶月”,喻义合力战胜强秦。现徐家洼村中存旧井三口,村北有一村名“月牙塘”,村前的月牙塘仍存。

七星井中的一口,传说是喇叭形,井底有几间房的面积

“七星赶月”中的月牙塘仍存,据说面积已经缩小
鼓山脚下徐家洼村后,旧时确存兵营古墙遗址,据传还有玉门槛。上世纪中叶,乡人在遗址上垦荒,挖出许多古砖、瓦砾和大量陶制的排水涵筒。
徐家洼、月牙塘等村背风向阳,依山傍水,林深静幽,东面是肥沃的圩田,又有清亮的溪流环绕,不仅风光宜人,也确是居家生产、生活的好地方。
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亚父”之名始终响彻这片土地。
鱼米大圩的灿烂文化
大圩,南濒巢湖,绿肥水美,物产富饶,自古就有“合肥粮仓”、“鱼米之乡”美称。历史的烟云造就了这个“鱼米之乡”灿烂的文化。在时光的长河中,大圩人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打夯歌、玩花船、舞龙狮、唱庐剧……作为全国文明村镇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大圩品位的提升,离不开外在的景观,更离不开内在的文化。美景之为血肉,文化之为骨骼,一个大美的大圩充实而又丰满。

大圩
位于大圩镇学塘村的大孔祠堂,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作为合肥市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古代宗祠之一,大孔祠堂也是合肥现有古建筑中彩绘规格和档次最高的宗祠。1986年被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又被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孔祠堂建于清末(1905年),是时任甘肃省督办、御赐二品顶戴和总统右江各军的孔华清(大圩镇人)为家乡族人所修建的宗祠。整个古建筑群属江淮地区古建筑遗存中的珍品和瑰宝,整体布局亦与孔庙、大成殿、文庙等一脉相承,其在儒家学派发展的研究中起着积极作用。

位于大圩镇的大孔祠堂
近观大孔祠堂,整个建筑群分布合理。其主轴线南北向,分为山门殿、寝殿、庑殿、寮殿、附殿、藏书楼及露台等。穿过大孔祠堂二道门,红木的香气扑面而来,大殿均为叠梁式多檀多步架单层建筑格局;中脊柱全部落地,列枋上有镏金的彩绘残存,图案俱行龙、盘龙之态;其他梁枋上三彩绘,构图清晰,图案鲜活、色彩斑斓,等级之最当数“和玺彩绘”,极为难得。
藏书楼是大孔祠堂的重要建筑物之一。该建筑为一幢两层楼房,整个建筑群贴近清代官式构图,细微之处反映了浓郁的地方风格,青砖、筒瓦、白灰罩面,飞檐翘壁配饰博脊、合角吻、戗兽、走兽等等,墙体装有成排落地格扇门和槛窗。寝殿内存有孔族中“英雄”孔繁琴荣获的“柳州鲤鱼峰击虎碑记”之圣旨“功德碑”和下马碑各一尊,并陈列着孔氏家族已故先祖列宗之木主牌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孔祠堂被作为学堂使用。1958年祠堂又被改为粮站,叫做“大孔粮站”。改作粮站时,东西两侧厢房的墙曾被推倒。那时藏书楼尚存,旁边是11间门市部和几间仓库。
2006年年底开始,合肥市政府投资对祠堂进行彻底修缮,还陆续恢复山门殿的东西配殿、东庑殿、西寮房、气势宏伟的藏书楼以及整个祠堂的围墙和庭院绿化等,修缮和恢复建筑面积1080平方米。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修复,久违的大孔祠堂终于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而合肥,也正因为大孔祠堂的存在和传承,平添了崇文重教的明朗性格。与今天“科教之城”的别称,可谓相辅相成。

“打夯歌”是大圩本地独有的艺术形式。“打夯歌”原本是旧时农村盖房子打地基、打圩堤时唱的劳动号子,具有调节呼吸、释放压力,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而现在,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打夯歌”不仅走出了大圩,还走进了“江淮情”的晚会现场,成为当地人必看的节目。

大圩的“打夯歌”
不仅仅是“打夯歌”,每到晚上,大圩村民们自编自演的庐剧和威风锣鼓也会准时上演。他们白天在田地里劳作,到了晚上,用自创的艺术表现形式去除疲劳,陶冶情趣。
在圩西村、许贵村、磨滩村,还有舞狮、扭秧歌、健身舞、划旱船、迪斯科等文艺表演,都由当地农民自发表演。
如今,大圩获得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基本形成了“一村一品”的民间文艺发展态势。现有民间文艺队伍十余个,全镇各类演职人员增至几百名。
牛角大圩最华丽的转身
沿着徽州大道,一路向南,便到了位于包河区烟墩街道的牛角大圩。派河犹如一条玉带,从它的身边静静流过。听着派河流淌的水声,几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今,古老圩转身现代农业,那些独有的“圩”印记却依旧深刻隽永。

牛角大圩
历史:狭长的牛角大圩神秘古老
《宋史·叶衡传》中,记载“合肥濒湖圩田四十里”。1803年(嘉庆八年)《合肥县志》亦记载,合肥有圩85个。不论是“四十里”,还是“85个”,神秘古老的牛角大圩身在其中。
牛角大圩建圩几时?无从考究。但是,从地处其腹地的“横城村”或可探究一二。据说,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56年),沿湖百姓大面积筑圩防水、耕种圩田,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丙子年,所以这里当时被称为“丙子埠”。丙子埠地处派河入湖口,水路交通便利、水产交易发达,逐渐形成繁华的水街集市。后来,居民纷纷沿着圩埂建造房屋。圩埂上的这些房屋面朝河道、背靠圩田,仿佛横排的城池一般,“横城村”由此得名。
从丙子埠到横城村一带的圩田,由于地形狭长,仿若牛角,所以被人们称为“牛角大圩”。村里老人说,“横城村”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想来,牛角大圩建圩也有几百年了吧。
随着人口增长、水土流失,派河河道日渐淤塞,巢湖岸线也不断后退。每到梅雨季节,牛角大圩因为地势低洼,雨水排不出去,形成内涝灾害。几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朝出打鱼暮归舟”的生活。
人文:与巢湖流域圩文化有渊源
过去在巢湖和派河文化汇流的牛角大圩,散落着一些圩堡,但后来因战火、自然损毁等原因,逐渐消逝。现在圩区的地貌构造,还有些许踪影。有关于牛角大圩的点点滴滴,都在这里生活的居民中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牛角大圩分为上大圩、中大圩、下大圩。之间分界的来历颇有趣味。上大圩连接岗区,地势比较高,每逢下雨,雨水就会淌到中大圩,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河,雨水沿着河流入派河。于是,以此河流为界,隔成了上大圩和中大圩。久远的故事,让牛角大圩显得更加古老而神秘。
延续:生态园中保留“圩”气息
2008年,牛角大圩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几年建设,作为一个被水簇拥着的田园,如今的牛角大圩早已“脱胎换骨”,成为环巢湖生态示范区的一颗绿色明珠。

欣喜的是,作为巢湖北岸最古老、合肥主城区保留的一块10公里的生态农业区。包河区在牛角大圩生态文化休闲旅游建设中,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将文化融入园区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聘请专业机构,精心设计园区LOGO,并对园区以及园区内的路、桥、水、林、景点等进行命名,赋予其文化内涵,比如“秋季花海”、“金色稻浪”等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使整个园区充满灵气,充满浪漫气息。


在农业生态园游客接待中心安家的“奋进牛”牛角雕塑,也将用无声的方式,展示牛角大圩人“牛”的精神: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垦荒开拓、干劲冲天。

(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