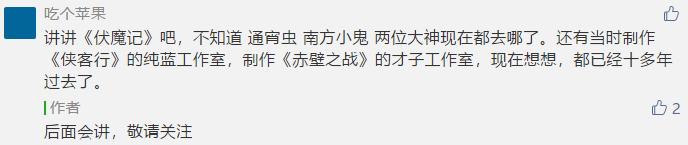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是哪一个?
东非的布隆迪,肯定算是其中一个。它不仅贫穷,更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受人重视的国家之一。
鉴于布隆迪史上的种族冲突现象,国际社会忧心忡忡,担心一场大屠杀将重演于此,即使该国总统表示已经向国际社会允诺和平,但经警方证实,酷刑、强奸以及杀戮仍然存在。言论不当可致杀身之祸,寻求正义之路更是危机四伏。
以下便是一些布隆迪人,一些受害者真实的故事,以及记者肖恩·威廉姆斯的所见所闻。
2017年春天,一个名叫蒂埃里的司机,在一个闷热的周五晚上,走进了他家附近的一间酒吧。
当晚的目击者称,大约晚上9点30分,有三名男子将他驱赶到酒吧外面。而周末整整2天时间里,他的朋友和家人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到了周一,老板发现蒂埃里没有来上班,于是前去探望。
蒂埃里的房子空无一人,房门紧锁。 老板叫来蒂埃里的妹妹席琳,她是住在首都布琼布拉的一个虔诚的修女。 席琳立刻动身,登上了的一辆公共汽车。
三小时的旅程中席琳一直在拨打蒂埃里的电话,却仍旧没有任何回音。她很好奇怎么会有人敢伤害她弟弟,他们家属于图西族,无论是在布隆迪还是在其北部邻国卢旺达,图西族总是血债血偿。
然而布隆迪的暴力冲突总是由政治原因导致的,而非种族原因。
席琳知道蒂埃里并不曾公开支持过该国领导人皮埃尔·恩库伦齐扎,恩库伦齐扎在位12年并且曾公开主张恢复君主制。蒂埃里也并不频频在政治活动中现身。蒂埃里患有精神疾病,原本开放且健谈的性格早已一去不返。 2015年4月,恩库伦齐扎宣布竞选连任第三任期,人们对此坚决抗议却毫无效果,整个国家再次陷入暴力冲突之中。但这一切和蒂埃里没有关系,他常常呆在家里,醉心于修理旧电子产品,这是他最大的爱好。
7月份,政变失败,恩库伦齐扎顺利地赢得了下一任期。他扩充了布隆迪安全机构的权力范围并扶持了一个青年民兵组织——Imbonerakure,其名字用当地语言基隆迪语意为“有远见的人”。政府逮捕了大批示威者,政客以及媒体记者。许多异见人士失踪,即使有些人侥幸被释放,身上也被刻上了侮辱性的纹身。
席琳知道蒂埃里在清醒的时候绝不会多言。但是她担心在喝了几杯啤酒之后,蒂埃里会不小心说错话。
席琳到了弟弟所在的城市,并拨打弟弟的电话,然而,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这个陌生人告诉席琳,他在他老板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部手机,至于老板的名字,他也不知道。席琳问到他住在哪里,这个陌生人给了席琳一个地址。之后席琳给位于布琼布拉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打电话求助,人权办公室果然查到了这个地址正属于该国情报机构SNR。

2004年加通巴难民营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被严重烧伤
联合国查明了杀害蒂埃里的暴徒身份并告诉了席琳,这些暴徒将蒂埃里驱赶到卢旺达边境,并在那里残忍将他杀害。
联合国的线人称,暴徒们把蒂埃里斩首以后残忍分尸。
席琳的另外两个兄弟闻讯匆忙逃离了该国。
联合国将她的案子转交给了当地维权官员,后者开始不停地给席琳打电话。此外,席琳还接到了许多陌生来电,她认为当地官员已经将她的个人信息泄露给了SNR。
席琳独身一人躲到了一个遥远的城市。杀死蒂埃里的暴徒们可能藏在任何角落里,她甚至无法在人群中辨别他们。这些暴徒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席琳,她必须离开这里逃命。一旦被暴徒发现,没人会为她伸出援手,被杀害后也不会有人替她伸张正义。
布隆迪这个国家,难道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么?
当然不是。
1922年,比利时从德国殖民者手中接管了布隆迪和卢旺达并在布琼布拉(Bujumbura)建设起了布隆迪现在的首都,彼时这里建立了许多艺术街区和棕榈林立的林荫大道。众多游客以及西方国家的退休外交官来到这里,这些人在布琼布拉的海滩上放浪形骸,夜不归宿。
如今的布琼布拉仍旧是一块自由放任之地,仍然拥有许多法国咖啡馆和露天酒吧,当地年轻人在那里为英超联赛的足球明星们大声呼喊。但是现如今这里的万人坑数量都要比观光游客的数量多。当我在当地的布隆迪大使馆申请签证时,那里的员工大吃一惊。她们去到一间尘封的屋子里,带回来一本落满灰尘的账本,并把灰尘吹得干干净净后开始为我办理手续。
在去年11月的一个傍晚,我到达了布琼布拉的机场。 在乘坐公交车前往酒店的十五分钟路途中,我见证了这个国家的满目疮痍:被砸坏的NGO广告牌;四处都是燃烧的垃圾;被炮轰过后的破烂房屋;平板车上躺着的年轻人衣衫褴褛。半个世纪以来,这些景象没有丝毫改变。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布隆迪实行君主专制。作为国家的代表,国王不分种族。妓女多由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农民组成,这两个群体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种族间的观念也以种姓作为基础。富有的胡图族可能凭借其财富或社会地位而成为图西族,反之亦然。
比利时人到来以后却加深了这两个种族之间的矛盾。比利时所谓的科学家们测量了当地人民的头骨和鼻梁宽度,图西族只占人口数量的百分之十五且皮肤相对更加白皙,于是比利时殖民者们宣布图西族为统治阶级,而胡图族却因鼻梁宽大,皮肤黝黑而被殖民者划分到农奴阶级。
在刚才的故事里,席琳是我使用的化名。如果该国政府知道了她的真名,她很有可能会被逮捕,受尽酷刑,并被强奸、杀害。我们在布琼布拉一个神学院里见了面。她是一个纤细苗条,讲话时轻声细语的女人。
在谈论到蒂埃里受害时,她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
席琳后来成功离开了蒂埃里所在的城市。她甚至没有机会去亲手埋葬她的兄弟,“即使我非常思念我的弟弟,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在我的旅途中,还遇到了的另一个和席琳有相似经历的人,他告诉我,军队拒绝释放受害者的遗体,即使在葬礼上也要去恐吓受害者的家属。

布隆迪公共安全部长阿兰·纪尧姆·本尼奥尼(Alain Guillaume Bunyoni)参观了Ru
2014年,三名意大利修女在距离席琳家不远的修道院里被残忍杀害。凶手强奸了其中两名妇女,并将其割喉,将第三名妇女斩首。
布琼布拉电台的非洲广播电台以“无声者之声”为座右铭,播出了一名情报人员的供词。特工说,他之所以成为谋杀修女的帮凶,是因为他看到了民兵武装的存在,而且就在刚果边境附近的一个前教区。
席琳大约30年前出生在南部的Bururi省,她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像90%的布隆迪人一样,她的父母在这片土地上以耕种为生,古老的布隆迪人认为这片森林是人间前往天堂的入口。她告诉我,蒂埃里的死给她的父母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甚至无处寻求慰藉,因为他们的许多朋友早在2015年就已经被相继被残忍杀害了。
席琳向我详细介绍了蒂埃里的死,但是她自己拒绝谈论宗教,种族屠杀或政府问题。她告诉我,这些都是“政治性的”,而且她早就学会了不讨论政治。
我在布隆迪遇到的独裁统治受害者中没有一个允许我公布他们的名字。通过手机,网络和闭路电视,总统恩库伦齐扎和他的执政党密切地注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恩库伦齐扎在2010年成立了Imbonerakure这个民兵组织,以帮助压制当年大选中的反对派。时至今日,这些民兵已经无处不在。
日落时分,成群的Imbonerakure涌向街头,竖立临时路障,随意拦下过路车辆。一位外交官告诉我,这营造了一种“阴险,令人不安的气氛”。 “很快,这个所谓的民兵组织,就要变成没有一点问责制,没有任何透明度的国家安全机构分支。”
我会被监视吗?答案简直不言而喻。
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两个男人出现在我布琼布拉市那间破旧不堪的小旅馆门口,穿着一身制服和便衣。到我退房时,人数多得已经可以参加一场足球比赛了。
人权监察员恩登德扎自2015年以来已记录了62起失踪案和89起谋杀案。自从蒂埃里被谋杀后,这些数据还在不断攀升。
许多人已经放弃了伸张正义。 有一位受害者的兄弟告诉我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得了病,那么你就必须治愈它,但是我对我的国家已经无能为力了,任何办法现在都是毫无意义的。”

2004年8月14日,加通巴难民营大屠杀的受害者
执政党也摧毁了布隆迪的媒体。许多人逃到卢旺达,卢旺达的独裁者对此表示反对。
那些留下来的人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作家瓦列里·穆科告诉我,一群流亡的记者于2015年成立了因扎姆广播电台来和独裁者进行对抗。
在布隆迪,每个和我交谈的人,都认为该国正在向种族分化方向退缩。 2017年4月,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视频显示,卢旺达边境附近一个村庄恩特加的100多名民兵,鼓掌并高喊要让“对手怀孕,以便他们生下民兵的孩子”。
我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遇到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布隆迪的族裔紧张局势与黎巴嫩的宗教仇恨很相似,只有在政治体制失败时,这种仇恨才会突显出来。
民兵们渐渐不再受独裁者的控制。布隆迪难民即使在国境外也受到他们的恐吓,并有传闻说民兵组织在肯尼亚将年轻妇女贩卖为性奴隶。妇女维权人士苏珊娜对我说,民兵组织成员认为强奸是一种“战争武器”。
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安德莱赫特地区会面,那里有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布隆迪人。苏珊在那里给我讲述了一些惨绝人寰的真实案例。一名54岁的女人甚至不记得在难民营中有多少民兵强奸了她。还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妇女被一名警察强奸,然后用步枪枪托殴打,并在三天后谋杀了她的丈夫。 2016年,七名警察强奸了一个三岁女孩;当她父亲走进去阻止他们时,这些警察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父亲。
自2015年以来,苏珊娜已收到40多个此类案件。“我们必须战斗,”她擦干了自己的眼泪, “我训练自己要学会坚强,如果我不去讲述她们的故事,那么这些事情将永远不为人所知。”她担心民兵们会在比利时找到她,所以整晚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在混乱中,总统恩库伦齐扎的独裁统治愈演愈烈。 2016年,为防止叛乱,他甚至禁止在布琼布拉骑摩托车。 2017年,他未经政府批准便禁止妇女打鼓,即使打鼓是一种民族传统,他也依旧不为所动。
去年3月,54岁的总统被命名为“永恒的最高准则”。

布隆迪现任总统恩库伦齐扎
不过,这位独裁总统在非洲大陆还算不上最顶尖的。即使他可以统治布隆迪直到2034年,在执政时间的排行榜上,他也挤不进非洲区的前五名:要知道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恩格玛·姆巴索戈执政已有整整40年了。
变成“永恒最高准则”不久以后,恩库伦齐扎便宣布他不会参加2020年的下届总统大选。
但没有什么人觉得他这是在放弃控制权。为了能采访到总统来考证这一事实,我做了数十次努力,却每次都无功而返。
后来,在2018年,布隆迪下令关闭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它要求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其国家银行存入资金,并移交其布隆迪雇员的种族记录。 “对我们来说,情况真的非常危险。”无国界律师执行董事范库塞姆告诉我。 “您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以及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当恩库伦齐扎宣布将首都从布琼布拉迁至吉特加时, 范库塞姆的员工离开了布隆迪这个国家。俄罗斯雇佣军现在捍卫着布隆迪的经济利益,并训练布隆迪的军队。
从许多方面看,2015年后的布隆迪更像是中世纪的封建领地,而非一个主权国家。而且随着其领导人更醉心于滥用权力,情况可能会迅速恶化。
今年3月,警察逮捕了3名少女,原因是她们在教科书上乱写总统的形象。 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对总统进行个人崇拜。而是总需要人们自己证明他们对党的忠诚。
近年来,在布隆迪的土壤下发现了稀土金属矿脉。但是因为政局动荡,除了仅剩的一家私营外国公司以外,其他公司均已倒闭。
甚至咖啡产业,这个布隆迪的摇钱树,一年的收入也比大多数英国中型企业还低。在一些地区,食物和汽油等基础生活用品正变得越来越难找到。制裁可能使本已贫穷不堪的布隆迪人遭受更严重的打击。一位联合国官员说:“人民非常贫穷。” “情况已经糟的不能再糟了。”
如今,只有20个国家在布隆迪设有使馆。恩库伦齐扎威胁大使馆以及国际社会,为区域稳定而放弃人权的诉求。一位西方外交官告诉我:“他们的所作所为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而且,如果回顾过去的一年左右,他们似乎越来越没有底线。”
布隆迪的邻国也希望布隆迪的政局能够稳定下来,这样能够让大约40万名难民回到他们的祖国。西方外交官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独裁者的举动,一位前政府官员解释说:“相当数量的有罪不罚现象仍旧存在。这使国际社会感到非常沮丧。”

逃难到邻国刚果(民主)的布隆迪难民
更让人沮丧的事,这里发生的一切似乎无人问津。
因为布隆迪穷,这里没有石油,它不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其移民者也没有登陆过欧洲海岸。这些原因可能会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但是酷刑,强奸和随意谋杀却不能。国际危机组织的蒂埃里·维库隆更简洁地总结道:“他们对此毫不在乎。”
席琳并没有停止将谋害蒂埃里的杀手绳之以法的战斗,虽然她知道获胜的机会很渺茫。人们仍然用匿名号码拨打她的电话,告诉她别查了。 4月份有人告诉她,他们看了蒂埃里被杀害的视频。她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她觉得,这是一种威胁。
蒂埃里的双胞胎兄弟乔纳森已经完全放弃了。蒂埃里被谋杀六个月后的一个早晨,乔纳森到一家商店购买手机充值卡。突然,警车包围了他。警察将他带到最近的情报机构SNR办公室。特工大声训斥他,威吓他不要向别人提及他兄弟的死。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他们释放了乔纳森。但那段经历仍然使他感到恐惧。 “这段恐怖的经历,它就在这里。”他告诉我, “我决定离开我的国家。”

警察国家,是布隆迪日常生活的常态。
现在,乔纳森住在南非。他很穷,几乎不会说英语。离开布隆迪之前,他正在布隆迪大学学习民权。 “我很困惑。我的项目不见了,”他说。 “一切都停止了。我不知道我是谁。”
乔纳森一直担心着席琳。他认识那几位被杀害的意大利修女,并且尽管皮埃尔·恩库伦齐扎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宗教领袖们仍然免不了被他所杀害。 “她可能顷刻之间就被这些独裁者夺走生命。”
席琳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当我问到她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以及她每天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时,她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她说:“现在我正在尝试回到以往的正常生活。”
她透过我们的影子,一直望向阳光下摇曳的树木。她说,那些为布隆迪祈祷和平的人与杀死蒂埃里的人是同一个人。
她回头看着我,说道:“当他们来找我时,我不会选择逃避。”
原文来源:《GQ》杂志
文/肖恩·威廉姆斯
译/潘子明
图/网络
【DAILY MEDIA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