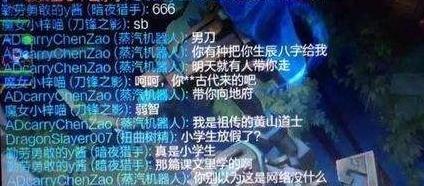导读
很多人认识余华,是从《活着》开始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余华便以“先锋作家”的面貌崭露头角——那个时候的余华,冷酷而乖张,有着激流勇进的新锐气概,是一部分文学青年的偶像。1993年,随着《活着》的出版,余华完成了现实主义的转向,也让他真正从“文学的余华”变成了“大众的余华”。这个时期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拥有先锋作家少见的温情与感伤。进入21世纪,余华在万众期待中来了一个大转身,回归到了充满先锋精神的自己——《兄弟》尚且是小心地试探,而《第七天》则彻底展开了一场无所顾忌的冒险。
文学70年,余华是一个“进行时”。他的创作历程,正反映了文学史上先锋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拉锯、腾挪。“写完这篇文章后,感觉自己和他更近了。”在与编者交流时,本文作者说了这么一句话。或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来说,这个在先锋与现实之间的余华,就是“我们的余华”。

文学的余华:永垂不朽的先锋
余华以前是牙医,专给人拔牙的。据他说,一天八小时,一直对着别人无聊的口腔,拔呀拔呀拔。以前的牙医不比现在吃香,没有经济上的抚慰,余华只觉出了拔牙的无聊。于是,他很轻松地爱上了文化馆的闲差。他开始努力写字,专写小说。因为一次进京改稿,他得偿所愿,去了小城海盐的文化馆。他的日子在闲得发慌中变得丰富起来。那时谁也不会料到,中国当代文学会因为一个半路改行的毛头牙医,多出如此丰厚的谈资。谈资往深了讲,便能变作轰轰烈烈的课题;往浅了说,那就权当下酒的好菜。余华值得大谈特谈,也经得起谈。
从1983年处女作《第一宿舍》发表,到1987年为业界乐道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刊出,余华用了较短的时间,确立了自己先锋作家的江湖地位。在此之前,马原写作十年但并无作品发表,后来史铁生等人奔走推荐,才有了马原的集中爆发。一年之后,余华等更年轻的写作者陆续喷薄而出,他们彼此风格各异,但皆与此前文坛的写实笔调大相径庭。他们的文字放纵,是一种激流勇进的新锐气概,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更浓的血缘关系。他们因“离经叛道”而被批评家称作先锋作家或新潮作家。
余华早期的作品,常被冠以残暴、乖张、冷血,像《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伦理失范,人性不复,读之触目惊心。这是主题研究。余华早期的作品,在结构上多有匠心,像《命中注定》《偶然事件》,故事发生塌陷,不同叙述层彼此吞噬,多条时间线存在叠合。这属于叙述学范畴。要我概括起来,不妨将余华的先锋小说大刀阔斧分两类。一类是写人的局限,或说写万物刍狗。小说无意照抄现实及现实中人,或是制造弗莱所谓反讽型人物,更无神话英雄。余华着迷人的碎片,那些多被世俗生活、秩序世界所遮蔽、掩藏的碎片,碎片又被余华赋予完整的人的皮囊,继而大大方方地为我们展演碎片所具有的能量及其可能的危险。另一类小说写命运造化,或说写天地不仁。余华喜欢强调宿命,人物徒劳地挣扎,断无出路,故而时时给人窒息感。这是一种叙述的专制,是叙述者的英雄主义,先锋作家多少都有叙述至上的英雄情结。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余华写的是一句话。
尺短寸长,在当年的先锋写作里,余华占领高地的是语言。格非文字偏智性,多有雕砌感。苏童、叶兆言写实功力更胜一筹,先锋起来,文字常常摇摆不定。孙甘露则是洋洋洒洒的六朝文气,或者说,是漂漂亮亮的欧美风情。余华的文字自然流泻又有滋有味,是平实出奇迹的那一个,很有点先锋作家里的陶渊明的意思。当然,他们是两类人。马原也有点这意思,但更多了一些哲感的缠绕,表达欲更旺盛。至于洪峰,洪峰是小一号的马原。也是在这里,余华的小说当仁不让是纯然的中国小说,然后才可能是世界的。余华的文字多干练,饶舌也是干练的饶舌,盖因气血充沛、文法清爽,不拘泥、苛求一字一词,所以生趣、可爱,余华的小说让现代白话文写作抵近一个新的高度。
余华同期及往后的创作谈同样颇有看点,像《虚伪的作品》《我能否相信自己》等。我以为最好别太当真,至少不能全然对号入座,不妨视作元小说来看。余华是讲故事的天才。天才的意思,一是看似无意为文而又处处留有余味,文字和思维缺一不可;二是就像那俏佳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放电。
从《活着》开始,余华完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转向,这也是一代先锋作家转型的缩影。但正是当年那些看似病态的、神经质的先锋小说,供养着最健康的、气血最足的余华。先锋小说和先锋精神,必将以其独特的气脉和格调而长存。
大众的余华:《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1993年对余华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年儿子出生,小长篇《活着》出版。这部标志其风格转变的小说,也是迄今余华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同样在1993年,余华开始用电脑写作。从手写到机打,是一个得解放的过程,作家不必担心浪费纸墨和自己的想象。原则上,电脑写作不会产生文字的废墟,写作者可以随时再造一个文字的世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余华写作的变化与创作工具的更替有关。但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余华小说的文字确乎来得越发放松,也更为散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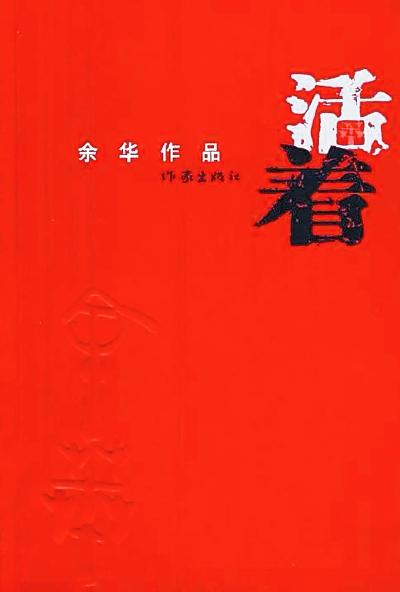
《活着》和余华能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益于次年张艺谋的影视改编。文学和电影两部《活着》,让余华成了大家的余华,也是大家余华。余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早早溢出了文学圈。《活着》的成功,在于其精准地抓住了时代的痛点,以淋淋的血和滚烫的泪,冲击读者同声相应的情感。
《活着》虽然名为活着,但本质是写死。老福贵幸运、乐观的活着的形象,是站在亲友的尸首之上、被硬生生托起来的。这是一种沉重的轻,因为那是不轻不行的重。活着的意义再可贵、再强烈、再深刻,也都是给读者的。福贵是一个死了的人。《活着》里头写了那么多的冤、那么多的怨、那么多的死,但不能否认,较早期而言,余华对自己的人物无疑多了更多的体谅和体恤。这也是为何《活着》能够积攒出余华此前的作品所未有的感伤和温情力量。感伤是一种力量。也是在此基础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可以放到一起来谈。

《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不再写死,他专注于刻画人活着的难度。人生就是一场挥霍和损耗,一如许三观的卖血,无非有度无度。许三观应对人生难题的方式是卖血,血是他的春风,这棵乏人怜爱的草儿想象着借由春风吹又生。反观我们,我们真心甘愿“卖血”吗?我们还有“血”可“卖”吗?我们的“血”有人要吗?当我们无从凭借一盘炒猪肝、二两温黄酒获得精神的还魂时,我们甚至没有“卖血”的权利和条件。我们绝大多数人要比许三观来得精明、来得自尊,所以也来得脆弱。许三观其实是一个有距离感的人物,他以卑微而坚忍的一生为我们警钟长鸣。
关于温情流露,其实在余华的长篇首秀、被其当年自称“当代最伟大的杰作”的《在细雨中呼喊》(原名《细雨与呼喊》)中,已初露端倪——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小说的此处细节,道出主人公孙光林对朋友国庆的婆婆观感的变化。从那时起,余华似乎对人的生命有了更深的体会,或者说,抱有更大也更真诚的兴趣。
同样是1993年的冬天,余华为自己购置了一套组合音响。古典乐登堂入室,正式进驻余华的日常生活。卡拉扬、肖邦,天才的旋律掺杂在一日三餐和吃喝拉撒中,矛盾又和谐。余华的眼光是世界的,矛盾又和谐的眼光。
余华的余华:《兄弟》和《第七天》
2005年《兄弟》上半部出版,故事是《活着》的故事,风格是《许三观卖血记》的延续,多有揶揄,不乏荒诞。次年下半部,彻底放开手脚,捡破烂发迹、倒卖二手洋装暴利、处女选美、遨游太空,从故事到叙述,放浪形骸,任性自在,倒也不失为风格一种。

所谓荒诞,就是幽默得让人心生畏惧,畏惧源自不安的陌生感。一旦超过负荷,便会反过来伤及我们的真诚和庄严,陌生感演变为厌恶。余华以趣味消解丑恶、以修辞技巧调和审丑的冒犯色彩的企图,并不意外地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适。
以《兄弟》为标志,余华似乎是想从大众那里收回自己,跳脱前阶段既有的好感和想象,让大众的余华归位为余华的余华。上半部是试探,下半部是行动。做自己,从一种文化影响的超越性中坠回自我,这种一意孤行需要十足的勇气和信念。读者有读者的不答应,余华有余华的奈若何。
七年后《第七天》面世,余华“做自己”的态度一以贯之。可以说,《第七天》是余华至今最具实验性的一次冒险。亡身未亡魂、阴阳两界、七日创世之喻,他从未如此用心地思考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可塑性和可融合性,叙述者不再肆意挥舞自身的权杖,转而站在人物的立场和界面,试图实现现实逻辑与想象逻辑的完美对接。《第七天》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意义重大。小说写得很理想,于是也容易想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是写得更自私了,哪怕素材是公共的素材。这样一部很自我的小说,余华将自己的爱心、野心、仁爱和愤怒纷纷暴露了出来。因此,《第七天》颇有可观处。

在2014年一次研讨会上,余华声称自己将反思把个人情感嗜好当真理的问题。这是他从儿子那里获得的启发。对于一个具备反思能力的人,我们自不必担心,他能否从任何人身上获得突如其来或循序渐进的启发。
回过头看,那篇让余华一炮而红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远行的男孩感觉公路的高处总在诱惑着他,“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到最后,“我”钻进那辆跟自己一样遍体鳞伤的汽车,在那一刻,“我”认定这便是自己苦苦寻找的旅店。他不得不对此满意,因为他别无选择。余华无疑比这个小孩来得幸运,似乎总有旅店在前方等候着他,等候这个一直在路上的男孩、老男孩。但与此同时,余华的失落也绝不会比这个男孩来得少——只要还有路,高处便始终诱惑着上路的人。
基于此,基于彼,基于所有的过往,没有理由不期待余华接下来的写作之旅。他或许能够找到那座自己心仪已久的旅店,又或者,他已将旅店放下,找到了更值得珍视的东西。那是余华的,也是中国文学的。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梁豪
监制:尹文胜
编辑:杨萌
流程编辑: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