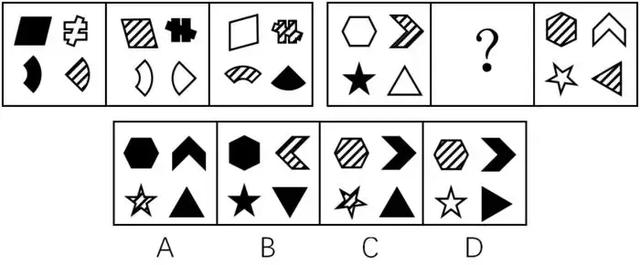编者按:张君劢是一名学贯中西、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哲人,也是“新儒家”八大家之一。《论王阳明》包括《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比较中日阳明学》两篇。前篇原著为英文,是对王阳明学术及生平的简短而通俗的介绍性小论;后篇是张君劢用中文写就的一本分析中日两国阳明学研究特色和专长的学术性小作,牟宗三曾赞其为“发前人所未发,抒意深远,其足警惕吾人者甚大,盖非有先生之志愿与识度,莫能道”。本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张君劢对王阳明的推崇和看重,也是大陆首次出版张君劢专门论述王阳明的著作,无论是对阳明学还是张君劢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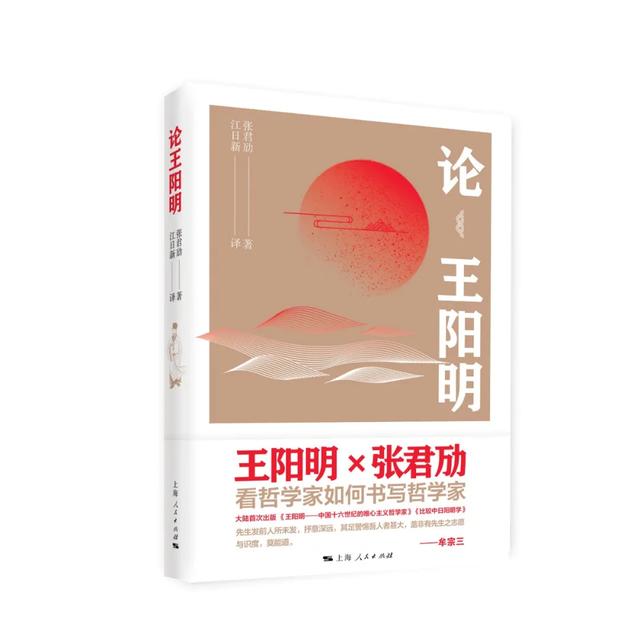
王守仁,俗称王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亦即明宪宗成化八年;11岁时随祖父到北京省父,过金山寺,祖父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阳明从旁赋曰: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龙眠。
客人闻之,大感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不一刻,阳明先生随口赋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同年阳明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说:“唯读书登第耳。”这位小孩子却怀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他的父亲龙山公听了,笑着对他说:“汝欲做圣贤耶!”
及弱冠,他出游居庸三关,于是乎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留月余而回。一日梦谒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庙,赋诗道:
卷甲归来马伏波,
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
六字题文尚不磨。
许多年后,王阳明即在此庙去世,因此这首诗被视为他一生事功及殁亡之处的预言。
阳明先生迎娶夫人诸氏合卺之日,传说他偶闲行入铁柱宫,遇一道士趺坐榻上,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因此对坐忘归,直到次日才被人寻获。
公元1489年,阳明先生携同夫人,由江西返浙江余姚故里,舟行至广信,谒见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后来,为印证“格物”之理,刚好其父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因为朱子曾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可是他始终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此后他随世就辞章之学,希望能通过科第取士的功名。第二年春天,会试时落榜,同考的人有以不第为耻,阳明先生安慰他们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后来,他终于在己未年会试,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时候他很关心边界事,及闻鞑虏猖獗,先生复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
公元1500年,他转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二年疏请告病归越,此时于诗文才名之兴减甚,并以佛道之教为非;于乡里闻说有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喻之,于是僧悟而还家。次年秋,主考山东乡试,九月转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再次年,即公元1505年,始收学生,教以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35岁乃是王阳明一生的大转折点,是时明武宗初临政,宦官刘瑾窃柄,有直官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阳明先生首抗疏救之,以是忤阉宦刘瑾,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王阳明年谱》:武宗正德元年丙寅。,赴谪道中,刘瑾遣人随侦,先生有诗志当时纯良承担之心: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王阳明谪官龙场驿丞,龙场位于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又旧无居所,乃教以范土架木以为居所。时瑾憾无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食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除此之外,阳明先生更致思“格物”“致知”之理。阳明先生学问本据朱子,以物、知二分而无相涉,然自格竹以后,常疑而不决。至此忽中夜(于1508年)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此作共有十三条,并附加一序,具载于王阳明的文集中,王阳明曾思注五经,不久旋弃置之。
谪处龙场,王阳明悟举“知行合一”为其学问宗旨,其后,他的学生徐爱因未会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于是决于阳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知与行分明是两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
徐爱又曰:“古人分知行为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晓否?”阳明先生回答说:“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尝说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一段阳明先生谪居于龙场的师生问答,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其哲学系统的基础。三年后他升任庐陵知县,贬谪结束。
及阉宦刘瑾伏诛后,先生复为朝廷重用,任司要职,然而他仍聚同道讲学,总要其言,则唯“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
正德十一年九月阳明先生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时汀漳各地有巨寇为患,尚书王琼特举先生以治之。治盗之事,阳明先生以为当设县立政以为防,他说:“盖盗贼之患,譬诸病人,兴师征讨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辑者,饮食调摄之道,徒恃政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也。”
当治盗时,先生仍聚诸生三十人,日与讲论《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同年并刊行《朱子晩年定论》一书。
及正德十四年己卯,宁王宸濠叛,阳明先生起义兵。宁王本封于江西南昌,叛,谋拟径袭南京,遂犯北京;其谋若遂,则势力必坐大而危及朝廷矣!为此,阳明先生念两京仓促无备,欲沮挠之,使迟留旬月,于是故意伪作两广机密大牌、备兵部咨、及都御史颜咨,摇乱宸濠心志,果然宸濠疑忌,延迟未发。
及接兵,阳明先生以军谋成功,不及四十天而平宁王之乱。由是先生声名大噪;至此,阳明先生非但为一书生,亦无愧为一能军略的全才。阳明先生虽处征讨宸濠军事,仍与诸生讲论学问不辍。
嘉靖元年壬午,王阳明的父亲龙山公卒,遵古礼居丧三年,当时新皇帝世宗擢先生为南京兵部尚书,但他实仍居丧于家。
武宗正德十五年到世宗嘉靖三年,阳明先生完成甚多论著。正德十五年曾致书罗钦顺(整庵)论《大学》古本之恢复;同年并得王艮为弟子,阳明先生于此事并谓门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无动,今却为斯人动矣。”
十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直下认取知行之合一,后诸生闻谤议先生者日多,因相与论言,先生曰:“诸君且言其故。”有曰:“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
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先生曰:“三者诚皆有之,特吾自知诸君论未及耳!”请问。曰:“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此段话乃阳明自指出其所行唯依据于良知,更不复管他人道是道非。
及居丧期满(1524年,即嘉靖三年甲申),阳明命侍者设席碧霞池(天泉桥)宴诸弟子,在侍门人有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有“铿铿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
及嘉靖六年丁亥九月初八日,钱德洪偕王畿访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其所论辩主题则为阳明著名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此论辩先是由王畿致疑曰:“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曰:“何如?”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工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
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晩可同进请问。”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曀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需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畿请问。
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一论辩甚为重要,盖日后阳明后学有以“无善无恶”直视为阳明学问的根本所在,此一误解终导致王阳明日趋偏激堕落。
由于皇帝之命令,阳明受命征广西思田叛贼,至思田,阳明布告叛贼,略谓自解散归者不究前过,因此叛事迅速即得平靖;以之阳明再于思田之地兴设学校,教育民众。
同年(即嘉靖七年,1528年),阳明患赤痢症,并为炎毒所困,养病中,阳明拜谒马伏波庙。马伏波即东汉征服安南的名将,其庙在广西南宁。阳明先生于15岁时尝梦谒伏波将军庙,至是乃亲拜其庙下,宛如在梦中,谓兹行殆非偶然,因识二诗,其中一首如下:
四十年前梦里诗,
此行天定岂人为,
徂征敢倚风云阵,
所过如同时雨师。
尚喜远人知向望,
却惭无术救疮痍,
从来胜算归廊庙,
耻说干戈定四夷。
阳明先生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乙卯(即1529年1月9日),灵柩运回故里安葬。然阳明先生之思想,在晩明一段期间曾引起学者的广大反应,并形成一支极具激发力的思想学派。
直觉主义研究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广泛地讨论了两个主要问题:“心即理”及“致良知”。这两点构成了中国直觉主义的基础,为了解王阳明在这个主题上的思想系统,我们首先必须讨论孟子。
孟子是直觉主义运动的奠定者,他宣称人这种理性动物天生具有四端:仁、义、礼、智。仁字是由“二”“人”合成的,是故“仁”这一端乃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义”之端则使人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礼”则是由仪节生发出来的礼仪逊让。“智”之端则是能知特殊事物是什么,以及分别物与物之间的能力。
此四端是价值判断的范畴。四端在孩提之时未得完全发展,但当它们得到发展之后,人们就能在这四端的基础上形成道德或认知上的判断。孟子即以底下孺子坠井而引起人们救援的心理反应的例子,说明其关于人天生即具有四端的理论: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观察到救援的反应是自发的,并没有其他的目的,于是他进一步说明,上举的四端是内在的且须要人加以发展的: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
虽然孟子极强调人天生而有的四端,但他也一样很清楚,人的个性亦相当依赖于教养和培育,也就是说相当依赖于外在的因素。底下一段话即说明这一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第七章)
底下这段文字指出了孟子直觉知识的理论: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第十五章)
孟子对是非善恶的本质也极为强调,根据他的看法,这也是自明的。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十章)
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道德义务——亦即是非的讨论,都是集中于讨论每一个人在其生命阶段上的道德责任。因此,比起西洋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快乐等似乎更具理论性、客观性的说法更接近于人。孟子下面接着说: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由是根据孟子的看法,是非善恶对于人类来讲是自明的,人应该小心维护,不使放失,他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何以只能选择义之一途: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噱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第十章)
我们认为,孟子的直觉理是建立在以下几个因素上:人之四端、心共同的认定或自治的能力。因此,直觉与直接的解悟不同,因为后者是人所认识到且被人把握着的,因此很清楚的只是整个历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孟子之后,中国哲学便走到一个停滞不进的阶段了,佛教便在这个有利的机会下流行于全中国。佛教梵文经典的翻译是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进中国以后的主要工作。在佛教深入中国人心灵之前已有许多世纪过去了。禅宗始于第五世纪,它主张众生皆具有佛性。
很明显地,佛教这一主张与孟子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主张相似。在禅宗第六祖惠能的卓越倡导下,人性天生为善的观点得到了支持。孟子的理论在这种刺激下得到了复苏,于是儒学和佛教以同样的方向并同着进行发展。惠能关于直觉知识的看法引起禅宗僧侣的回应,经由禅宗僧侣惠能的直觉学说散布到儒家学者间去了。
于此简略说明禅宗的发展史当是有所裨益的。禅宗是菩提达摩所创立的,他大约是在公元470年到475年间来到中国,他为中国人带来了这样的信息: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契嵩:《传法正宗记》)
达摩的一位徒弟慧可向他问道:“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汝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
上面这种表面上看来深奥难解的说教告诉我们:心是在个人自身中,只有个人自己才能知道,他人是无法为他做任何事的。菩提达摩的教导亦是个人应该自宁静其心。心的发用是自知自明的,它从来无法在外物中展现,也无法被客观地或逻辑地证明。
当这一宗派发生了影响而凌越于其他佛教宗派之上时,便对儒者造成了刺激的作用,儒者于是开始阅读禅宗的语录,并且也似乎表现出喜欢阅读这些著作。唐朝(618—907)大部分的政治家、学者及诗人都与禅僧有很密切的接触。韩愈(768—824)这位古文大家曾上书宪宗皇帝谏迎佛骨,并且他还写了《原道》这篇文章。在《原道》这篇文章中他为儒家肯定尘世生活的态度作了辩护。
但韩愈自己却有一位禅僧朋友,亦即大颠和尚。他曾写信给朋友说明与大颠友善的经过,“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余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韩愈:《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简书》。)
韩愈虽然是位反对佛教的人,但显然却也欣赏禅僧对于世界的态度。韩愈之后,诗人白居易一样也与禅僧友善,他曾作过八首诗偈阐发禅僧凝公的心学理论:
1. 观偈
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之,则辨真妄。
2. 觉偈
惟真常在,为妄所蒙,真妄苟辨,觉生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3. 定偈
真若不灭,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
4. 慧偈
慧之以定,定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
5. 明偈
定慧相合,合而后明,照彼万物,物无遁形,如大圆镜,有应无情。
6. 通偈
慧至乃明,明则不昧,明至乃通,通则无碍,无碍者何?变化自在。
7. 济偈
通力不常,应念而变,变相非有,随求而见,是大慈悲,以一济万。
8. 舍偈
众苦既济,大悲亦舍,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渡者。
始创于菩提达摩的中国禅宗,在宋朝(960—1279)儒家重振之前的五代时期极为活跃。
禅宗的基本原则是(1)以心为主人;(2)肯定由心得到的直接了悟。这两个原则对新儒学的复兴——特别是宋朝时心学派的兴起——极有贡献。
宋儒对这种思考方式的态度并不一致。宋儒分为两派:(1)心学派,此派相信本心的恢复;以及(2)理学派,这派相信可以从外界求得许多知识。陆九渊(象山,1139—1193)及杨简(1140—1226)是心学派的代表人物;而程颐(伊川,1033—1107)、朱熹及其弟子后学则声称他们相信“理学”。而他们的共同面貌是认为正确的知识来自心。
陆象山是宋朝心学派的开山祖师。王阳明(1472—1529)则在明代(1368—1644)承继陆氏的学说。下面是他们之贡献的一个简要叙述。
陆象山经常要求人返求本心,他的哲学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原则上:
其一,先立其本或先立其大。陆象山这一原则是学自孟子,其中包含了心的认知以及感官欲望的去除。陆象山赞同孟子的主张,认为人们若顺从心的权威,那么便有能力发现何者对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人性天生就是成全完善的。
其二,去欲。虽然人本身是成全完善的,但他却经常行事乖错,这是为什么呢?这乃是因为人经常受到感官、欲望及激情的刺激;或者乃是说人经常由于受爱恶的影响而变得有偏见。
其三,不把道问学工夫看得最重要。陆象山确信心的优先性。基于这种信念,他轻视心应该从外面世界学习更多知识这种看法。
在陆象山写给其学生曾宅之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自己的观点说:
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所病于吾友者,正谓此理不明,内无所主,一向萦绊于浮论虚说,终日只依借外说以为主,天之所与我者,反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返,惑而不解。
这封信很明显这是一封指责朱熹这位拥护理学者的信。
于此我们将看到,陆象山与其门人杨简的谈论中,如何将禅宗的方法借用进来,阐明心自知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道理。杨简本来是富阳主簿,后归入陆象山门下,杨简曾问陆象山说:“如何是本心?”陆象山乃举孟子的话告诉他:“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
杨简回答说:“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杨简这个问题一直提了好几遍,但陆象山仍一直是同样的答复,而杨简也一直不能懂得其道理。
由于杨简是富阳主簿,适有卖扇子的来诉讼,杨简判定其是非曲直后,又向陆象山提出同样的问题。陆象山于是说:“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忠本心。”于是杨简恍然大悟,更加确信心的自知自明。
现在我们要谈谈心学在明代的发展。起初王阳明很难了解儒家哲学,尤其对“格物”的道理无法了解,朱子认为万物背后都有某些“理”在,我们必须经由研究从而发现这些道理。王阳明于是将朱子的理论拿来实验,格其家庭园中的竹子以求其理。
经过许多次的苦思反省后,王阳明终无所得,并且还因为苦思用力太过而生病。王阳明于是得出结论,认为他极力苦求学习正是他无法致得其知的原因。于是王阳明想到,当事物与其理相互分离时,它们如何能够在一个人的心中同而为一呢?由于他深受到这种问题的逼迫,于是有一小段时间放弃了格物的想法。
当王阳明38岁时,他遭受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当驿丞。这期间他忽然顿悟了格物的意义,当时由于他太高兴了,出声太大,使得在房中睡觉的人也被吵醒起来。他的了解乃是建立在一种所谓物只不过是心之所对的观念上。当事物要被人所认识,它必须经由人的意识;当然事物的原理也就因此而能被人的心发现。于是王阳明接着考察古代经典,并在这些经典中找到了表示这道理的话,证明其新发现与古经典相符若契。(按此即是指阳明于龙场顿悟后著《五经臆说》一事。)从这时候起,他揭橥“心即理”,亦即知为实在之核心的理论。
以下一点显示出王阳明是如何定义其基本观念,并且也显示出他的思想结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
这一段引文只是其思想的一个核心部分,若要彻底地了解王阳明的思想,我们还有待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王阳明曾经说过: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王阳明论点中的一些要点如下:由于动植物能够养人,药石能够治疗人的疾病,因此在生物世界—物理世界与人类两方面之间必然要有精神上一气相通之处,因此宇宙核心中存有灵觉这一点是王阳明的根本信念。在这一核心处,人紧密地与在上的超自然世界和在下的自然世界连在一起。宇宙即是以人为其中心的一个整体。
底下一段王阳明与其学生的对话更详细地告诉我们他对于宇宙作为整体的看法: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
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
请问。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曰:“人又什么叫作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这一段对话告诉了我们,王阳明是如何来看待这一基本问题。他的意思是说:灵明即是实在,灵明包含两项,其一端是“心”,也就是能知,另一端是“宇宙”,也就是所知。它不但不能只指实体性而不指另一端,也不能单指人类。因此王阳明说: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以上王阳明的意思是说,宇宙的本性依待于心知;并且若是没有人的灵明或心,那么只有一片混沌错乱的知觉而已。由此他说: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王阳明认为良知就像光明而富有能量的太阳;它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它将无上命令具现出来。然而良知(或心)必须要保持纯洁无私,以免使得它在人心中表现得像太阳遭受云朵的遮掩。精灵是实在,然而实在的把握则要依待于一个纯洁无私的心灵。王阳明很喜欢从《中庸》中摘引句子,例如,“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上下察也。”鸢鸟在高空之上飞行,鱼悠游于泽海之中这个现象背后,隐含着许多高妙的隐奥,由此我们很可以理解地明白整个宇宙即是一个整合的整体。
这种将真与善联结在一起的做法,很明白的是良知的定义,也是王阳明希望是他首创出来的一个定义。对于王阳明来说,善与真理之光即是宇宙的真实实在。
【内容简介】
张君劢是一名学贯中西、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的哲人,也是“新儒家”八大家之一。本书包括《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比较中日阳明学》两篇。前篇原著为英文,是对王阳明学术及生平的简短而通俗的介绍性小论;后篇是张君劢用中文写就的一本分析中日两国阳明学研究特色和专长的学术性小作,牟宗三曾赞其为“发前人所未发,抒意深远,其足警惕吾人者甚大,盖非有先生之志愿与识度,莫能道”。本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张君劢对王阳明的推崇和看重,也是大陆首次出版张君劢专门论述王阳明的著作,无论是对阳明学还是张君劢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张君劢(1887-1969),中国近现代学者、哲学家、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张君劢学贯中西,终其一生都在提倡复兴儒学,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代表作有《新儒家思想史》《新儒家哲学史》《明日之中国文化》《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来源:《论王阳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