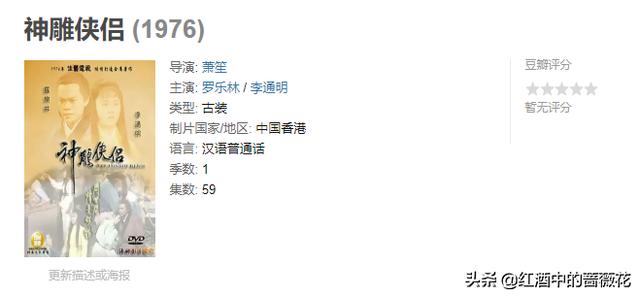雅言即是古代通行大江南北的文言,与俗语、白话相对,这是《论语》中“雅言”二字的本义,也称“正言”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没有任何一种方言是雅言,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雅言的真实身份?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雅言的真实身份
雅言即是古代通行大江南北的文言,与俗语、白话相对,这是《论语》中“雅言”二字的本义,也称“正言”。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没有任何一种方言是雅言。
《辞海》对雅言的解释:“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很明显这个解释是矛盾的,错误的,古时称“共同语”,那意味着现代称雅言,确实,将共同语称为雅言是现代人干的。古人从来不将共同语称作“雅言”,而称作通语,正音,雅音、官话等等。
今天的普通话,大体相当于古代的通语,正音,雅音、官话。通语是四方百姓普遍使用都能听懂的通用语言,实际上就是通行的北方话。雅言则是天下文人的通用语言。举个例子,“司阍”一词的意思是看门人,司阍就是雅言,只有文人能听懂,“看大门的”,就是通语、普通话,老百姓都能听得懂。
明朝开始出现的“官话”一词与普通话相似,自然也与雅言不同,明清官话实际就是指北京话,它更多强调的是语音一面。对外地人来说,你学得了一口标准的京腔,就是学得了标准的官话,不管你会不会之乎者也,识不识字。
官话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明朝谢榛《诗家直说》中:“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甲科”就是明、清朝的进士,谢榛表达的意思是,秀才在家说家常话,一中进士就开始学官话,就是一副北京腔调了。因为能说北京话的外地人通常都是当官的,故有官话之称。谢榛是山东临清人。
然而,对明清时的南方人来说,整个北方话甚至都被认作是官话,语言学上也将北方方言命名为官话方言。
《清稗类钞》载:
“官话为正音,流俗不察,以为必官吏而始有此话。北人之普通语言,颇似官话,非若吴越语言之为古时南蛮駃舌之音也。吴越人乍与北人遇,闻其言,辄以官话目之,敬礼之心,不觉油然而生,此亦奴性表示之一端也。
.......
光绪初叶,吴人周甘卿入都,自清江浦遵陆而上,闻道旁男女之发言类官话,归而语人曰:“北人多智,虽三尺之童,皆操官话,不待学而能也。”
就因会说北方话,南方人对遇到的北方人竟有“敬礼之心”,最后一句更有意思,哪是什么北方人聪明,而是北方人的发音普遍与北京话接近而已,这都是南北方语言差异太大造成的心理错觉,以为北方人都会说官话。过了清江浦(淮安)就是徐州,是非常正宗的北方话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有此感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人不像现在,没去过北京的人,都不知道真正的官话即北京话是什么样的。
对于雅言和通语的区别,可以用《金瓶梅》中西门庆使用的两种语言来区别。
官居五品的西门庆慌躬身施礼道:
“卑职重承教爱,累辱盛仪,日昨又蒙赙礼,蜗居卑陋,犹恐有不到处,万里公祖谅宥,幸甚!”
这是雅言。不是通语,不是普通话。不是官话。
西门庆哭李瓶儿:
“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
这不是雅言,是通语,是普通话。也是官话。
问题中所提到的雅言,主要表达出的是语音的意思,这是现代语言学将雅言与雅音、正音相混而乱用所致。即前面所言,现代语言学对“雅言”的定义有问题。
作为雅言的文言,是历经数千年天下文人广采天下语言约定俗成的,并非完全源自河南话、洛阳话。再换句话说,古代的河南人洛阳人未必会说雅言、懂雅言,比如白居易是河南人,他被称为白话诗人,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讲求通俗易懂,写的诗要让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懂,老太太听不懂的就改。但这丝毫不排斥老太太会说让外地人羡慕的正音、雅音。这和承德滦平的农村老太太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样。
雅言的发音,即是古人学习文言所用的读书音,基本上都是以通行北方的中原语音为准。但魏晋时代的南北分裂,定都南京使得文化中心南移,雅言的音韵掺杂了过多的吴语成份,历代文人都批评前代留下来的韵书吴音太重,这也难免,毕竟韵书主要都是在南方诞生的。雅言的正音在韵书中就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总体上还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其中以文人所看重的中州即河南话元素最多。
韵书都是无声的,很难想象古代中原人具体的发音和音调是什么样子的,但音类和现在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宋朝《广韵》中“孔”的发音是“康董切”,即“康”的声母加“董”的韵母,无论发音和声调都完全和北方话是一致的,都是kǒng, 音调是上声,即三声。当然这里所说的北方话并不是北京话和普通话,因为北京话是北方话中最北边缘的古幽燕汉语方言发展而来的,最不能代表北方话的就是北京话。河南话的“孔”与北京话声调完全不一样,包括山东话也是,在河南话和山东话中,通常都将北京话的三声发成一声,即河南人与山东人发“孔”的音,听起来很像普通话的“空”音。如果你要问宋朝时的河南人发“孔”的音,更像今天的河南人还是北京人发音,当然是更像今天的河南人发音了。
也就是说,你今天所听到的和所说的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孔”的发音,肯定不是宋朝雅言“孔”的发音。原因就是今天河南话和北京话对这个字的发音完全不一样,同时,没有任何理由今天的北京人比河南人更会发河南人祖宗的音。
换句话说,若问哪的方言和古代的济南话最接近,当然是今天的济南话,哪的方言与古代的山东话相近,当然是今天的山东话。问哪的方言与古代的洛阳话最接近,当然是今天的洛阳话,哪的方言与古代的河南话相近,当然是今天的河南话。
古代的洛阳话、河南话作为古汉语的雅音,只有今天的洛阳话、河南话与其最接近。简单的逻辑推出简单的结论:现代洛阳话、河南话”最接近古代的雅言“。
同样,也没有理由说南方人比河南人更会发河南人祖宗的音。说粤语、福州话、宁波话最接近古代雅音,纯属胡说,他们三家彼此互相都听不懂,谁更接近正音,他们自己先辩论一番再说。
有两点可以从逻辑上证明,题主所说的南方话不是古汉语的正音:
1、从孟子的“南蛮鴂舌”开始,到南北朝,到唐朝,宋朝、元朝直到清朝都称南方话为鴂舌鸟语,说明北方话一直都不是鸟语,但今天南方话依然是鸟语,北方话依然不是鸟语。(语言学中的“鸟语”二字不含贬义)
王羲之是山东人,他的儿子们生长在浙江绍兴,被当时人形容说的全是乌鸦般的呀呀声。
唐朝韩愈被贬广东阳山时,写过《送区册序》一文描写当地人的语言:“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文汇报》曾登过一篇名为《汉语:何妨听其自然》的文章,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比如贫富对审美观的影响。在宋代,广东地区经济很落后,在中原人眼里,那里的人丑,话也难听。苏东坡就曾说过广东人‘面似猿,声如鸟’。”(注:文汇报,《汉语:何妨听其自然》,许博渊2005年01月17日)
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惠州,深受语言障碍之苦。跟随他去惠州的儿子苏过为此写了二首反映听不懂惠州方言的诗,收在其《斜川集》 中,有几句曰:“茅茨谁氏居,鸡鸣隔林丘,……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未著绝交书,已叹交游绝;门前空罗雀,巷语纷鴃舌。”苏轼父子来到惠州,尽管左邻右舍“巷语纷鴃舌”,非常热闹,但苏轼父子因不懂“鴃舌”般的惠州方言,无法与惠州父老“相酬”交往,自家门前空可罗雀。
说“杜甫来到现在的泉州基本可以和当地的老人进行交谈”。这直接就是现代语言学的痴人说梦。唐朝诗人刘禹锡《刘宾客文集》云:“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语不通。”刘禹锡,是正宗的河南洛阳人。
今天的福建,一省之内就有五种互相听不懂的国际语言。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在东南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岛国就占了世界语言数量的近四分之一,分别是839种和707种。福建、广东都地处东南亚。有人问,南方话为何那么复杂和多样,就是这个原因。南方各方言一直在往北方话靠拢,被北方话所同化,但依然保持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语音上。
2、第一、东晋时的永嘉南渡,很多西晋的洛阳人移民到南京,硬生生使得本来属吴语的南京话变成了北方话。要说正宗,也是南京话更正宗。南京话和吴语、粤语、闽语明显不同。
第二、南宋时的靖康南渡,很多北宋的开封人移民到杭州,使得本属地道吴语的杭州话有了开封味的汴音,其儿化音这一特色保留到今天的杭州话中,这一特色与吴语、粤语、闽语也明显不同。
这些逻辑很容易理解。那些说更接近古代雅音(即中州音)的南方各方言,凭什么能比有很多河南人聚居的南京话和杭州话更接近呢?
如果说要寻找中古以前雅言的音韵,想听听唐宋朝人说话的音和调,第一目的地无疑是河南。
看一下古人对中原语音及其代表洛阳音的推崇:
[唐]李涪《刊误》:“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宋]寇准《说郛》:“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宋]路德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
[宋]陈鹄《西塘集》:“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
[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
[元]范德机《木天禁-语》:“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惟中原汉语,四方可以通行。”
[元]孔齐《至正直记》:“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辩,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
[明]沈宠绥《弦索辩讹》:“以吴侬之方言,代中州之雅韵,字理乘张,音义径庭,其为周郎赏者谁耶?不揣固陋,以中原韵为楷!”
[明]陈全之《蓬窗目录》:“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
[明]郎锳《七修类稿》:“城中(杭州城内)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明]王伯良《方诸馆曲律·论须识字》:“识字之法,须先习反切。盖四方土音不同,故须本之中州。”
[明]杨文骢《同文铎》:“得中原之正音,去五方之啁杂。”
[清]朴隐子《诗词通韵·序》:“词严声律,韵必中州。盖河洛当九域之中,其音可通于四方耳。”
[清]潘耒《类音·南北音论》:“河洛天地之中,雅音声韵之正。”
[清]罗愚《切字图诀》:“摄以开合口呼,正以中州音。”
[清]阎若璩:“洛阳为天下之中,南北音词,于此取正。”
[清]王德晖《顾误录》:“天下之大,百里殊音,绝少无病之方,往往此笑彼为方言,彼嗤此为土语,……愚窃谓中原实五方之所宗,使之悉归中原音韵,当无僻陋之诮矣。”
[清]张燮承《翻切简可篇·读横直图口诀》:“填图字样皆系按中州韵填入,学者不可因今古音讹、南北音异妄自更改。”
[清]毛先舒《与婿徐华征书》:“汴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
[清]周赟《山门新语》:“夫中国车书一统,而音韵必叶中州。”
自古至清,没有哪位古人说南方的某种方言是雅言正音,而都强调洛阳音、河南话是正音。所谓南方方言是正音的说法,源自于清末以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反满斗士,以革命情绪取代了历史事实,当代南方经济的发展,又为这些说法推波助澜。
补充一点:所谓洛阳音是自古以来的雅言正音,这是语言学家们的一厢情愿。我们知道普通话明确规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韵书产生与三国和魏晋时代,在此之前你在家想学洛阳话也没法学,韵书产生之后,从来也没有任何一本韵书说它的标准音是洛阳音,甚至也没有一本韵书的作者是洛阳人。即使韵书是以洛阳音为标准音,但洛阳音和开封音以及河南其他地区的发音有区别但又很接近,洛阳音与它们的区别在韵书上根本体现不出来,也就是你只看韵书根本学不会洛阳话,除非你有一位洛阳人做老师。以《切韵》的八位作者为例,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所谓的正音,也就是大体差不多的通用的掺杂了南方话的北方话发音而已。
假如你要找找古代不同地域的人说雅言的感觉,你听听蒋介石、毛泽东等领导人所说的以北京话为基础音的国语南腔北调的感觉就知道了。
==========================================
详细补充一点我在写的一本书中的几段内容供参考:
第三点,忽视了古代人学习正音的难度。
即使将单一的洛阳音确定为正音,将其作为标准音写一本韵书,让你自学洛阳音你肯定也学不会,洛阳音和开封音以及河南其他地区的发音和声调有区别但又很接近,洛阳音与它们的区别在韵书上完全体现不出来,只看韵书根本学不会洛阳话,除非你有一位洛阳人做老师。同样,给你一本南京、福州、杭州、长沙、南昌、武汉、济南、郑州、太原、西安的当地方言的韵书,你也学不会。即使运用现代语言学教材的方法,附上有口、舌、鼻、喉发音的解剖图,把这些地方的方言都标成看图说话,照样学不会。不信各位读者可以想象和尝试一下。
清朝大力推行北京官话,最让雍正、乾隆头痛的是闽粤人,其他南方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称“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走南闯北、能模仿古人说话的语言大师章太炎先生,在北京讲课时也需要刘半农等人为其做翻译。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的回忆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那个时候的正音是国语北京音,能够看出,毛泽东这个师范生在长沙并没有学会。
韵书上所谓的正音,一定需要以某地方的实际方言为载体,否则正音都是虚的。因而在现实中,正音在不同时代大多都是以政权所在地的都城口音来体现,毕竟正音的第一大用户是中央政府,都城在南京或北京,你想以河南人的口音作为正音,根本办不到。你上街买根葱,面对的是都城的老百姓而不是河南老百姓。我举个例子,颜之推有个名气也很大的孙子叫颜师古,是唐朝著名的经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生在长安,长在长安,老在长安,颜之推虽然在家训中要求孩子们讲正音,他定的正音《切韵》是洛阳话和金陵话的二合一,读者可以猜想一下,颜师古说的是哪里的话,是金陵话还是洛阳话呢?我想都不是,他说的应该是天子脚下的长安话。本章开篇我就讲了《孟子》中“楚人咻之”的故事,楚人学齐语,尽管还找了齐国人做老师,但众楚人在一边叽喳,就算天天拿鞭子打他,他都学不会。
民国时云集北京的知识分子的语音,可以用鲁迅先生的“南腔北调”来概括。古人的所谓正音大体也只能是这个样子,韵书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认字和作诗,跟老师学正音,老师说成什么样,最多就什么样,主要还是与各地的方音相近。唐朝定都长安290年,云集长安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只能是南腔北调之长安话;北宋定都汴梁近170年,说的则是南腔北调之开封话;明清定都在北京500年,只能是南腔北调之北京话。东晋南北朝定都在建康270年,也只能是南腔北调之建康话。举例来说,宋朝的王安石说的应是江西味的开封话,苏轼说的是四川味的开封话,清朝的林则徐说的则应是福建味的北京话,曾国藩说的是湖南味的北京话。
正音对进过京城的官员文人的影响较大,对远离京城的文人来说较小,例如康有为、梁启超,用雅言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到北京面圣,同样也要靠翻译。
正音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影响就更小了。作为雅音发源地的洛阳,其北面一百公里处的山西,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晋语,南京话被称为南方的雅音,东南一百多公里处的无锡,也是完全不同的吴语。
妻子曾问我,为何古代老百姓不学正音(京城话)。我答:第一、古代没有广播电影电视,没有师范学校,读书识字的人很少,来自京城的人更少,我小时上学,老师是用家乡话来教我们读课文的。第二,学了没用,让老百姓学北京话,给钱吗?
......
郑张尚芳先生说“复杂的是东南这一带,因为这些地方原来住的是少数民族,越族和南蛮,学汉语学得不标准,所以形成方言,比较复杂”,“形成方言,比较复杂”主要不是因为学得不标准,如果是由于学汉语学得不标准而导致南方各地人互相都听不懂,那真是也太不标准太没标准了。“
......
世界语言有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地球上的低纬度地区普遍语言种类多,例如印尼有700多种,巴布亚新几内亚有800多种语言。这种多样性是天生的,是这些地区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各聚落间缺少政治文化和文字的联系而形成的各语言的原始遗存。中国有300种语言,主要集中在南方。南方方言以及壮语、黎族语等各少数民族语言与东南亚语言有一个共同特征,声调特别多。
由此来看,“比较复杂”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原来就比较复杂。南方方言一直处在被北方方言同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彼此听不懂,是因为同化得还不够,南方各方言依然顽强地保留着各自百越语的语言和语音特色。这就是语言传承的力量,是非常值得欣慰的。南方各地方言,都是一代代人流传下来的最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大力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