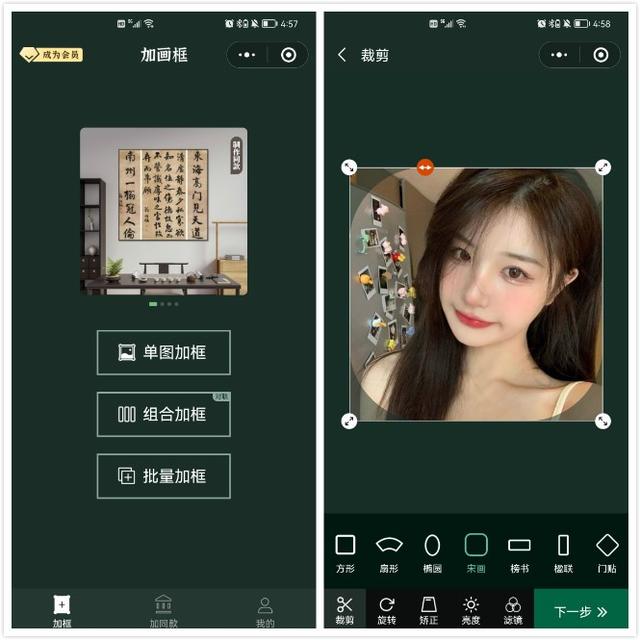花拉拉
文/孙宏文
夏季,是山村孩子们的最好时光,不仅可上山摘果、下河抓鱼、进地偷香瓜、爬树掏鸟掏蛋,还可钻进地里去撸“花拉拉”。
“花拉拉”,是头年秋天落在地上的高粱,经一秋的土埋,经一秋的湿浸,又经一冬的冷冻,落地的高粱粒就变质变异了。当春天种地时,它就和种在地里的种子一起出土。如重茬就和高粱一起生长,如换茬种了玉米,它就在玉米地里长出;如种了矮秧作物的谷子、豇小豆、芝麻、黍子、黄豆或栽了地瓜等,它就“鹤立鸡群”地似标志物般长在地里,在风雨中摇晃。在地里,因是独高显眼,人们在地边、地沿、地头就能看到。

花拉拉比大田的高粱早熟,当高粱刚扬花的时候,花拉拉就熟了。花拉拉熟了的标志是:用手一摇晃它的秸秆,花拉拉穗上的粒子就哗啦啦地往下掉,因这人们就把这作物叫了“花拉拉”。
话说回来,孩子们因何进地去撸花拉拉呢?在那口粮不够吃、生活极其困难的六十年代,撸花拉拉就是为吃、为填饱肚子充饥。花拉拉的米粒外壳硬而有光泽,用碾子破壳后米粒很小,再用簸箕颠出硬壳后,把小小米粒碾成面,用其掺菜贴菜干粮(大饼子)或滚菜团,虽吃着口感涩涩的,但在没粮吃的时日,花拉拉也是饱腹的好东西,故村里孩子们为了一饱就进地去撸花拉拉。
其实,地里的花拉拉并不是很多,上年秋落地的高粱也并不一定都能出,就是出了些花拉拉也经不住孩子们天天进地里去寻、去找、去撒目,有的花拉拉还没怎么熟,用手摇秸秆还不掉粒呢,就被割了头、割了穗,怕是熟透了得不到,所以就提早下了手。
那时,刚上小学的我,也常常随小伙伴进地去找、去撸、去割花拉拉。有次,我在一块很隐蔽的黄豆地里发现了五六棵花拉拉,近前拉穗头一看,粒子还是绿的,用手一掐粒子还没定浆就没采割,想等几天定浆后再来采。可过了几天后,来到地里一看,这几棵未熟花拉拉都被割了头,只有光光的秸秆还长在地里。
花拉拉的穗同普通高粱穗不一样,高粱穗有紧码、散码之分,但花拉拉没有这说道,它的穗同绑笤帚的粘高粱苗子穗一样向下弯垂着,但穗码没有笤帚苗子长、密、粒大粒多,笤帚苗子熟了不掉粒。花拉拉熟透了的时候,经风、经雨都会掉粒,有的就会在风雨中把粒掉光,仅剩了穗上的码。花拉拉,因其熟透好掉粒,所以在撸花拉拉时就格外小心,先是轻轻把秸秆拉弯,把花拉拉的穗头伸进铺了布块的筐里或围扎系在腰间的布兜里,然后一手攥着花拉拉穗头的尾部,一手撸花拉拉穗头,那花拉拉就一粒不剩地落在筐内、落在兜里。会过日子的人,撸了花拉拉后,还顺手把已无粒的穗割下,攒多了也可绑一把笤帚。
在还有生产队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生存,是年年进地撸花拉拉的。
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生产队解体后,粮食年年丰产,人们不再愁吃粮,粮食不缺,村中人也就不再进地撸花拉拉了。
前数日,我又回到乡下老家,到地里转一转、绕一绕、看一看,仍然在谷黍类、豇小豆类的矮棵作物中,看到花拉拉像哨兵一样立在其中,但那已熟透了的花拉拉穗没有了米粒,穗头上的穗码似少女披肩发一样向下弯垂着,并不时地在微风中摇动着。
望着风中摇动的花拉拉,我深信不疑:秋天,只要有落地高粱,地里就还会长出花拉拉。
作者简介:
网名猴哥,实名孙宏文。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新闻媒体从事采编工作,《新华社》《人民日报》均有稿件通发、刊发。退休后,长居南方,亲山近水,笔耕不辍,撰写了百多篇散文作品,部分发表在《辽宁职工报》《朝阳日报》《燕都晨报》《辽西文学》《双塔消息》和《中国乡村》《作家•新视野》《今日作家》《华人文学》等报纸杂志。现为辽宁省朝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村作家首届认证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