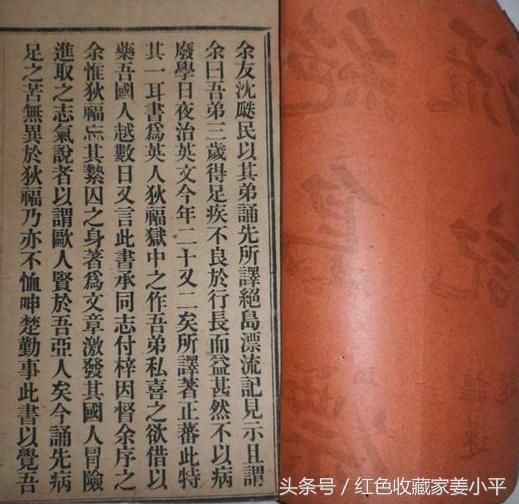2014年,河南上蔡文楼村,图/姜晓明

2004年,河南上蔡文楼村,图/姜晓明
马深义,河南上蔡文楼村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妻子雷妹生下两个得病的孩子:二女儿马茹和3儿子马占潮。2001年,妻子因艾滋病过世,留下马深义,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生活。马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都因卖血染上艾滋病,父亲2007年去世。从2004年起,本刊每年都派出记者访问马深义一家,记录这个豫东平原农家小院的酸甜苦辣。
2015 平凡的一年
文|杨静茹 徐丽宪
马深义两年没出过远门。
他现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骑电动车赶到建筑工地打工。工地离家十多里,中午他在那儿吃大锅饭,下午5点半下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一辆电动车是马深义家今年添的唯一“大件”。
马深义是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农民,1990年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妻子生下两个孩子(注:此前已育有一女):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2001年,妻子因艾滋病过世。
今年是回访的第11个年头,马茹19岁,马占朝16岁。
房子
马深义今年铆足了劲攒钱,他准备明年春天在老房子的地基上盖个新房。
现在家里有一大间堂屋,隔成连通的3个小间,虽然向阳,但低矮破旧,显得阴暗,墙皮顺着墙根往上脱落。
马深义打算把这间屋子拆了,盖成两层小楼,这是一笔将近二十万元的开销。
他想出去打工,“在家里杂事多,有点这事那事就得请假,一个月也就是上二十来天班。”但是孩子离不开他,只得作罢。工地上干活一天120元,都是搬砖砌墙一块一块挣回来的。
马深义还种了五亩地,今年收了不到五千斤玉米,一斤八毛多,卖了四千多块钱。“粮食价格涨不上去,种地根本不赚啥钱,除去成本和功夫钱,不剩下什么了。”
孩子长大了,家里的花费也大了,“我们两三口人的家庭,一年没一万多块钱根本下不来。”
5年前,马深义完全没有盖房的打算,他觉得两个孩子都是艾滋病携带者,活到什么时候都还不知道,盖什么房啊?现在五年平安度过,盖房成了他最大的心事,“(儿子)占朝过了年就17了,房子不给他弄好,找个对象人家也不愿意啊。”
马深义手头攒下一些钱,仍然不够,但是他等不及了,准备跟亲戚朋友借一部分,明年麦收前把房子盖起来。
“我现在身体没啥毛病,但是这个病像一个定时炸弹,不行的情况下就爆炸了,到时候这个事情不给孩子弄好,心里不安宁。”14年前,在这个小院里,马深义亲眼看着妻子发病,她挣扎不动,为了出门输液方便,她就睡在一辆平板车上,临死前苍蝇爬到嘴边,她也没有反应。
孩子
妻子去世后,孩子们是马深义最大的牵挂,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希望。
上个月,马深义带着马茹和马占朝去检查身体,马深义的CD4计数是850,两个孩子都是600。(注:CD4是最重要的免疫细胞,正常人的CD4指数大约为700-1500,CD4低于20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被认为处于发病期。)
“我的身体还可以,我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我要是倒下了,孩子都无依无靠了。”
马占朝从两岁开始由父亲一手抱大,他小时候身体瘦弱,经常生病,马深义怕他见风感冒,经常一整个冬天都不让他出门。 马占朝现在上初二了,成了父亲的骄傲,“他长到我眉毛那么高了,脑袋瓜可聪明,就是贪玩,学习不是很好。”马深义经常教育马占朝要好好学习,“他有这个病身体不好,上好学了能靠头脑赚钱,那样轻松。”
还不到懂得发愁的年纪,马占朝除了在家摆弄手机和拆装小电器,就是跟小伙伴四处跑着玩。今年暑假,马占朝去找在广州打工的姑姑,住到第十天,他开始不高兴也不吃饭,跟姑姑说想爸爸了,要回家。
因为这个病,马深义总觉得对不起孩子,他用宠爱弥补,但是对于两个女儿他仍然觉得亏欠。
马茹现在在县城打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不少人来提亲,她一个也不见。马深义很想问问女儿是不是自己谈了男朋友,但是他张不开口,“没有她妈了,我这个当爹的,不好意思。”
大女儿马妞是这个家里唯一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她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去年过年都没有回来,前几天打电话说今年也不回来了。”
马妞3年前嫁人,跟男人在北京开了个小超市,去年两口子分开了,超市的房子也到期了,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打工。马深义不知道女儿为什么离婚,也不知道她现在做什么工作,“女孩子大了,当父亲的有些事也不知道该咋问。”
他让马妞没事的时候回家看看,马妞回他:你好好的,我回去看啥?“她不愿意回来吧,”马深义对大女儿的事没再多说。
日子
2006年前后,马深义找了个后老伴,她的丈夫艾滋病发病死了,自己也感染了,带着一个男孩。这两年,后老伴都在内蒙当清洁工,腊月里回家过年。“我俩在一块,我的能力也有限,也不能让人家完全帮你啊,得让人家出去挣点钱。”
马深义每天干完活回家,儿子还没有放学,一个人冷锅冷灶,“人的一生啊,最怕半路两个人走一个没一个,有时候我也很苦恼,感觉活得很累。”
没事的时候,马深义除了做家务就是看看电视,他很少到村子里跟街坊邻居聊天,“没有什么聊的啊,人家都是健康人,说是没什么,但是从自己内心来说,感觉跟人家站不到一块儿。”
相比十年前,马深义觉得满足。妻子刚去世的几年,马深义被年幼的孩子拴在家里,没法出门干活,一家四口靠补助和捐款过活,那些年,他身体不好,觉得生活没有指望。“十年多了,我能把3个孩子养活这么大,我感觉很自豪,那时候过的日子就是水火中的日子,不是水就是火,我都不知道我咋熬到现在。”
马深义过得简单,只要房子不漏,被窝不冷,有吃有花。他说现在日常生活都能过得去,日子还是越来越好的。
年底了,今年整个文楼村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村西的主路上了一层柏油,又是平凡的一年。
英雄父亲的 2005
文|徐振江
电话刚一接通,马深义就有些迫不及待地问:喂,你啥时候再过来一趟?
前几天,记者专程去文楼村里找他,他不在家。邻居说,马深义进城了,现在买了个机动三轮,像是做起生意了。
“进城办事,没做啥生意。”马深义说,问他办啥事,他说“私事私事”,就再不说了。
2005年,对于马深义(河南文楼村人,在卖血过程中感染了艾滋病。一家五口,只有一个孩子没染上,妻子已因艾滋病去世。本刊2004年《中国抗艾英雄》专刊,曾大篇幅介绍他的故事)来说,生活没有太多变化。
现在,患艾滋病的两个孩子都在按时吃着药,这是政府免费发放的。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病情有太多的显著变化。小儿子马占槽还是喜欢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蹲在地上哭嚷着要钱,三毛五毛的,然后欢天喜地地跑到代销店里买零食。
二女儿马荣上一年级了,学费是免除了,但是平时买个资料,买个寒、暑假作业本,还是要马深义掏钱。“这孩子学习还不错,得了两次奖状了。都在墙上贴着哩!”说这话的时候,马深义语气里显露出一丝欣慰。
让人稍微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今年新添了一个机动三轮车,二手的,花了马深义1000多块钱。他说,地里的活多,农忙时还得借人家的物件,没有个机动三轮车不行。
今年秋忙的时候,雨水连连,他家种的苞谷(玉米),很多都在地里发霉了。政府每月给每个孩子补贴50块钱,除了这些,这个家庭,并没有多少经济来源。
这个破烂的院落,几乎每隔几天都有人光顾,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每个记者的问题,他都照实情回答。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平静地生活着,秋收了,他下地劳动;想进城了,开着他的机动三轮车就去了;亲戚朋友有翻新房子的,他也去帮上几天忙。
记者问了很多问题之后,还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他说没有,不需要。后来,他偷偷地告诉说:其实他很想要,因为家里没钱。
但犹豫半天,他还是没有开口,“人家跟咱又不熟,也就是客气一下,开口就跟人家要东西,我感觉很不好意思。” 说完,他嘿嘿地笑了。
地里的活都忙完了,村里有的人出去打工了,他没有去,呆在家里,“其实我平时闲着的时候也很想做生意,但没有本钱,家里还有这么一个摊子。根本离不开身!”
他从来不打麻将,没有那个钱,两个有病的孩子已经够他操心的了。
马深义依然喜欢蹲在门口的围墙脚。秋天时,他去集市买了两个小猪娃,这个冬天,那些发霉的玉米将成为它们的主食。
他说,出不了门,家里总要有个活钱吧。他计划着,等猪长成了,卖了,自己再置买点农具,等着明年开春,小麦长起来,地里的活就多了。
英雄父亲的2006
文|马金瑜
午餐
锅里的水开了,白色的蒸气腾上来,水把锅盖冲起来了,马深义一把抓起锅盖,把案板上擀好的面条急急忙忙刨到锅里,刚用筷子搅散,锅里的油又吱吱叫了,辣椒白菜倒进去,锅里还“嗤啦——”响着,大闺女马妞已经放学推着自行车进门了。
马的妻子雷妹去世5年了,不知道啥时候,马妞就长大了,14岁了,知道打扮了,红棉袄,银白丝巾,衬着红扑扑的一张小脸,头发也黑亮亮的,就是眼睛安安静静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眼睛看什么都是亮的,透着好奇和高兴。
马深义翻着锅里的白菜,还没有喊叫,马妞已经拿着筷子站在锅边,轻轻地搅着面条。锅里的面条翻着滚着,雾气罩着她,个子长得真快,快赶上她爸爸了。
“妞,你看,油冒烟了,烫了,才能倒菜,温油炒菜不好吃,快点倒菜,不用怕。”马深义往菜里加着盐巴、十三香粉末。
白菜熟了,再倒进滚了的面条锅里,马深义舀一点尝了尝咸淡,又倒了点香油在里面:“倒上点,面条喝着香。你看着面还中不?你和面少掺点水,面和硬一点,擀出来的面条就没有那么软了。”
“嗯。”马妞看着,点点头,把洗干净的碗拿出来,在一边站着等着舀面。
“赶紧晒我的花,今天出太阳了。”10岁的马茹在大门外面就喊着,6岁的马占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进院子就颠颠地跑去把马茹的那盆花抱出来,放在屋檐下面。
花还是姐姐马妞一个半月前从别的地方挖来的万寿菊,最平常的小黄花,绿叶子,矮矮的,蔫蔫的,在冬日暖黄色的阳光里,成了这个破败的满是泥泞的小院子里最亮眼的物件。
猪在圈里不停地叫,马深义这才想起来,猪都饿一天了。“妞,你先给小茹、占槽装饭,我和猪食。”马深义把和猪食的塑料盆拿出来,一只手上糊着玉米面,一只手拿着凉水瓢,朝厨房喊着。他盘算着,猪喂肥了,过年还能让三个孩子解解馋,好好吃几顿肉,包饺子,吃包子,炖骨头……
小茹一会把塑料袋给花盆戴上,一会又取下来,跑进跑出,鼻涕还挂在上嘴唇上,忙得顾不上擦。占槽跟在马深义后面不停说:“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饼干!”
几把和完猪食,马深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旧的一毛钱,不晓得揣了多长时间,钱磨得毛毛的,占槽拿上跳着走了。
“小茹,你赶紧喝面条,凉了不好吃了。”看见小茹进厨房去拿碗,马深义这才端起碗,呼噜呼噜把面条刨进嘴里。
马妞把妹妹的花搬到太阳光亮亮的地方,看了一会,“爸,我上下午学了。”
占槽掂着几块饼干跑进来,“爸,我要喝茶!”
马深义叹口气,又站起来赶紧倒开水,占槽每天吃村卫生院里发的抗病毒药,可还老拉肚子,老也长不胖。
等再端起饭碗来,面条都凉了,马深义不管那么多,又接着喝了两碗汤面条,不管咋说,他都得吃饱,三个孩子还都指望着他。
“马妞,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吃完饭,马深义也不出门,他爬上厨房的屋顶,这里可以看见文楼村的很多屋顶,可以晒晒太阳,可以望望远处,“我出门干啥呢?跟人家说啥呀?家里这个样子,大家也都有病,都等着那一天……”
隔着两排屋子,住了村里另一家人,男的已经发病死了,女的虽然感染上了,身体还行,什么活都能干,家里的男孩也十六七了,在外面打工。
“那一家……就是我新找的。”马深义指了指那一家的屋檐,望了半天,“我们有时候在一块,我们的小孩也都知道,就是各人的孩子还是各人疼,我还是觉得,孩子跟着谁都没有跟着我好。”
“她身体比我身体好,也比我宽裕,反正是各管各的孩子,各管各的家,我指望不上她。”
马深义还望着,那家的院门一直关着。
家,还是那个破败的样子,堂屋里用黄纸壳做的雷妹的灵位还在那里,最显眼的,是摆在堂屋桌子上的两铁罐奶粉,那还是帮助艾滋孤儿的智行基金的主席杜聪拿来的。最阔气的,是家里的厨房,贴着瓷砖,那是拍纪录片的记者陈为军和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给了他一点钱盖的。
三个孩子和马深义脚上穿的,还是孩子的奶奶做的木头底的棉鞋。可是马深义也照顾不上住在同一个村的老两口,两个老人也都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心里不能想这些,一想就不得劲……”马深义声音小小的。
出去打工,谁要呢?身体也没劲,三个孩子谁管呢?大闺女眼看着就大了,打工,太可惜了,两个小的还每天都要吃药,喝奶粉,病了谁管呢?给谁,都不放心……
“马妞,要是哪天,爸也和你妈妈一样走了,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不能,我不行……”
马妞还太小了,每次炒菜都害怕烫油,案板砌得高,擀面够不上,马深义搬了四块砖头,垫在地上,马妞才能使上劲。晚上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上晚自习,马深义把两个小的哄睡着了,一个人在黑黑的堂屋里坐着,听见自行车声音,赶紧站起来到门外头看看,不是,又坐下。
他不知道马妞来月经没有,也不敢问,孩子大了,他只好在吃饭的时候说,马妞,你少吃点辣椒。马妞就问:“为啥呀?”
“你是女孩子。”
“为啥女孩子要少吃辣椒?”
“吃多了不好,肚子疼。”
“为啥肚子疼?”“……”
“我真想啊,想她的妈妈雷妹还活着,把孩子照顾着,我出去干活,要是她活着,该多好!”马深义叹一口气,搓着一双大手,两只手全生了冻疮,手背红红肿肿的,一会儿还要给孩子们洗衣服。
最长还能活十五年?
记者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曾记载了农民马深义一家从2001年夏至2002年春节的生活。马深义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妞,其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人,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有HIV病毒。
纪录片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片子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雷妹几乎不识字,但听得懂广播。广播里号召“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时,她自然就跟着“奔小康”去了。随着几十元人民币落入口袋,艾滋病首先降临在跟着丈夫卖血的雷妹身上。
纪录片里,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个比她的身体稍长一点的扁箩筐里,呻吟挣扎着,大声喊着:“娘哎,娘……”疼痛过去后,她支撑着身子从那个扁箩筐里爬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长条桌前,战战兢兢地点上一炷香,恳求神明不要再惩罚她,放她一条活路。雷妹的面前,其实并没有神像,只有一面墙皮剥落的破墙和一个又旧又脏的水瓶。
马深义和雷妹的家,除了那个充作神位的长条桌、一个矮脚桌、几个小板凳、一个洗脸盆、两张床,就再没什么了。雷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连床都没有。挣扎得动时,她睡在那个扁箩筐里,挣扎不动时,就被停放在一辆平板车上,苍蝇爬到她的嘴边,她也没有感觉了……
雷妹去世后,陈为军很悲哀:“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茹,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我把马妞供上大学多好,一辈子就变了……”
马深义看着院子里的泥巴,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神已经飘得很远了。
除了地里的麦子,每月有个香港人给他寄500块钱,一家基金会不定期让他去武汉取点钱,马深义花得很省,除了吃药看病和给孩子买奶粉,能省点钱他就攒着,“能给孩子留点钱多好,万一我走了……”
村里其他人问他,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于是马深义每次去外地,就把患病的两个小的带上,“让她们多看看,多看看……”
下午很快放学了,马妞在院子里洗头,小茹和占槽也围上去,“姐,我也要洗。”“姐,我也要香。”
马妞把头发擦干,帮小茹把外面的大棉衣脱了,用手试试水,把手往小茹的头上撩着,热气往上冒着,占槽跑着绕来绕去,木头棉鞋在泥地上发出闷闷的“呱呱”声。
又撕掉一张日历,这一天,是2006年12月11日,马深义把撕下来的一页日历捏在手里,坐在门框上。一到下午,太阳跑得真快,一会儿就没有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茹已经把她的小花放到屋子里暖和去了。
英雄父亲的2007
文|陈磊
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马深义在睡觉。那是2007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三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大冬天的,没什么事,而且最近心里也不大舒服——二妞马茹病了,而且是一病10多天,天天吊水吃药,都不见怎么好转,所以就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想心事。
马深义是河南上蔡文楼村的农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妻子雷妹生下两个得病的孩子:二女儿马茹和三儿子马占潮。
2001年,妻子因艾滋病过世,留下马深义,一个人拉扯着没有艾滋病的大女儿马妞和得病的马茹、马占潮生活。
马深义大家庭里,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都是因卖血染上艾滋病,马深义最担心的是“自己死了,孩子没人托付”。
从2004年起,本刊每年都派出记者访问马深义一家,记录这个豫东平原上农家小院的酸甜苦辣。
现在,冬去春来,又一年过去了,马深义和他的三个孩子在2007年过得好吗?
病魔依旧肆虐
2007年8月,马深义的父亲马毛去世了。
“春节后就开始发病,拉肚子,拉了7个月。”马深义说,“拉得厉害的时候,来不及上厕所,就直接拉在了裤子里。”
在马深义的记忆中,父亲马毛的肝脏不好,还有其他一些老病,所以政府免费发放的针对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吃不下去,只能靠以前的身体撑着。到了今年,终于撑不下去了。
马深义认为,要不是得上艾滋病,65岁的父亲是应该可以再活10年的。“你看,现在农村80多岁的老头活着的多得很呢。”
父亲死后,母亲没有和马深义一起过日子,还是“自己照顾自己”,马深义还要给三个孩子做吃做喝,忙得整天抽不开身。
曾经有一段时间,马深义用购买的三轮摩托拉过一段客,后来因为中午、晚上都要给孩子做饭,太忙,不干了。
最近,二妞马茹又病了,让他心情很烦。
刚开始的时候,马茹是咳嗽,马深义没放在心上,领着女儿到村卫生所吃药打针,他想问题不大,毕竟,马茹吃抗病毒药物已经三年多了,平时发病次数不多。
可事情并不像马深义想象的那么简单。
几天后,马茹还是咳嗽。马深义将女儿带到了上蔡县人民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女儿染上了肺炎,再检查心脏,发现女儿原来心脏也不好,“先天性的”。
记者去的那天晚上,马深义正给女儿吊水,是从村卫生所扎上针后,拿到家吊的。天冷,没有给药水加温的设备,马深义只得将用过的葡萄糖瓶子灌上开水,把针管子缠在上面——这样,注入女儿体内的药水就不那么凉了。
屋角边,放着一个纸箱子,马深义掀开盖子,全是用过的吊针瓶子,马茹“每天要吊四瓶水”。
即便这样,马深义对女儿的病也不敢乐观,“还要再吊一段时间吧”。可孩子还是小,只有10岁,吊的时间一长,她就有些急。
“爸爸,我急,想出去……”在药水滴到第四瓶的时候,马茹就不想继续吊了,苦着脸向马深义小声央求。
“快了、快了,吊完就让你出去玩。”马深义安慰着女儿。
由于有艾滋病,马茹和马占潮都不胖,看起来都比同龄孩子稍微瘦小一些。而且马茹还挑食,害得马深义不得不变着法来哄孩子吃饭。
21日中午,马茹不想吃馍和稀饭了,让马深义给蒸米饭,还嚷嚷着要吃蘑菇,马深义只得去村超市里买了蘑菇来炒。蘑菇水多,一斤多炒了一大盘,三个孩子一分,锅内剩的就不多了。
马占潮上学了
2007年9月,马深义的小儿子马占潮上学了。2001年他母亲雷妹死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就有艾滋病的小男孩还在蹒跚学步。
现在,厨房的门上、门口的柱子上,都已留下了小男孩稚嫩的笔迹,写的都是他自己的名字,他似乎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2007年12月21日上午,马占潮兴冲冲地背着书包放学回来,看到二姐马茹正在吃零食,于是也向马深义叫喊起来:“爸,我也要……”
马深义于是每人给了5粒,马茹没舍得一下子吃完,可马占潮这个有些调皮的小男孩很快吃完后,随即又向马深义伸出了手。
无奈,马深义只好到藏糖的地方给两个孩子又各拿了三颗:“就这三个,饭后上学路上吃,现在吃完就再不给了!”
接过糖,马占潮立即跑到了院子里,偷偷剥开一个糖塞到嘴里。趁着他正开心,记者问:“马占潮,你上午学的什么啊?”
“数学。”马占潮头也不抬。
“那我考考你,9加5等于几?”
半晌,他嘴里迸出一个数:“11!”
“不对,问你姐姐等于几。”
马占潮向马茹奔跑过去,“姐姐,9加5等于几……”
马茹不理他。这让小男孩有些失落,不搭理记者了。
马深义说,马茹和马占潮姐弟俩常斗嘴,比如放学后,看到对方不写作业,两人就开始相互监督,然而,结果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看电视的继续看电视,出去玩的继续出去玩。
“都有病,我也不怎么管他们。”马深义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们活一天,就开开心心地过一天,学习这件事他看得不重。
可已经被纳入教育体系的俩孩子不这么考虑,当记者问起马占潮考试考多少分时,这个小男孩害羞了,他语文和数学都只考了40多分。
和马占潮相比,马茹的成绩好一些,语文50多分,数学90多分,是“班级内的前十名”。马深义曾让马茹停课去吊水,这个要强的孩子死活不同意,是怕耽误功课,一定要等下午放学后才去。吊完水,天已经黑透了。
于是,在马深义堂屋的墙上,一连贴着好几张马茹的三好学生奖状。
马茹和马占潮两个孩子都有艾滋病,在文楼村小学上学后,人们担心他们的同学是否会歧视他们,因为,他们各自所在的班级,只有他们是艾滋病儿童。
“他们有的和我玩,有的不和我玩。”马茹说。
马深义说,是班主任不允许其他同学歧视俩孩子,所以目前的氛围都还好,但也有一次,班里同学看不起马茹,他找到学校,让班主任狠狠训了那几个学生一顿。
艾滋病名人
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以及武汉电视台编导陈为军拍摄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该纪录片获得美国2004年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马深义已经名声在外,成了当地很多人知道的小名人。
出名了,办事也就方便了许多,有时候还能享受一些特殊照顾。比如,给其他艾滋病家庭儿童每人每月补贴65元,成年的艾滋病人每月补助30元,然而给马深义一家则每月多补贴了200元。
还有捐款,在丹麦由律师无国界组织创建的“马深义基金会”已经开始为文楼村的艾滋病孤儿筹集善款。通过媒体的介绍,香港的一个老板每月定期资助马深义500元。
记者去的时候,马深义正为两个月没有收到这个香港老板的捐助而焦虑:“那个老板打了几次电话了,都说是钱打不进我卡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要不我重新办张卡?”
因为出名,地方上的政府领导也大都认识了马深义,比如以前的常务副县长、县委书记,马深义每次见他们“都不会让空手回来”,而县政府的门,马深义“可以随便进”。
2006年春节过后,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亲自到了马深义家里。王来之前,当地政府忙给马深义购置了几件家具。
当王菊梅问到马深义有无困难的时候,他反映了自己的大女儿因鼻息肉需要动手术,经过领导过问,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不然,自己去县医院动手术,要花好几百元呢。”马深义说,出名后,他和孩子看病基本上全免费了。
有一次,马深义凭借和原乡长熟识的关系,替同村的另一位村民讨回了娶媳妇的彩礼钱,这让村民十分感激。
当然,出名后的马深义有时候也感到不愉快,比如今年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再次到上蔡文楼看望患病的村民,可他被当地政府派人看在了屋内,后来让出去也还是有两个人跟着,“怕起哄”。
还有一次,他为艾滋病人的救济面粉被一些干部私分的事到县里上访。结果,到了县信访局,被里面的工作人员顶了回来:又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管这么多干吗?吃饱了出门转转,该干嘛干嘛去!
这让马深义很郁闷,从那以后,如果不是他自己的事他很少再抛头露面了。
“毕竟,我在这个地方生活还要靠当地政府啊。”马深义说。
英雄父亲的 2008
文|陈磊
2008年12月13日,村里有人结婚,远远地就能听到唱戏的声音。这是大喜的日子,马深义带着三个孩子都去了,还喝了点酒,脸红红的。听马深义说,前来为新人庆祝的很多人都得了病,小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但日子特殊,谁也不会说什么。
爱看书的大妮今年初中毕业,没有考高中,她想去驻马店电脑中专学校读书,因为这样能快点毕业出来工作。据说中专毕业生的工资不低,每月能有1千多。但学费很贵,每年要4、5千。
马深义觉得,拼命去借钱也得让她上学。在三个儿女中,老大是唯一身体健康的,老小经常拉肚子,老二则经常感冒,他们两个都在吃药,身子很瘦,但都在长个子。“我希望她读书,这样至少有一个人能走出去,将来能自己生活。”马深义这样安排。
老二也爱读书,墙上贴了不少三好学生奖状,都是学校发给她的。老小则调皮一些,不停伸手跟马深义要零花钱,好去买零食吃。马深义不忍心拒绝,总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今年11月,马深义的父亲去世了。他是当年第一批卖血的人。死之前连续多天低烧不退、拉肚子、什么都吃不进去,到了最后就是昏迷,走时什么都没有说。
父亲的黑白照片放在堂屋,马深义指着照片说,“父亲算是活得时间比较长的了,从得病到死有十八年。”他掐着手指算,觉得自己至少还有十年可以活。
看上去,他的脸色比之前好,人也长胖了一些。他要吃很多药,每顿饭尽量多吃,稍微不舒服就去村里的卫生所打针,希望自己身体能好些。今年的病情检测,他发现自己的病毒携带量减少了,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还有点力气。”
他对记者说,“在这十年里,说不定谁有能力就发明了治疗艾滋病的药,我和两个女儿都可以过下去,”说这话时,他很认真。
英雄父亲的2009
文|陈磊
2009年12月22日,冬至。豫东南的上蔡县文楼,以艾滋病闻名于世的村庄。
早上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马深义醒了,没什么农活要干,家里也没什么事,就那么半睡半醒地迷糊着,不再想那些悲伤的往事了,“徒增思想负担”;也不想以后怎么办了,“那样脑细胞死的多”,只要有吃有喝,“还想什么呢?”
大女儿马妞去年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主要是“学习成绩不好,自己不愿意上了”。“是不是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因素?”
“说不清,可能吧!”
不上学了,呆在家中也不是办法。
秋天的时候,马妞跟着马深义的妹妹到广州打工,进了一家工厂,干了一个多月,“工资1200元都领到手了”。后来,马深义的妹妹看到侄女爱上网,还是用手机上网,管不住,没办法,给马深义打电话:你女儿我管不了,让她回去吧。
就这么着,马妞从广州回家了,把马深义“气得不行”。有什么办法呢,女儿大了,“打不得、骂不得”,这让马深义很感慨,“我们小时候啊,老人说打就打了,哪里还考虑那么多,现在啊……”
中午吃完饭,马妞骑着今年刚买的电动车到县城的大姨家去了,大姨病了,她要代表父亲这边去看看。
电动车是今年春天买的,马深义花了2000多元,有些心疼,前一年秋季收下来的玉米全卖掉了,买了这辆车,“进城方便些”。
遗憾的是,60多岁的老母亲不能享受这个方便了。因为,骑电动车带着母亲上城,身体就不太好的母亲很容易感冒,一病好多天不好——母亲也因卖血患有艾滋病。
母亲要强,没有和马深义一家4口住在一起,独自住。她知道有病的儿子带着3个孩子过得不容易。
大哥的身体也不行了,消化道老是出血,肝脾肿大,饭不能多吃,一吃就胀,这让马深义很担忧。
好消息也有,去检查,发现自己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减少了。马深义说,这大半年来,他自己也吃胖了些,感觉更有了力气。“前几天在刨树根,过年时候用,等过两天准备再刨点,备用。”
10多天前,村里宣布了一个消息,让马深义有些狐疑——不让村民再新建住房了,说是要统一到什么地方去盖,搞新农村,但钱哪里出,马深义不清楚。但是,有一条他听清了——宣布消息后再盖的房屋,拆了是不赔钱的!
马深义不打算盖房,除了大女儿马妞,两个孩子都有病,活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盖什么房啊?!
妻子雷妹死8年多了,马深义也不打算结婚,不是没合适的,是担心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道理他知道。
二女儿马茹已经十二三岁,在农村基本算是懂事了,学习成绩还不错,小儿子马占槽依然调皮,和健康的孩子相比,已经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平时俩孩子感冒多些,不过,这些马深义已经习惯了。他所要做的,是每天监督两个孩子吃抗病毒药物,注意天气的变化,让孩子加减衣服。所以,平时他不大出门。
也有人提议,可以让大女儿来照顾两个弟妹吧,他始终有些不放心——让去西边村口诊所拿个药,大女儿都不愿去,“害羞,还是个孩子呢”。
同龄的很多健康人都到外面打工去了,马深义就这么天天呆在文楼的家里,有时候他会感到憋闷,“我真的很想到你们广州、上海那些大地方去看看,真的,天天被这俩孩子给拴坏了,怎么办呢……”
英雄父亲的 2010
文|陈磊
快过年了,天寒地冻,庄稼不用怎么侍弄,马深义就去刨树根,准备春节时晒晒当柴烧。大冬天,他干得满头大汗。“抗病毒药物一直在吃,身体还不错,(今年)连感冒都没有。”马深义说,他一个人种了5亩多地。
对记者“今年有什么新变化不?”的问题,马深义想了好半天:“好像没什么(变化),就买了个豆浆机,花了399元,算不算?”
12月15日,国内很多地方下了雪。马深义所在的上蔡文楼村天阴着,冷风嗖嗖的,他起得很早,多少年了要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提起做饭,这个年届40的汉子连连抱怨:“想死的心都有了,提起来就烦……”
也难怪,从妻子雷妹死后,快10年了,他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当爹又当妈,生活的风霜早已爬满额头。大女儿马妞虽然不上学了,但毕竟还是个孩子。今年秋天离家时,她连个招呼都没和他打,这让他颇感伤心。
本来,大女儿马妞在离家不远的鞋厂上班,每月一千多元,在马深义看来,“已不算少了”。可女儿爱玩,8点钟下班,有时候到11点她才回家。这让作为父亲的马深义感觉很糟糕:“一个女孩子,哪能这么晚回家?!”
当面责怪了几次,也苦口婆心地劝“我知道她妈死得早,她心里有阴影”。可一切都没大的改观。终于,在一次激烈争吵后,马深义抽了女儿几个嘴巴“心里蛮不是滋味的,我脾气不大好……”
很快,家里不见了女儿的踪影,后来得知是去了郑州。
结果,工作没找到,加上消费贵,每天吃住要几十元,大女儿给他打来电话要钱。这让马深义有些疑虑,“要求打钱的那个卡号怎么不是她名字呢?”
出于谨慎,马深义没有给大女儿寄钱。再过一阵,得到消息,说是到了上海打工,这让他的疑虑更深了:“说没钱,怎么去的上海呢?”
怀疑归怀疑,女儿毕竟是女儿。离家三四个月,马深义给孩子打过两次电话:一次说在上班,噪音大,没讲几句就挂了;第二次,女儿告诉他,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今年春节她不回去了。
“孩子大了不由爷啊!”这句老话,马深义重复了好几遍,有些意兴萧索。好在另外两个孩子让他欣慰“马茹(二女儿)在上六年级,明年上初中,马占槽(三儿子)在三年级,他们俩学习成绩都还可以。”
“马茹眼中有活(方言,懂事、会来事之意),已经学会了做简单饭菜。我不在家,她也能带着马占槽吃吃了,就是现在天冷,不让他们做,怕手冻坏了……”马深义说,“抗病毒的药物,这俩孩子一直在吃。马茹吃胖了,马占槽还是经常拉肚子,喝个豆浆都拉,所以很瘦。”
2011 失妻10年
文|徐丽宪
马深义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吹了一口烟,右手抖了抖烟灰,说,10年来,他一直在快乐地等死。
马深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一名艾滋病患者。10年前,他的妻子雷妹因艾滋病去世。
从此,3个孩子便与马深义相依为命。其中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也是艾滋病患者。
10年过去了,19岁的大女儿马可(化名)在当地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马茹和马占朝也在学校里读到了初一和小学四年级,成绩都还不错。
“雷妹在下面可以安心了。”马深义用脚踩着扔在地上的烟头,淡淡地说。
添了台冰箱
12月8日,阳光有些懒散地洒向马深义家的堂屋。屋里,除了摆在进门靠左手的一台电冰箱和一辆摩托车,无其他贵重物品。
冰箱旁边的木桌上,零零散散堆放着一些西药。马深义说,都是感冒药、“老二和老小经常感冒,家里要经常备着。”
马深义说,摩托车是邻居家的,因为他们一家都出去打工了,就临时让他帮助看看。他偶尔也骑着摩托车上县里走走,他说,这东西老不骑就容易坏。
冰箱是今年7月添置的。马深义说,那时候天气特别热,剩菜在屋里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坏了。“怪可惜的,倒掉又觉得浪费,吃了又坏肚子。”
在孩子们的建议下,马深义跑到上蔡县买回了一台冰箱。这也是10年来,他们家添置的惟一电器。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马深义觉得,他和老二、老小还没有习惯吃冰箱冻过的东西。
家里有冰箱之后,马茹和马占朝特别兴奋,有事没事就把水装在矿泉瓶里放进冰箱,放学回来后再喝。每次喝过之后,他俩都要闹上几天肚子。不仅仅是孩子,马深义喝过冻水之后也是如此。
马深义说,不仅是喝冻水,就是西瓜、香蕉之类的水果,只要在冰箱冻过,他和孩子吃过之后肚子都不舒服。
后来,冰箱除了用来放剩菜剩饭之外,基就没别的用处了。“饭菜拿出来热热,吃了后还好,没什么问题。”马深义说。
大女儿的婚恋烦恼
雷妹去逝时只有9岁的马可,如今已开始谈婚论嫁。
然而,马可的婚姻问题也成了马深义最大的一块心病。“想替她找个好人家啊,不能因为我和她弟弟妹妹把她拖累了。”马深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马可在广州打工,一个月前与老家邻县的一个男孩自由恋爱,但男方父母因为马可家里的情况,最终未同意让男孩与马可继续交往。
对此,马深义常常自责。“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让男方家里知道我和她弟弟妹妹的情况,但这瞒也瞒不住。”马深义叹了口气。
马深义说,马可刚与男孩恋爱时,就打电话跟他说。并没有反对,他对马可说,只要你们合得来就行。末了,他告诉马可,最好通知男孩的父母过来家里看看。
为此,马可和男孩商量,辞掉工厂的工作,于本月初回到各自的家里。
6日,男孩带着父母来到了马可家。马深义便把家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对方。“他们脸色很快就变了,坐着也觉得不怎么自在。”马深义摇了摇头说。
尽管如此,男孩和父母还是留下来,在马深义家里吃了午饭,下午他们就回家了。“吃饭时,大家什么都没说。”
男孩父母最终拒绝了这段少男少女间的感情——吃晚饭前,马深义接到了男孩的电话:“我们一家商量过后,认为你们家的负担太重,不同意继续交往。”
马深义相当来气:“他说了一句不中就算了,便啪地挂了电话。说什么负担重,其实就是对我们家恐惧。”
挂完电话之后,马深义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不过,当他和马可说过此事后,马可倒是安慰起了父亲,“不中就算了,那边交通不方便,都是泥巴路,走个路啥的脚上全是泥巴,我们家门口都是水泥路。”
村里邻居找到马深义,想帮马可说门亲事。但见过面之后,马可嫌男方个子太矮。“这种事,我也不能勉强孩子,一辈子的事啊,由她自己选择。”
不过,马深义还是希望马可尽快找个人家。“毕竟还是要成家的,哎,三里五里的不要紧,只要我百年之后,有个人照顾她就行。”
学会感恩
马深义说,这些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了感恩。“如果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家早就不在了。”
雷妹去世后,马深义只要在外面遇到残疾或乞讨的人,他都会给个一两块的。“要把帮助传递给别人。”马深义望着家里的院子说。马深义说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一般都是绕道而行。
如今,马深义在家种了五亩多地。风调雨顺,收成好时,一年可收四五千斤小麦。农闲时节,马深义也到一些工地上做泥水活。“我不会砌墙,只能做做小工,一天赚个五六十的。”
马深义说,趁自己还活着,多给孩子们攒点粮食。两个患病孩子的未来,是马深义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如果是死在我前面还好,如果是我先死了,那两个孩子怎么办?”马深义一脸的木然。
但是,当马深义见到满墙的23张奖状,他会暂时忘却这些苦痛。“这是两个孩子上学后,得来的全部奖状。”马深义指着墙,回过头对本刊记者说。
雷妹过世时,马茹和马占朝分别为5岁和2岁。
马深义说,雷妹去世这10年,他最大的困难就是照顾孩子。“老大还不需要管太多,老二老小要管。”
他甚至怀疑老小顶多只能活到4岁。“当时大家都说,那么小的孩子得了这种病,最多只能活4年。”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在每天服用抗艾药物的情况下,马茹和马占朝除了会经常感冒之外,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学习成绩都还不错,“都考八九十分的。”马深义露出牙,笑着说。
两个孩子各有特长:马茹的歌唱得特别好,去年底,还获得了学校的歌咏比赛三等奖,而马占朝的特长则在绘画,“画什么像什么,老师说画得特别好。”
马深义说,如果把孩子画的画烧给雷妹看看,她也可安心了。雷妹逝世时,任凭马深义怎么用手抚摸,雷妹的眼睛终究都没能合上。“可能还是担心孩子吧,走了都放不下。”
马深义的2012
文|黄金
大女儿马妞出嫁了,这是马家今年最大的喜事。
马妞是马家惟一健康的孩子,她的父亲和弟妹都是艾滋病患者,母亲雷妹因为艾滋病在11年前已经去世,那年她9岁。去年在广州打工时,马妞谈过一个邻县的男孩,是自由恋爱。后来双双辞工回到老家,男孩父母登门拜访,知道了马家的情况。
那桩婚事最终没成。
在老家,马妞呆不住,又跑去上海打工。今年正月,有媒人来说媒,男方是离文楼村不远的王营村的,比马妞大两岁,今年22,上面还有个姐姐,是家里的小儿子。这回,一开始就讲清楚了马家的情况。今年10月,马妞出嫁了。
“个头差不多1米72,长得还行。”马深义对女婿比较满意,“只要能干活就行。”结婚没多久,女婿就返回北京继续打工,新媳妇马妞则留在婆家。
孩子们
打电话过去,马深义正在家里看电视,广为传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里出现过的那台小电视,如今已能收到四十多个频道。这天是周日,二女儿马茹去邻村大姐家玩了,小儿子马占槽却没有一同去,他说今天阴天,不想出门。
马占槽今年上五年级,刚刚考完试,数学得了99分,第一名。语文虽然没上过90分,也能保持在80分左右。
“今年又长高了!大概有1米45,比去年高了将近五厘米。”马占槽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发育缓慢,在班上一直坐第二排,马深义很担心孩子长不高,“不过还是瘦,不到70斤。”
马茹和马占槽都是从出生就携带艾滋病。天一凉,俩孩子就感冒,只是马占槽感冒容易好,马茹不容易好,马深义也没有办法,只能让女儿多吃点抗病毒药,早一次晚一次,量也增加了。
从读初中开始,马茹就骑自行车上下学,今年已经初二了,晚上要上晚自习,常常8点半之后才能到家。
女孩已经到爱漂亮的年纪,“穿得薄,骑车又冷,”马深义常常唠叨,没什么用。由于生病经常缺课,马茹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在班里排几十名,念不念高中是摆在马深义面前的一道难题。
读高中要去城南中学,在镇上,离马家二三十里,不住校不行。“她愿意就上,不过她自己也还没开始想这个事哩。”马深义说,他最担心的是马茹一个人在学校没人照顾。
愿望
马家种了5亩地,今年都是玉米,收成不错,有五六千斤。除了感冒冲剂自己掏钱买,平时的抗病毒药物国家免费。政府还发补贴,两个孩子都有,一月两百,按季度发,马深义自己也有,一个月一百出头。有个香港的好心人每月都寄钱来,马深义说,一次寄1000块,已经五六年了,也是因为当初被拍了纪录片广为人知的缘故。
今年正月二十四,马深义的大哥去世了,大哥也有艾滋病,身体一直不好。“如今我们家的担子就只我一人扛了。”电话中,一向乐观的马深义有几分消沉。除了收拾地里的庄稼,马深义还要操持家务活。好在孩子已经渐渐大了,里里外外也能搭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占槽说:“我会洗衣服,也会做饭,但是不常做……爸爸能做的我都能做,炒米饭、糯米粥、煎蛋。”基本上,马占槽每天都会去看望奶奶。爷爷因为艾滋病去世已经5年了,留下同样患有艾滋病的奶奶。
马占槽比较内向,每次开口前都要沉默好一会,回答也很短,但说到二姐的时候,话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终于说出,今天之所以没跟二姐马茹一起去大姐家,并不是因为阴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姐姐马茹不怎么搭理弟弟马占槽了。
“我想和好,但她不跟我和好,我也不知道原因。”马占槽说,现在他俩不怎么说话,“有时候心情好了,她会问我几句。”马占槽很苦恼,他也找过大姐帮忙劝劝,但是没有用。
马茹人缘很好,班里朋友也很多,有村里的,也有邻村的,而马占槽大多时候都呆在家里,不怎么出去玩。
除了跟二姐和好,马占槽还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参加运动会。“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不让我参加,但是我想参加,我能跑得过他们。”马占槽认为自己身体很好,“而且爸爸还给我吃了补钙的药。”
还有一个是去北京。很小的时候马占槽去过一次北京,那是在上学之前,直到现在他还能记起天安门广场的样子,但也只有天安门广场。他没见过长城,也没去过故宫。
“跟爸爸提了,却总是推迟,明年、后年。”如今有了个在北京打工的姐夫,似乎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不过也只是想想,他从来没跟姐姐、姐夫提过,“我不好意思。”
父子相依的2013
文|徐丽宪
今年,马深义决定少种些地——3亩,比往年少了2亩。他明显感觉到,身体比以前差了很多。
这种变化在外表看来,就显现在头发和脸上。如今,头上的发丝已黑白参半,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只有些许白发。脸颊和鼻梁上长出来的不规则的硬币大小的红斑,让他失去了的皮肤应有的光泽。
唯一还有点光滑的就是那双嘴唇。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干裂,出门前,他抹了地摊上买的一块钱的唇膏。
两年前,我们谈到死的话题,他很随意,只是说“放不下孩子”。今年,他对这个话题好像有些忌讳,总是有意岔开话题。但依然谈到孩子,“希望把孩子养大,给他办一门亲事。”
2013年,马深义和马占朝父子相依为命。
广东40天
今年过完春节,在村里老乡的带动下,马深义把马占朝交给了后妈照顾,去了东莞石龙镇。“听老乡说,骑摩托车载客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赚两百多块。”
马深义花了四千多块买了一辆摩托车。为了熟悉路,第一天,他就骑着摩托车从汽车站到火车站往返了4趟。
东莞治摩,有一次,马深义的老乡被抓住了。老乡拿出患有艾滋病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没说话,就放了他。但也没走,就站在一旁看着。当有人要搭摩托车的时候,他们就上去阻止,“你们是艾滋病人,不允许载客。”
客人还没听到后半句,就吓跑了。
马深义听说此事,气急败坏,给此前认识的一个记者打了电话,“治摩托车的歧视我们。”
下一次再遇到,治摩办的人就不管马深义和他老乡了。马深义说,记者的电话起作用了,治摩办的人抓住我们,拿出艾滋病证明,就放了我们,可别人被抓起来,连车都没收了。
马深义觉得,艾滋病人也是人,不能歧视。“我们靠着自己的辛苦一分钱一分钱地赚,又没连累政府。”
马深义顺利地跑了40天。
到东莞半个月后,马深义就感觉身体没有以前好,稍吃点荤腥就拉肚子。此时,他还偶尔接到“后伴”的电话,说马占朝在家不怎么听话。“毕竟不是亲妈。”马深义说。
马深义放心不下,把摩托车作价3000块卖了,回到上蔡县文楼村,和儿子马占朝相依为命。
马茹的碎梦
大女儿马可(化名)去年出嫁后,跟着丈夫在北京一个小村里开了间小店,不常回家,偶尔打个电话回去问问好。“嫁出去了,就是别人的人了。”马深义说。
二女儿马茹读到初二,不想再读了。关于读书的问题,她跟马深义好好谈了一次,一句“我实在读不进去”,就让马深义同意了。
马茹和同村女孩一起到了邻县一所中专学美容美发。马深义说,这也是马茹的梦想,学成后,回上蔡开个理发店。
到学校后不久,校方要组织一次验血。马茹找到班主任,把自己患有艾滋病的事实告诉了他。
不久,班主任劝她改专业。“主要是怕在用刀刮眉毛的时候,误伤到自己和别人,造成血液传播。”马深义说。
马茹走了,再也没回学校。她去了北京,在大姐马可小店里帮忙。
马深义觉得,马茹心里其实是有怨气的。
刷出来的新家
我在文楼村见到马深义时,他正站在路边看同村人举办的一场婚礼。“看着别人给孩子盖新房,办喜事,心里不得劲。”马深义挤出一点笑容说。
他觉得从今年开始自己的心态不好了,老觉得是自己害了孩子。“太焦虑,头发就白得快。”
马深义老想着,趁自己还活着,多赚点钱,把马占朝养大,也给他办一门亲事。
从广东回家后,马深义买了一台时风三轮拖拉机,农闲时给人运运砖头。为了多赚10块钱,马深义把装车的重活也揽下来,累得喝水的力气都没有。
今年,马深义把玉米和麦子卖了,得了近六千块。可他算下来,减去种子、化肥、人工的成本,就没剩几个钱了。
国庆前夕,村里来人通知,要农房翻新。“让自己先拿钱,翻新合格后,县政府再把钱补贴给我们。”
马深义跑到县城,花了几百块买了一桶白色涂料和红漆,把外墙来来回回刷了好几遍,把大木门也刷了个红通通。
不久,县里来了几个人,拍了一通照片,走了。村里干部说,补贴的钱很快能发下来。
年底了,补贴的钱仍不见踪影。马深义说,身体不好,以后不准备出远门了。
2014 父亲的心愿
文|徐丽宪 杨静茹
马深义的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一,但是精神比去年好了很多。
马深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的一名艾滋病患者,十几年前因为卖血染病。2001年妻子艾滋病发作去世以后,他与3个孩子相依为命,其中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也是艾滋病患者。
今年是回访的第10个年头,马茹18岁,马占朝也已经14岁了。
“感觉这一年也没啥变化,”马深义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背倚着门框,手紧紧地揣在兜里。
去年从广东回来以后,马深义就再没出去打工——身体不好,适应不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今年种了一年庄稼,收了三四千斤小麦,五六千斤玉米,“卖个万八千,除去化肥、种子,剩下来几千块钱,还是不如打工挣得多。”
冬天地里没活,马深义跟同村的一个工头到附近的工地上去当小工,一铲一铲往搅拌机里放沙子,一天能挣个八九十块钱。“孩子长大了,开销也越来越大,我就光想着出去干点活,我干的重体力活还是比较多,身体还能承受。”
活一天扒蹬一天
马深义心里憋着一股劲,他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现在住的这间屋子已经十几年了,阴暗返潮,墙皮都脱落了。马深义想明后年把房子翻盖一下,盖成两层小楼。“我有这个病,一年不如一年,一旦发病了,谁给孩子操这个心,我得给他盖。”
盖房子再加上装修一共得需要十几万块钱,这给马深义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有种争强好胜的心情,其他人你弄得好,我比你弄得还好。”
村子里有一批跟马深义同样遭遇的人,其中几个破罐子破摔,每天喝酒不干活,“我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我活一天就得扒蹬一天,给小孩子创造财富,人活一天不干活,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年轻的时候不干活,等到老了想干也干不了了。”
可能跟这种积极的心态有关,马深义今年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一个多月以前检查身体,他的免疫力有六七百。
大女儿马可(化名)两年前结婚,跟着丈夫在北京的一个小村落里开了一间小超市,但是今年马可跟丈夫分开了。“她跟男人合不来,细节我也不知道,老人很多时候干涉不了,只能劝劝她,也没有用,倔得不行。”马可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曾经给马深义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现在这点安慰也破灭了。
二女儿马茹去年就不上学了,闲在家里,“之前跟别人一起卖衣服,别人嫌她不行,不让她干了。”马深义还没有学会跟这个慢慢长大的姑娘交流,“她跟我沟通不多,女孩子跟我也不好沟通”,这句话他重复了三遍。
马深义老觉得自己连累了孩子们,“干活的时候不想这个事,不干活的时候在家里老想。”
想上趟北京
今年五六月份,玉米秧刚种上的时候,”北京一位陈女士给马深义打来电话,说她看了关于马深义一家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想请他们到北京玩,带他们去天安门。这个提议让马深义心动了,占朝一直想看看天安门,看看长城。
暑假过后,马占朝到离家四里外的中学去读书。“他说骑车子蹬得腿疼,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电动车。”马深义用手比划着儿子的身高,“他都到我脖子了,站在我跟前,感觉比我低不了多少。”
过去马占朝的学习成绩是马深义的一大骄傲,简陋的屋子里,整整一面墙的奖状格外抢眼。初中以后,进入了调皮叛逆的青春期,马占朝成绩下滑得厉害。“我说他,大哥哥大姐姐都看见你这些奖状了,你将来考不上大学,你说你咋交待啊?他光笑,不吭声。”
大女儿留在家里的一台智能手机成了马深义的一块心病,马占朝放学回家就拿着玩游戏,马深义怕他把心思全花在这个上面,不好好学习,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控制。
马占朝从来不跟马深义说学校的事,平常聊天就说说哪里哪里又打架了,马深义很担心儿子会掺和进去,不走正路。
可能是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带孩子,马深义对孩子倒是很有耐心,“我从来都不凶他,都是慢慢说,不过没什么作用。”
“他脑瓜可聪明哩,好奇心重,好多东西都能卸开再装上,就是不好好干,玩性大。”虽然是责备,马深义的语气却很温和。我们说想见见占朝,他头往外扬了扬,“骑车找同学玩去了,天黑才能回来。”
马深义最大的心愿,就是趁自己还有能力,把马占朝好好养大。“我也没啥事,你到这跟我聊聊天,我心情就好得多。”马深义送我们走出堂屋,阳光下的院子比屋里还要暖和,一只黑白花的小猫懒洋洋地卧在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