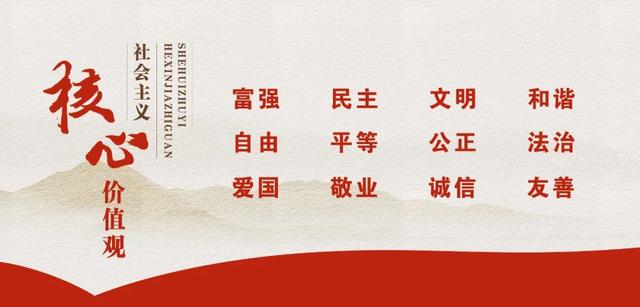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交际花形象,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文学作品中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学作品中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
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交际花形象
看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艰难曲折
----以《日出》中的陈白露为例
武抒祖
自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伤势》对五四时代女性个性解放的冷静审视、理性思索与深刻反思,以“另类”者的姿态从个性解放建立美满家庭结束处启动,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婚姻为纬,以个性解放为经,提出了大家易于忽略的、未曾深思的、极具现实的困扰青年男女个性解放“后”“怎么办”的难题。
鲁迅先生意在通过小说表达了个性解放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做好打持久战、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因为保守顽固势力依然强大,弱小的新生力量需要假以时日舒缓“麻痹了的翅子”,练习“忘却了的飞翔”的技能,社会需要假以时日理解接受它。而保守势力的仇视围猎,社会对新生力量的不接纳,不可能给弱小的新生力量以优容的时间让他们舒缓“麻痹了的翅子”,练习“忘却了的飞翔”的技能,极有可能把个性解放扼杀于摇篮之中,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反证个性解放任重道远并非杞人忧天。人生最痛苦的是觉醒后无路可走。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演说中,纵论娜拉的个性解放是一个社会命题与时代课题。
十九世纪后半期挪威作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社会问题剧《娜拉》,叙述了女主人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娜拉由于觉醒而反叛,随着她身后那扇门“咣”地一声关上,娜拉为了自由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剧本虽然结束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留下的社会问题与时代课题具有强大的召唤结构。鲁迅先生正是发现了作品的这一召唤结构,开始从剧本结尾处入手,思考娜拉走“后”的种种遭遇,“……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觉醒者”娜拉走上个性解放后,依然没有准备好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一旦冲决牢笼、打破枷锁恰如“……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性累加的背负的包袱太多、太重,对女性的压抑又最深,女性的个性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
五四后,新文学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在个性解放思潮的启迪与鼓舞下冲决出旧式家庭,拥抱新生活,实现人生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她们面对旧思想的合围,在险恶的社会中无疑于裸奔,毫无疑问遭遇“堕落”或“回来”的宿命,管窥个性解放之路任重道远。
有趣的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的新女性大多属于交际花形象。这些交际花们破笼而出,在追求新生活的个性解放之路上,遭遇“鹰”“猫”的围猎而无路可走,最终走向堕落的人生悲剧,让人掩卷深思。
现以曹禺的《日出》中的交际花陈白露,叶灵凤的《未完的忏悔录》的“歌舞皇后”陈艳珠,茅盾的《子夜》中的交际花徐曼丽,寡妇刘玉英,少女冯卿,台湾作家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中的百乐门舞女尹雪艳等众多交际花形象分别展开论述。
一、《日出》中纸醉金迷的陈白露
“交际花”现象是与工业文明的勃兴而生的一种衍生物。小农时代的社会不会也不可能给“交际花”的发轫提供任何契机。但工业文明时代就不同了。机器的轰鸣声创造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源源不断的金钱迅速注入巨大的财富池里。同时,社会阶层快速分化。一些嗅觉敏锐的人捕捉到了工业文明散发的巨大商业气息,紧随工业文明的脚步而一跃成为了商界巨贾,折射这些人的商业头脑,管窥他们在商界的才、识、见。他们腰缠万贯,豪掷千金,大都会是他们的栖息地,霓虹灯是他们的娱乐场,权贵们是他们的座上客。他们呼风唤雨,展现自己作为成功人士的傲娇身姿,魔性魅力,都市成为他们的想象,豪宅是他们的标配,霓虹灯紧随他们的身影,香槟美酒与他们亲吻,因此交际花应运而生。
交际花自然别于旧时代的妓女。她们属于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美丽的容颜,怀揣良好的现代教育,衣着华美,举止优容,仪态万方且玲珑剔透,处处散发着她们的修养与气质,生活奢靡,经常穿梭于戏院、舞场、宴会等上流社交场所等大场面;“交际花”们长袖善舞,靠色相又不仅仅恃色相周旋于豪门,游走于权势。毫无疑问,交际花成为豪门权势豢养的一只“金丝鸟”,成为坐拥戏院、舞场、宴会的一件精美“玩偶”;“交际花”们依附于豪门权势的供养,豪门权势当然是她们的“宿主”,但她们又不单单依附于某一特定男性,有较为充裕的交际空间与游走时间;她们既是众多男性的亲密情人,也是男人们心目中的女神,更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交际花”不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独特现象,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前,他们就已经活跃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了。这不难理解。因为工业革命最早发轫于西方,商业的繁荣催生了都市的繁荣,那些琳琅满目、散发出种种诱惑的物质容易俘虏欲壑难填的人性,加之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还没有为女性准备更多的职业,职场竞争力明显处于弱势,但又不得不外出谋生,“交际花”在西方都市中萌发是自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西方许多文学作品的关注点投向了“交际花”形象并非个例。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就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交际花形象——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穿梭于巴黎上流社会,与阿尔芒之间演绎了一出凄美的爱情悲剧。尽管《茶花女》演绎的是一部爱情传奇与爱情悲剧,然而锋芒所指,是对冷漠浮夸的巴黎上流社会和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的深刻批判,也对交际花玛格丽特的不幸人生报以深切的同情。不可否认,作为交际花的玛格丽特沉溺于巴黎的繁华,迷醉于巴黎的风情,对自己的人生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缺失的无疑是振翅飞翔的翅膀与飞翔的能力,遑论独立的人格,更不具备娜拉的觉悟,这无疑为她个人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无独有偶,巴尔扎克深邃的眼光也游弋到了交际花这一弱势群体上。他的《交际花盛衰记》,讲述了巴黎交际花埃斯黛简短、奇特、悲剧的一生。埃斯黛“是个过着流浪生活的妓女。”对沉浮上流社会的诗人吕西安一往情深,为了渴望与吕西安享受幸福贞洁的生活,埃斯黛前往修道院接受四个多月的宗教仪式教育,借此想洗白自己的交际花身份。然而,在吕西安眼里,她充其量只是一颗摇钱树与玩物而已,埃斯黛的身世、交际花的地位使她与吕西安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社会天堑,最终含恨殒命。巴尔扎克借小说再现了巴黎社会的风情:无论地位显赫却逐渐没落的贵族,抑或是财力雄厚又锱铢必较的资本家,还是野心勃勃且不择手段想跻身上流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周旋于险恶社会与丑恶人性之间最终惨淡谢幕的交际花,无不是散发着浓浓商业气息的巴黎大都会的牺牲品,把商业罪恶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而批判了商业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无尽丑恶及对人性的荼毒。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沉睡在黑屋子的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一代知识分子以觉醒者的姿态睁开眼睛向外看,看到的几乎都是新奇的世界。他们反躬自省,我们的思想文化几乎都是陈旧落伍的,他们决绝地抛弃旧传统,拥抱新思想,极力推介在他们眼里属于文明的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对西方文艺作品的译介就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鲁迅回顾自己接受现代西方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方式,曹禺的话剧、胡适的现代诗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原来文艺作品还可以这样写!
曹禺无疑是属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
他在《日出》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浪迹于都市的、不甘沉沦又无力自拔的、过着纸醉金迷的高级交际花——陈白露——的形象。在剧本中,剧作家并没有详细地叙述交际花陈白露堕落之前的生活,但是在剧作家的叙述中我们发现这个常驻高级旅馆里的交际花曾经有着和五四新女性相似的经历:出生书香门第,女校高材生,还有一个暗恋自己的方达生,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育背景,陈白露似乎有一个令人期待的美丽人生,有可能过上一种优渥的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尊宠的地位。但偏偏父亲去世,经济陷入困窘,陈白露既不愿意退回到原来的乡下去过一种庸常的人生,又无法跻身上流社会,在这样的矛盾中陈白露勇敢地走出家门,只身闯荡上海寻找自己的人生。在上海,陈白露做过电影明星,也做过舞女,这些都是吃青春饭的职业,一旦成名出道,将光环笼罩,人人追捧。从陈白露的职业选择管窥她不甘寂寞,不甘平庸,渴望凭借一己之力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位,这与旧时代的女性甘愿依附男人做附庸有云泥之别,她的行动无疑是一个个性解放者的独立宣言。设若陈白露的人生轨迹按照她设计的路线图推进,这对个性解放者具有极大的精神感召力,示范鼓舞力,也证明了个性解放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个性解放只需要勇气、决心与毅力完全可以实现。但这太概念化与理想化了,把社会、人生想得太过平面化与表面化。惜乎飞出笼子的陈白露折戟沉沙,既破灭了她的电影明星梦,也销蚀了她的舞女奋进梦。她不见容与银幕,又无法立足于舞台,只好挣扎在十里洋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级交际花,成为商界巨子的“玩偶”。这一激情而又昙花一现的个性解放历程充满了血和泪,掺和着挣扎与屈辱,陈白露目睹了社会的残酷,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她既厌恶这种如鸦片般腐蚀肉体的生活环境,又无法挣脱如“黑洞”般吞噬灵魂的都市生活,她没有决心,更没有实力再一次冲决牢笼她的现实,肉体与灵魂绑架了她,她不可遏止地堕落但又不甘心堕落,她渴望振作但又无法振作,只好在堕落与振作中挣扎,夜晚在宴会、舞池中放飞自我,白天在高级大旅馆里虚掷青春。陈白露的堕落自然离不开社会等外部因素,但毋庸置疑,她自身不具备飞翔的翅膀与飞翔的能力是内部因素,但至善至美的本性并没有销蚀殆尽,残存的一丝人性时不时地敲击着她那脆弱的灵魂,拷问着她的人性,有时候不免满腔正义,甚至单纯得像个少女。
“陈白露惊喜地发现了窗子上的霜花,她惊喜地叫:‘你看霜多美,多好看!”
从这个细节我们不难发现,陈白露即使堕落风尘但内心依然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敏感与向往,正因为内心深藏着美,渴望着美,她才能在不经意间发现美、拥抱美、欣赏美。由此反观,美对人心灵的涵养与浸润,具有强烈而持续的效应。让我们暂时把镜头推向陈白露纯美的“竹筠时代”:那时的她单纯而快乐,有理想且向往自由,拥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竹筠时代”。“竹筠时代”时代无疑是美好的,但又是极为短暂的。它因美好而短暂,因短暂而弥足珍贵。但是家庭的变故,睁开眼睛开始看世界,呼吸到新鲜空气的陈白露,当然不愿意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起点,她被迫直面残酷的社会,在大都市上海一番摸爬滚打使她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一切以钱为中心”。问题是,她极为痛恨这个金钱社会所散发出来的铜臭味,但又无法抑制对“上层社会”富裕生活的渴望,表面光鲜的“上层社会”恰似巫蛊一般镇魇着她,使她无法自拔,被迫开启惨淡的人生。一方面,陈白露厌倦上层社会的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同时惊悚于他们的勾心斗角,想要置身事外但又身陷旋涡,想要逃逸但又无法逃逸这个社会对她的蚕食:她意识到自己沉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在啮噬着她的肉体,销蚀着她的灵魂,她一直在这种矛盾的泥淖中挣扎,由于她不具备飞翔的翅膀与飞翔的能力,每次挣扎只能让泥淖把她裹挟得更深更紧,对人生的绝望使她不能自救;陈白露虽不能自救,却可怜同情营救他人——“小东西”,因为在“小东西”身上发现了曾经的自己。我们能不能这样设想,剧作家设计的“小东西”这一角色,是否是一架时光机,是“竹筠时代”的陈白露的别样复现,“小东西”的人生轨迹就是陈白露的人生轨迹,“小东西”的最终命运就是陈白露的结局。如果洞穿了这一隐喻,就会理解她为何不惜得罪权倾一时的金八爷来营救“小东西”。陈白露的自杀就是她的觉醒,也是一次自我救赎。剧本结局设置了一幕场景:伴随着一轮初生的太阳的冉冉升起,陈白露结束了自己的屈辱人生,完成了自我救赎,成为一曲个性解放的挽歌。
鲁迅说:“没有看到希望就在睡梦中死去的人是可叹的,而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那就更残酷了”。作为个性解放者的陈白露就是因为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腐烂的尸骸,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她的自杀无疑是她清醒后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唯一选择。方达生与陈白露同属于“竹筠时代”的个性解放者。方达生与陈白露的悲剧其实与涓生子君的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鲁迅先生高论:“笼子里的小鸟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陈白露固然厌恶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身陷龌龊的泥淖,但是方达生无法提供泥淖之上的罂粟花,这样,陈白露只能选择自我毁灭应是逻辑使然。涓生子君的悲剧参见拙作《从<致橡树>管窥新时期女性爱情观的反拨》,此不赘述。剧作家有意设置清纯的方达生,似乎要阐明一个深刻的道理,无论任何时候,清纯只能是一面镜子,反衬出镜外的污浊而已,与《日出》时代的个性解放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和鲁迅一样,曹禺关注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都市里的新女性(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之路,只不过曹禺笔下的新女性最终变成了交际花而凋零,鲁迅笔下的新女性变成了平庸的家庭主妇而凋零,从这个角度看,她们殊途同归。但是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女性的个性解放之路的漫长与艰难,也是对个性解放者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