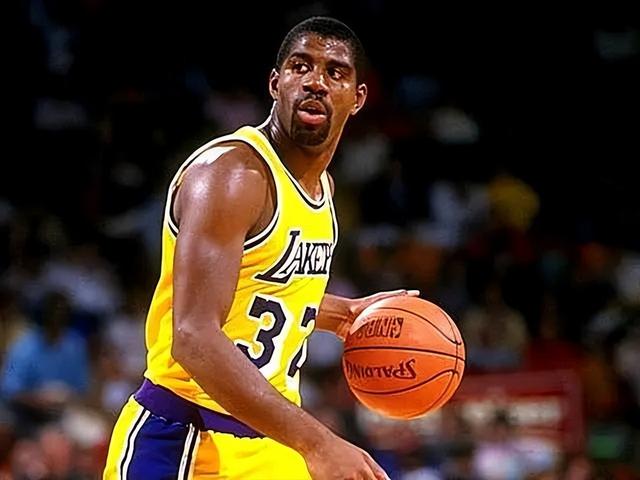在温(今河南焦作温县西南)之会上,首先处理的就是卫国的事。卫成公让大夫鍼(zhēn)庄子充当自己的代表,让另两个大夫宁武子和士荣担任助手和辩护,跟元咺(xuǎn)争讼,结果也不知道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卫成公败诉了。不过这并不代表《公羊传》的说法就更符合事实,因为以晋文公这时候的势力,他想要说谁有罪那就是谁有罪,卫成公屡次惹他不爽,遭到不公正对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败诉直接导致了士荣被杀,鍼庄子被砍脚,只有宁武子因为被看做是忠臣而幸免于难。我们不知道这是卫成公做的还是晋文公做的,因为《左传·釐公二十八年》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没有主语,但不管是谁做的吧,败了诉的卫文公终归要受到制裁——晋文公把他抓起来,关到了周天子的监狱里,只允许宁武子负责照顾他的衣食。元咺则返回卫国,改立公子瑕为卫君。
卫国的事处理完之后,曹国一个名叫侯孺的“竖”,也就是“内廷之小臣”,见没人提曹国复国的事,便收买了晋国的筮(shì)史,让他跟晋文公说说这件事。这时候晋文公正好生病,需要筮史禳(ráng)除,可见侯孺之所以收买筮史是经过考虑的,而这个筮史胆子也挺大,竟然敢对晋文公说让曹国复国他的病就会好。
让曹国复国晋文公的病就会好,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这个筮史接着说的话却很有些水平,他说:“曹国和晋国都是姬姓,当年齐桓公迁邢存卫、会盟诸侯是为了封异姓,可现在您会盟诸侯却是为了灭同姓。会盟诸侯而灭兄弟之国,叫做非礼;承诺了让曹国复国却不兑现,叫做非信;曹国和卫国有同样的罪行却得到不同的后果,叫做非刑。有这三个‘非’,您说该怎么办呢?”不知道晋文公是相信了他的胡说八道,还是被他上面的这段话说服,同意了释放曹共公,让曹国也复了国。

元咺告状
曹国和卫国的事看上去已经尘埃落定了,但其实晋文公并没放下。两年后的周襄王二十二年(晋文公七年,鲁釐公三十年,前630年),也不知道仍然关在“天牢”里的卫成公碍他什么事了,他派了一个叫衍的医生去下毒,想要害死卫成公,幸亏负责卫成公衣食的宁武子很警觉,收买了衍,让他减少了毒药的分量,卫成公才躲过一劫。
杀卫成公没杀成,第二年(周襄王二十三年,晋文公八年,鲁釐公三十一年,前629年)晋文公又打上了曹国的主意,逼迫曹共公割让济水以西的土地给他用来赏赐诸侯。曹共公这回可没犯什么错,但是又不敢得罪他,只好听命。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晋文公这个霸主真够“霸”的。
不难想象,跟卫国和曹国一样不曾礼遇流亡中的晋文公、后来又背晋助楚的郑国,也逃不过晋文公的报复,就算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以后也归附了晋国也没有什么用。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谋杀卫成公的前一年,周襄王二十一年(晋文公六年,鲁釐公二十九年,前631年),晋国就曾召集诸侯在翟(dí)泉(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东南)会盟,商量讨伐郑国的事,但不知为什么没采取具体行动。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谋杀卫成公的那一年,晋国才终于出手,联合秦国包围了郑国,要求郑文公把大夫叔詹交出来。
当年叔詹曾建议郑文公礼遇流亡的晋文公,被拒绝后又建议杀掉他以绝后患,所以这时候晋文公才把矛头指向了叔詹。但这其实不过是个幌子。我们已经能看出来,就算叔詹死了,以晋文公的为人,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史记·郑世家》正是持有这种看法,它说:叔詹为了保全国家,毅然杀身取义,可是当郑国人把叔詹的尸体送给晋文公的时候,晋文公却不肯退兵,改口说:“我一定要见到你们的国君,当面羞辱他一顿才行。”叔詹算是白死了。
《国语·晋语》有不同的说法,它说:叔詹并没自杀,而是只身前往晋营面见晋文公,做了一番表明自己明智忠君的演讲,然后走到烹他的鼎跟前,抓着鼎耳对周围的人大喊:“从今以后,人们该知道忠君的人都是我这个下场了吧!”这简直就是在鼓动晋国的大夫们以后不要忠君。晋文公哪还敢杀他?只好“厚为之礼而归之”。

叔詹据鼎耳而疾号
我们不知道《史记》和《国语》哪一个说得对,我们只知道不管叔詹死没死,秦晋两国都没有退军。这时有人建议让烛之武去说服秦穆公。烛之武“夜缒(zhuì)而出”,见到秦穆公,说:“秦国和晋国围攻郑国,郑国知道马上就要灭亡了。如果灭掉郑国对秦国有好处,我不敢来说这些话,可是隔着好几个国家去治理远方的领土,您也知道这有多难,干嘛要灭掉郑国而给邻近的晋国带来好处呢?晋国的国力雄厚了,秦国的国力就会相对削弱。如果放弃灭郑的打算,让郑国成为秦国在东方道路上的‘东道主’,那么秦国使者路过的时候,郑国就可以随时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对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之前在晋惠公的时候,您曾经对他有恩,他也答应把焦、瑕二邑割让给秦国,可是他早上渡河归晋,晚上就筑城拒秦,这您是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呢?它如果在东面得到了郑国的领土,一定又会想扩张西面的领土。如果不侵损秦国,晋国从哪里取得它所企望的西方土地呢?所以说灭郑是一件使秦国受损而使晋国受益的事情,请您好好考虑考虑。”
烛之武这番话完全是站在秦国的立场替秦国考虑的,不由得秦穆公不赞许,于是他“与郑人盟”,并派杞(qǐ)子、逄(páng)孙和杨孙协助郑国防守,然后不管晋国撤不撤军,自己先率军回国了。
秦军这一撤围戍郑,弄得晋军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处境变得有些尴尬了。幸亏郑国终归还是害怕晋国,抓住秦国退兵的机会派人来跟晋文公求和,晋文公才找到台阶下。他跟郑国约定,把之前流亡到晋国的郑国公子兰立为郑国世子,总算是体面的撤了军。

烛之武说秦穆公
第二年(周襄王二十三年,晋文公八年,鲁釐公三十一年,前629年),也就是抢了曹国土地赏赐给诸侯的那一年,以抵御狄人入侵为由,晋文公增设新上军和新下军,加上原来的三军六卿合计五军十卿,从此晋国成为春秋诸国中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这要感谢晋惠公时候吕省“作州兵”,取消了“野人”不能当兵的限制,才使他能够获得这么充足的兵源。
又过了一年,周襄王二十四年(晋文公九年,鲁釐公三十二年,前628年)春,楚国派斗章到晋国讲和,晋楚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外交关系,暂时结束了敌对状态。然后,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春秋时代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与世长辞,结束了短短九年的国君生涯。
晋文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颠沛流离的流亡之中,但是身边却能聚集像狐偃、赵衰(cuī)、先轸(zhěn)、魏武子、胥臣等等这样一大批贤能之士,说明他很有一些过人之处。他即位之后,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扭转了晋惠公时期所造成的颓势,纳襄王于王城,败强楚于城濮,为践土之盟,召天子,服诸侯,算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但这个人做事有些不择手段,心胸也不够开阔,跟春秋首霸齐桓公比起来,显得有些假仁假义、阴森狡诈。《论语·宪问》批评他“谲而不正”,也就是诡诈而不正派的意思,应该不算冤枉他。

——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