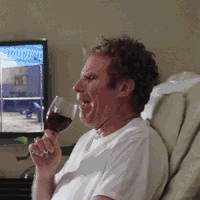清朝末年,著名学者严复翻译西方的《天演论》,出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赫氏此书前半部分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半部分讲伦理学。
严复选译了此书的部分导言和前半部分。
在翻译中,他不完全照原文直译,而是有选择地意译,并在不少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一种以译文为形式的借题发挥,阐述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办法。
严复的翻译,完全使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在今天看来,这与阅读古书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根据严复的译文进行讲解。

清代末年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

严复译《天演论》时的照片,当时他44岁。
严复《天演论》的译本自序(以下严复原文用黑体字,其他的是我的解说)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
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名学即现在所说的逻辑学,穆勒约翰,即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论自由》,严复译作《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
理极,指理论的奥妙处,最深的理论。
这是说,要想了解别的国家的著作中的深刻道理,必须通晓几国语言文字才行,否则无法理解人家在说什么。反过来讲,要想搞好翻译,也必须懂得其中的道理,不是只懂外语就能成功的。
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严复认为,穆勒这个说法,他开始时是不太相信的。通过翻译西方的著作,他才理解了这一说法,是不可动摇的至理。
这是因为人们撰写一部真正的学术著作,里面包含着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古代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的思想义理,是他们耗费一生的精力所得出的结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又因为这些深奥的道理在义理层面是相通的,所以需要阅读不同语言文字写成的书,将它们互相比较,这样才能加深理解其中的丰富义理。
另外,还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情况,但在不同国家的学者的著作中,由于论述的角度不同,可能会有此书说得简单,而彼书说得深入的情况,因此把它们拿来比较着看,就能帮助人们加深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读懂中国的古书,也必须广泛阅读外国的学术著作,以此作为参照。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
这是说后人读古人的书,但没有从事过古人的学问,所以古人所论说的道理,后人在理解上,是与古人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的。即古人对所说的道理的理解是深切的、精到的,而后人对古人所说的道理,其理解则是肤浅的、粗疏的。
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
再加上时代久远,古书在传钞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字句的错误,古今的读音也不一样,还有许多是假借字,也往往也分不清,还有不同时代的风俗也在变化,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也不一样。在读古书时既有这些情况,虽然历代学者不断注释疏解,但对于古人在书中所要阐述的道理,则变得更为隐晦了。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人要读懂古书,是非常难的。
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虽然如此,古人在书中所寄托的道理,却一直不会变,如果所说的道理真的精妙,所说的事情真的可信,则年代的久远和风俗的差异,都无法隔断它。所以古人所说的道理,没在此处传承,就在彼处(西方著作中)可见,虽然相互之间并没有交流,但所说的道理却是相通相合的。研究道理的人,用在彼处获得的道理反过来考证中国古人所说的道理,就会变得非常清楚明白,让人如梦初醒。这种收获让人感到亲切有味,比那些只知道死读书、死背书的呆子们,这种用西学反证中国古代学术的方法,其效果真是远远超过一万倍。这真是学习研究外国语言文字所能获得的最高快乐。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
现在的中国,对于孔子提倡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已经视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尊之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了。而孔子对于这六艺,以《周易》《春秋》为最严谨。司马迁说:『《周易》根据隐晦的事物说出明显的道理,《春秋》从显著的现象推出隐晦的道理。』这是天下最为精到的说法。
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
原来我认为所谓的『根据隐晦的事物说出明显的道理』,是指《周易》用来观察物象而系上卦辞爻辞,让人们据以判定事物变化的吉凶而已。所谓的『从显著的现象推出隐晦的道理』,是指孔子在《春秋》里对人们的行为之善恶进行褒贬而已。
等到我在英国学习与阅读了西方学者的逻辑学,才知道他们在研究自然事物之科学时,有两种方法,一是内籀术,一是外籀术。前者是逻辑学中的归纳,后者是逻辑学中的演绎。
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所谓的内籀(归纳),是观察事物的详细具体情况,从而了解全部事物的普遍情况,这是根据细微情况而对整体情况加以会通的方法。所谓的外籀(演绎),是根据公理(定理、规律)来判断更多的事物,这是设下定理来判断未知的方法。知道了这两种方法,我不由得推卷而起,感叹地说:
有这种方法吗?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周易》《春秋》的学术方法啊。司马迁所说的『根据隐晦的事物看出明显的道理』,就是西方人说的外籀法。司马迁所说的『从明显的事物推出隐晦的道理』,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内籀法。他的话是那样清楚而明白,让人顿开茅塞。这两种方法,是穷究事物根本道理的最重要途径。可是后人却不知道广泛地加以应用,不去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具体事物,也没有继续深入研究这两种方法而已。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的兴盛远远超过古代,他们获得的各种名理、公例(规律、定理),都能让人获得最正确的认识,不可置疑。但我们中国古人提出的方法,往往早于西方人,这不是牵强附会的抬高自己。我要举出最明显的例子,来向天下人求证。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奈端即牛顿,动之例三,指力学三定律),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西方学术中最为切实而有用的学问,有四种: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用这四种学术可以解释复杂的各种事物之变化。而我们中国的《周易》是以逻辑学和数学为经,而以化学和物理学为纬的,合起来就称为《周易》。自然界内,物体与运动相互任用,没有物体,就无法看到运动的变化,没有运动,就无法看出物体的变化。
而在《周易》中,凡是运动,都是乾,凡是物体,都是坤。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其一是说静者不自己动,动者不自己停止,而且运动的线路必是直的,速度必是均匀的。这个定律真是旷古以来的发现。自从他的这个定律发现之后,天文学就获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这都是人类事务最有利的工具。而《周易》里则说:『乾的静是专一的,乾的动是直线的。』见《周易·系辞》:『天静时专一不乱,动时刚正不差。』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着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指牛顿力学第三定律),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之后二百年,英国学者斯宾塞尔提出天演说,认为事物的变化都是天然的自然进化,无论是天、地、人,无不如此。这也是近代最有名的学说。
他为『天演』下定义说:聚则合为物质,散则形成运动,事物在开始时都是简单的,发展到最后,就都是混杂和复杂的。而《周易》里说:『坤的静是聚合的,动是发散的。』即《系辞》里说的:『大地静则凝闭,动则万物生长。』
西方还有全力不增减的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而《周易》则有『自强不息』的说法,在西方之前。西方有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但方向相反。此即凡动必复之说,也就是《周易》里的『消息』之义:《周易》的丰卦里说: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意思是说天地有盈与虚的变化,实质上就是阴阳消息变化所引起的。古人说的消息,消指生,息指止。与现代所说的消息,意思不一样。
而《周易》里的『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是说易(变化)不可见(不存在)了,乾坤就几乎完全停止了。这与西方人的热力平均说意思相近。热力平均说,即德国克劳修斯提出来的热寂说,即热力若完全消失,则天地就随之毁灭。
这些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的说法,难道都是巧合吗?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而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
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说西方的发明,都是我们中国以前就已有的,更不能说西方学术的这些发明,都来自于东方,因为这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这样说,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古人创始的很多思想与道理,后人都不能继承与发展,古人提出了大致的说法,而后人不能深入研究而使之专精,这仍然是不学无术的没有开化的人而已。爷爷再圣明,也救不了子孙的愚昧。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
总之,古书的难读,以中国的古书为最。二千年来,读书人只知靠读书来谋求利禄,抱残守缺,没有独辟的思想。所以生在今天的人就转向西方的学术,通过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学术,反过来了解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这种事情,只能与深知其味的人说,很难与对此完全无知的人说。
中国与西方相互交往以来,读书人都知道闭塞与鄙陋是一种耻辱了。要想学习西方学术,方法与途径也越来越多。但是却有一两个大人物,以傲慢的态度说西方的长处只在于形而下的技术方面,他们所追求的,都不过是各种功利而已。
这不过是只凭自己的臆想提出的看法,没有考察事实。讨论国事,考察敌人的情况,自我反省,断不能抱有这种想法。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而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绪丙申(1896)重九严复序
赫胥黎的这部书(指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主旨本来是对斯宾塞的学说进行补救。因为斯宾塞只相信天然的进化与变化,所以人要听任自然的发展变化,而赫胥黎认为还要强调人力的重要性,这是他与斯宾塞的不同之外。而赫氏的看法,与我们中国古人的看法甚为相合。而且这种看法对于中国在近代的自强保种问题(变贫弱为富强,保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不被列强所消灭),也颇有参考价值。
夏季天长,就翻译了他的这部书。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些空谈而对实际政治无所裨益,那我也是置之不顾了。光绪二十二年严复序。
把严复这篇序细读完后,觉得有两点值得说一下。一是近代以来中国多次出现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但都不能持续下来,使国人及国学从中受到真正的益处,而往往成了过眼烟花,一时热闹而已。这就是因为人们不能如严复所说的那样,认真结合中国古书中的道理来思考问题,西学一热,就妄自菲薄中国古学,不知二者可以互通,都是用来思考各种问题的有益养料。
另一种情况,是熟悉外语的人不一定熟悉西方学术,熟悉西方学术的人不一定熟悉中国古代学术,对阅读中国古书还不能具有自如的能力。所以严复一再说读古书难,读中国古书更难。这种情况,也导致了中国人不能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只成了偏于一隅的井蛙。所以既不能理解中国古人的精妙思想,也不能掌握西方学术的精华内容。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三不成四不就,所以在思考处理中国的种种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肤浅空洞。
二是细读中国古书,不要忽视近代以来学者用古代文言文撰写的文章与著作,此类文章与著作并不少,也离现代中国人不远,但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已觉得这类文章与著作,似乎是过时了,其实他还不能真正读懂它们。所以近代以来有志之士思考中国问题的许多精妙见解,就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了。
如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还有很多是严复在翻译时的想法与见解,他都一并写在这些译著中了。而我们也没有对它们予以足够的重视。且严复写文章,喜欢用古代汉语,这是他在科举上没有取得功名的一种报复。但这样写成的文章与著作,却让不少中国人读起来感到生涩难懂,所以我们说要细读古书,也应包括近代严复等人的文章与书籍。
此类人物在近代颇为多见,他们的著作与文章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要才过了一百年就忘了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阅读古书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要想不忘记过去,就要努力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不要把阅读古书理解为背几首唐诗宋词那样浅薄。

严复译《天演论》正文页

严复译《天演论》正文页面
三是在今天大谈国学的时候,也不要忘了西学,可以说近代以来,没有中国人积极的学习西学,也就没有现代的中国。将来要发展得好,同样不能置西学而不顾。现在学外语大行其道,许多人的外语只会说几句英文,却看不懂西方的学术著作,这样学外语,有多少价值?我们的大学把外语系定义为外国语言文学,这是非常片面的。学习外语的最大用处,应该是掌握外语这门工具,去了解外国的学术,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这样才能使中国人真正掌握外国的先进事物,为我所用,加速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严几道就是严复,这时早年的版本,首先是严复的自序。

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手稿

严复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