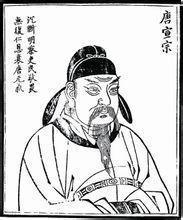一
东汉一朝,羌人逐渐取代匈奴成为东汉王朝最具威胁的边患。自从光武帝平陇右、收河西之后,较大的羌汉战争共有五次:第一次是从建初二年(公元77年)到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第二次是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到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第三次是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到永嘉元年(公元145);第四次是从延熹元年(公元159年)到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五次是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了东汉一朝,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伏、无有宁日。羌汉战争波及到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范晔的《后汉书》中新设《西羌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历史上这一问题的凸显。
东西差别古已有之。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秦陇一带既有适于农耕的黄土高原、绿洲和河间谷地,又夹杂着宜于游牧的草原地带,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和游牧文明交融区,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此消彼长的交替过程。山西地区迫近游牧民族的地理环境以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混融的特征,使得山西文化有着浓厚的"戎狄"色彩;而山东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有强大的经济、文化优势。直到战国中期,关东诸侯对秦国仍是"戎狄遇之"。战国后期,秦国日渐强大,东向拓地,山西自成一独立区域和山东诸国对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西的地域观念基本形成,东西矛盾开始凸显。秦国最终以锐不可挡的气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似乎不可一世的秦帝国旋即二世而亡,对此当然有许多解释,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王朝低估了统一的帝国内部业已存在的东西差异和矛盾,急于强求一致。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东西矛盾依然存在。关于西汉东西地域文化的差别及特点,《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的生动描述早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对于西汉一朝山东、山西人士在政治舞台上的境遇及相互斗争,傅乐成先生也有过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此不赘述。由于西汉帝国定都长安,客观上必须重视山西地区;而山东人士则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文化优势,通过入仕、向山西移民等途径参与到中央政权中来;山东、山西两者之间政治重心功能和经济重心功能的分化,也使得帝国东西两大部分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正是由于西汉帝国东西之间有着频繁的良性互动和全方位的对流、保持着一种巧妙的均势,才使得东西矛盾得到较好的协调,矛盾双方能够凝聚在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下,不至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严重对立的程度。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才使得西汉帝国血脉周流,保持了相当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张力,最终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空前强大的西汉帝国。
二
东汉帝国定都地处山东的洛阳,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虽然三辅地区由于历史的惯性,在东汉初期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文化优势和繁荣,但这毕竟已属于"落日的辉煌"。三辅人士并不甘心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还都长安的建议,如京兆杜陵人杜笃就专门写了《论都赋》一文,恳请光武帝还都旧京。直到几十年后的章帝初年,"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时山东、山西地位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了。
凉州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同西汉相比也有所下降,这一变化和匈奴威胁的减弱以及西域战略重要性的下降密切相关。自西汉武帝通西域以来,汉廷对西域的行动均和解决匈奴问题联系在一起。东汉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匈奴势力对东汉帝国周边的威胁大大降低。但北匈奴的存在和侵扰仍使东汉帝国不得不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和向背。正如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的不断侵扰,耿秉所指出的那样:"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很明显,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控制西域,而要控制西域又必须牢牢控制通往西域孔道的凉州。在这种战略态势下,东汉初朝廷对凉州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还是相当关注的。随着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的西遁,困扰两汉的匈奴问题大大缓解,匈奴已不再构成东汉帝国的致命威胁。东汉帝国周边战略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自然导致了西域战略地位的下降。东汉一朝对西域的经营,远不如西汉那么卖力;对西域的控制也是时断时续,很不巩固。这固然有东汉国力下降的因素,但也是西域战略地位下降使然。西域战略地位下降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东汉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三
正是因为山西的政治地位下降,朝廷对凉州的重视程度相对减弱,才会在第二次羌汉战争初起时,东汉朝廷弃守凉州之议甚嚣尘上。东汉政府在弃保之间摇摆不定,很大程度上因为朝廷这种徘徊不定的态度,再加上凉州"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和凉州的地方利益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并无守战意"、"畏恶军事"、"皆不肯专心坚守"。以至于原本起事时人数不多,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军事、政治意图混乱不一的"羌患"愈演愈烈。最终造成"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军费耗资达240余亿,连绵12载之久的巨大灾难。
在这次羌汉战争中,东汉政府虽然由于要确保三辅安全和防止凉州地方势力坐大等原因,没有采纳放弃凉州的建议,但实际上还是选择了部分放弃的政策:即在永初五年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大大损害了凉州士民的切身利益。举家迁徙他乡对凉州百姓来说,不仅意味着心理和日常生活的不习惯,而且会直接带来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正像王符所说的那样:"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亡失财货类多灭门,少能还者。"正因为如此,百姓多"不乐去旧",不肯迁徙,于是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徙民,"发民禾稼,发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其为苦痛,甚于逢虏",在兵祸之外,又遭受了更大的苦难。这种部分放弃的收缩政策不仅无助于"羌乱"早日平定,反将凉州广大民众推到了东汉政府的对立面。所以在下诏内徙后不久,即永初五年九月,就有汉阳郡百姓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起义,对抗东汉政府,投向羌人一边。这样一来,羌汉战争已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战争。东汉帝国的内部冲突深深卷入到羌汉战争中来,使局势更为复杂,平定"羌患"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困难。
东汉政府的收缩政策和在羌汉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凉州地方利益的漠视,引起了凉州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王符认为那些抱持关东本位主义、轻言放弃凉州的公卿大臣是"痛不著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故兢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羌",如果"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切急如边民者,则兢言当诛羌矣"。痛斥那些"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哉!"他呼吁中央政府抛却狭隘的关东本位主义,平等对待东西之人。既然东西皆为帝国子民,那么"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乎!","圣王之政"就不能厚此薄彼,而应"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
可以说正是东汉帝国内部东西矛盾的存在、东西地位的升降以及与此相关的收缩政策加大了平息"羌患"的难度,成为羌汉战争长期延续的一大主要原因。反过来,羌汉战争又必将加剧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长期而频繁的羌汉战争不仅使地当边陲的凉州饱经战火,连山西的腹心地带---三辅也是屡历兵燹之灾,五次羌汉战争,后四次均波及三辅。由于战乱,山西居民大量死亡或远避他乡,导致这一地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王符在《潜夫论实边篇》里描述第二次羌汉战争刚刚平息以后凉州的情形时说:"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万里,空无人民。"顺帝永和五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三辅人口只及西汉最高峰值的22%(和帝末,东汉总人口就已恢复并接近西汉的最高水平)。东汉的总人口在经历了殇、安、顺、冲、质诸帝时期的停滞不前之后,到桓帝永寿二年又恢复并超过了和帝末的纪录。但广大的山西地区,由于羌汉战争持续不断,局势仍很严峻,缺乏人口增殖的有利环境,所以人口恢复乏力。以三辅地区的长陵县为例,西汉盛时曾拥有和户数50057,口数179469,而到东汉末灵帝光和年间,领户竟不盈四千。虽然后汉的户口隐漏情况比较严重,但数字相差如此悬殊,也可见羌汉战争对山西地区破坏之大。
战乱本已使很多山西官僚世家遭受重创,逐渐败落。而自和帝以来,东汉政府又规定郡国察举以人口多寡为标准,这一改革看似公平,实际使人口最稠密的山东地区在入仕机会上占有了更大的优势。山西人口的大量减少,直接后果便是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降低。山西官僚世家的没落以及山西人士入仕机会的减少,都使东汉帝国的中央政权中能够代表和维护山西利益的政治势力大降。山西的政治影响力在立足于关东本位的东汉帝国大大减弱了,山西势力似乎再也无力向关东独尊的政治格局挑战。
人口的减少使山西地区人口密度大降,连一向人口稠密,所谓"郊甸之内,乡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的三辅,在东汉中后期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旷土。庞参在永初四年的奏记中称:"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崔成于桓帝初的《政论》中也说:"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他们显然已将三辅地区视为与地处边疆的凉、幽两州类似的荒凉之地。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汉族人口下降、地广人稀,另一方面被东汉政府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人口比例大为提高。山西地区汉人和羌人等少数民族之间这种人口数量上此消彼长的趋势以及分布区域上杂居并处的格局,为山西地区特别是凉州一带的汉人羌胡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一地区出现了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蛮夷化"倾向。
我们知道在胡汉杂居的客观情况下,是否"蛮夷化"及其程度深浅还和汉族居民的文化素质有很大关系。例如同为以军功著世的凉州政治精英,皇甫规、张奂就与董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和行为方式。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乃是文化素质高下的差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世代官宦、儒学传家的人物,皇甫规曾"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张奂更是"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还将"浮辞繁多"的牟氏章句删为九万言,两人皆具有相当高的的儒学素养。而董卓则家世无称,父仅官至颍川轮氏尉,董卓"少好侠"、"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未闻有何学养。凉州居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这和凉州居民的来源有很大关系。自汉武帝开边以来,西汉政府大量移民西北,这些移民多为底层平民或罪犯,文化素质较低。而东汉一朝弛刑徒徙边已成定制,正像班超所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再加上许多地方文化精英因为长期的"羌乱"而内迁,更使凉州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每况愈下,所以在东汉末的社会上形成了"凉州寡于学术"普遍看法。文化素质低下的广大凉州居民在羌汉杂处的环境下更易于沾染羌胡之风,山西地区的"蛮夷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这点从现在的考古材料上也能得到旁证。
安帝元初年间东汉政府的兵制改革使东汉帝国在军事上更加倚重凉州兵;中央政府为应付羌汉战争,屡兴武猛之选,一批凉州将领在羌汉战争中脱颖而出,逐步控制了东汉王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山西逐渐沦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地区。这些变化使得本来就"忘战已久"的山东人士更加疏远战阵之事,与山西的隔膜日增。东汉帝国内部东西之间越来越形成两个社会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的区域。
山西地区政治地位的下降,社会文化的"蛮夷化"倾向,高尚武力、寡于学术的民风都让山东人士产生了轻视山西、视其为化外的心理。东西之间隔阂日深,东西矛盾以羌汉战争为催化剂日趋激化,最终到全面对立的程度。
正是基于这种东西矛盾的发展,山西地方势力对以山东为根本的中央政权离心力日增。凉州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羌乱",最后与羌人合流,共同对抗东汉中央政府。如果说第二次羌汉战争中与羌人一起对抗东汉政府的只是像杜琦、杜季贡、王信这样没有多少背景的普通凉州百姓,那么到了第五次羌汉战争时,则有一大批凉州地方实力派卷入"羌乱",并逐渐掌握领导权,最后羌人只是他们对抗中央而加以利用的一支军事力量,仅处于胁从地位。这次战争与其称之为羌汉战争,不如将其视为凉州地方对抗中央的割据战争,或许更准确些。
东汉人的地域观念甚为浓厚,地缘关系常和政治势力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山东士大夫群体的所作所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东汉中后期逐渐崛起的以武功名世的凉州政治势力,关东人士一直抱着猜忌、怀疑的态度,这在东汉末的政治生活中有生动的反映。陈勇的《凉州三明论》一文就精辟地分析了即使像皇甫规、张奂这样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文化修养和立身行事方面均与一般党人名士无异的凉州之士也和关东的党人名士存在着严重的隔膜。东汉士大夫的地域分化及党人名士强烈的地域意识都大大制约、压抑了凉州人士在中央政治舞台的活动和影响。这种压制当然只会增加山西对中央的离心力。
一方面是山西地区对中央的渐行渐远,一方面是关东官僚士大夫对这一趋向的不思补救、反倒火上浇油。东西矛盾对立发展到高潮,终于酿成了对东汉中央皇权造成致命打击、对关东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董卓之乱。
四
董卓之乱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南北矛盾逐渐代替东西矛盾上升为关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矛盾。在这一过渡的初期,东西对立的情绪仍然依稀可见,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凉州贾诩其人其事这一具体个案来看看东西对立现象在历史屏幕上投下的最后的影子。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三国志》本传中称他"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谓诩有良、平之奇"。后"察孝廉为郎",不久因病去官返乡,时约在熹平二年。此后一段时间他的经历史书无载,估计是投身董卓军中做幕僚。因为当董卓进京、自官太尉后,他是以太尉掾身份出现的,后迁为平津都尉。初平三年,董卓被刺身亡,由于主政中央的王允等人善后失计,逼反了董卓部下还攻长安。在这一行动中,贾诩是凉州军人集团的谋主。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裴松之指责他:"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衰,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而另一方面,贾诩入长安后官拜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救",史书称"出天子,佑护大臣,诩有力焉",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又在极力维护东汉中央政府。如何看待贾诩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呢?其实如果我们考虑到东汉末年东西对立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贾诩之举了。贾诩兴谋的初衷并非要颠覆中央政府,他所反感的主要是董卓死后以王允为代表把持中央朝政的党人名士集团所表现出的狭隘的关东本位主义和对凉州人的极端敌视态度。兴谋入关对贾诩而言,并不是要颠覆朝廷,而是作为凉州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救、自保的一种权宜之计,所以在李、郭等人"欲以功侯之"时,他才会说:"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凉州军人集团由于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以毫无来自关东地区的支持,不足以领导群伦,不会在中央政权中有大的作为。所以他尽量和凉州武人保持一定距离,行事低调、自抑以求明哲保身,当要被委以尚书仆射的重任时,他推辞道:"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
当董卓旧部渐次散灭、中原群雄割据时,贾诩也在寻找新的归宿,在这一选择过程中,东西对立的阴影也起了很大作用。面对当时中原最大的两股割据势力---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贾诩在两强对峙于官渡、袁强曹弱的形势下,最终选择了曹操集团。以往论者多将这一选择归于贾诩的远见卓识、智计过人,而未注意分析这一选择背后的东西对立因素。毛汉光先生在《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逐一分析了汉魏之际几大割据势力的政治背景及社会基础,总结了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不同之处。袁绍本人是典型的党人名士,其集团关东本位意味最浓,这一集团对贾诩之类凉州人士有强烈的敌意,存在巨大的心理距离。而曹操则出身阉宦之家,"自以本非严穴知名之士",其人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均和一般党人、士大夫迥异,格格不入,著名的《魏武三令》就是其典型写照。他在用人方面能够突破狭隘的地域意识、不拘一格,曹操集团具有远比袁绍集团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凉州人士眼中曹操"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对曹、袁两大集团的这种差异,贾诩自然心中了然,所以才会最终投靠曹操集团。在曹操集团内,贾诩也确实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曹丕代汉后,贾诩官居太尉,陈寿称他:"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只亚欤!"其实贾诩在加入曹操集团后,东西对立的心理阴影依然笼罩着他。本传中说他:"自以本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从这段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贾诩在构成朝臣大多数的关东人包围中倍感孤独与隔膜;在朝廷中有强烈的不安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贾诩的经历,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出东汉末的东西对立对当时人的心理影响何等深巨。
结论
两汉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西汉王朝正是由于较好地协调了东西矛盾、使帝国东西两大部分能够密切配合,才造就了全盛之局。而东汉王朝,对山西地区不予重视,帝国东西之间严重失衡,发生了偏枯之病。其结果是"山西得不到山东经济的支持和文化的滋润,社会日趋衰落。但山东的经济、文化,最后却遭到山西武力的严重破坏。东汉帝国的根本在山东,山东的经济、文化既然遭受破坏,整个帝国的基础产生动摇,自然难逃乱亡的命运"。东西矛盾关乎东汉帝国国运盛衰,而羌汉战争正是推动这一矛盾发展、演变的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羌汉战争是导致东汉之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