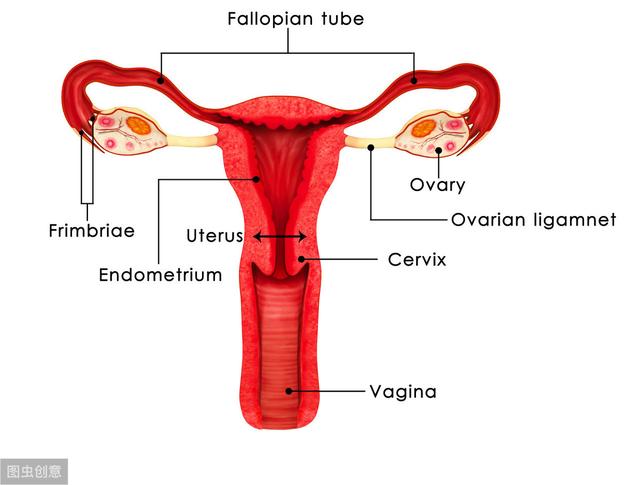◎连城
关注北影节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田中绢代执导的《月升中天》与影迷见面,这部与小津安二郎的《宗方姐妹》形成对读的作品,表达出田中绢代作为女性导演的独特视角,也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她的导演作品。
1
田中绢代是日本电影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其电影生涯横跨了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的两个黄金时代,出演了250部作品,合作的都是日本影坛的一流导演:小津安二郎、成濑巳喜男、木下惠介、清水宏、岛津保次郎、五所平之助等,她更是沟口健二的缪斯,两人合作的《雨月物语》《西鹤一代女》《山椒大夫》是影史的不朽名作。
田中绢代作为演员的光芒过于耀眼,以至掩盖了她作为导演的光彩。她并非第一位日本女导演(第一位为坂根田鹤子,1936年首次执导了一部作品,已失传),却是战后第一位女导演及作品在主流院线大规模上映的第一位女导演。1953年到1961年间,她共执导了6部作品,日本银幕上的女性从此有了自己的视角,彻底摆脱了男性的凝视,从而能够更切身和坦率地正视女性自身的存在,这意义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田中绢代的导演事业顺风顺水,多少借助了她大明星的特权,这使她能够获得拍片的各种资源并获得名导们的支持,如成濑让她担任《兄妹》的第三助理导演,使她磨练了导演经验;木下惠介为她的第一部作品《情书》(《恋文》)撰写剧本;她的第二部作品《月升中天》更是得到当时日本导演协会会长小津安二郎的大力支持,小津不但撰写剧本,还大力帮她排除各种干扰,创造良好工作环境,使其可以全身心投入导演工作中。
巧的是,这最大的干扰恰恰来自于她的恩师沟口健二,沟口此前积极鼓励自己的场记坂根田鹤子成为导演,现在却无视田中绢代1953年已经成功执导了佳作《情书》的事实,反对她做导演:“绢代拍不了电影”,意思是她没有足够的能力拍电影。时人看出这是沟口出于“如果田中绢代一直把导演工作做下去,一旦失败就会损害她这个大明星的名声”这种良苦用心以及“一种占有欲——沟口自己一直可以使用作为演员的田中绢代”的私心才发出这样的声明。对于沟口的PUA,田中绢代没有上当,否则就不会有后续的五部导演作品了,并且她此后也再没有出演沟口最后的几部作品。
2
小津原想自己拍《月升中天》,因故没成,尽管如此,成片中还是有很多小津元素,如题材(嫁女)、构图(榻榻米构图)、机位(低角度机位)、演员(小津御用演员笠智众出演),甚至在“新VS旧”的主题上,也和小津的《宗方姐妹》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倒——《月升中天》对《宗方姐妹》和小津的晚期嫁女题材作品进行了颠倒的表现。
比如,小津晚期作品里处于前台的永远是老男人,而《月升中天》中笠智众被推到了背景,走上前台的是家中的三个女儿,特别是最年轻活泼的妹妹北原三枝。《宗方姐妹》的主题是保守的姐姐田中绢代VS新潮的妹妹高峰秀子的新旧对比,妹妹说:“不管是好是坏,不跟上潮流就要落后于人。我不想落在周围人后面。”姐姐说:“落后又有什么不好?真正崭新的东西永远不会变老变旧。”小津的态度更倾向于姐姐。而《月升中天》中,田中绢代让朝气蓬勃的妹妹北原三枝成为绝对的主角,她的青春和朝气几乎溢出银幕,深深地感染了观众。相对守旧的姐姐和父亲,只有寥寥几场戏。
就连“女儿出嫁”的内容,《月升中天》也和小津作品大异其趣。小津作品中忧虑和操心女儿婚事的始终是年老的父母,而《月升中天》中妹妹北原三枝为二姐杉叶子的婚事简直操碎了心。在小津的作品里,女儿往往不愿意离开父母离开家,而《月升中天》中,妹妹北原三枝想快快离开宁静的奈良的家去东京,她急切让姐姐亡夫的弟弟、也是默默爱恋着她的昌二赶快在东京找到工作,这样她就可以随他去东京生活。昌二将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机会拱手让给朋友,她那急火攻心的惋惜和生气的样子让人目瞪口呆。
影片中,一对年轻男女在宁静奈良古城望月的场景,表面上是正常不过的约会,实际却成为女性自我觉醒的契机。庄重内敛的二姐杉叶子在妹妹的强力安排下勉强赴约,接下来就接受了男方,很快就跟着男方去了东京生活,结尾处妹妹和昌二的月下漫步,则是在确定奔赴东京后对奈良的告别,此时妹妹内心里涌动的念头,必定是“向东京去、向大都市去,投奔爱情、投奔年轻、更有活力、更西化的城市(网友彼得潘诺夫斯基语)”。
这家人是战时从东京疏散到古典的、传统的、保守的、落后的、宁静的古城奈良的,父亲和大姐对这样的岁月静好甘之如饴,可是妹妹北原三枝却更向往现代的、先锋的、充满泥淖、充满脏污、从废墟中崛起的东京。于是,两个月上柳梢头的约会故事,实际上标示的是两种生活的抉择:是向往脏污热闹的东京还是享受古老宁静的奈良?这就是《月升中天》的新VS旧主题,妹妹北原三枝和大姐山根寿子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日本战后最早的一部“上京”(日本人从小地方到东京谋发展,类似我们的京漂、沪漂)电影,影片中新旧对比的旨趣已经不同于小津,这或许正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区别,反映的是两位导演对于战后日本社会的不同看法,田中绢代将一个十足小津味道的故事翻出了新意。
3
尽管被小津誉为“佳作”,沟口也在看后主动打脸:“拍得真不错,以前我反对拍这部电影,认输了。”《月升中天》说到底属于家庭轻喜剧,要了解田中绢代的导演才华,我们终究还是得到《情书》《夜里的女人》《永恒的乳房》《漂泊的王妃》和《阿吟大人》这几部严肃作品中去寻找。
田中绢代1953年的导演处女作《情书》,透过一对兄弟的职业——哥哥为美国大兵的日本情妇代写情书,弟弟的书摊专门搜罗和转卖美国大兵带给日本情妇的时尚杂志——带出了二战后“堕落女性”受日本社会歧视的议题,同时将日本男权社会的伪善与懦弱暴露无遗:受过教育的两兄弟是知识分子和社会正义的代表,他们靠这些女人维生,却对她们以及她们与美国士兵的关系大加批判,哥哥痛心疾首于她们的堕落,弟弟则要帮助她们走上正道。
讽刺的是,哥哥曾经是参战军人,他没有反省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其实比他所批判的女性堕落的罪行要可怕得多。导演借助自己饰演的一个老年妓女对大哥的说教嗤之以鼻的场景,点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在艰难时世里,生存高于一切道德和说教,从而对这些堕落女性寄以关怀。此外,本片也说出了“我们所有日本人都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台词,这在承认日本战争罪责的日本电影中颇为鲜见,实属难得。
她的另一部关于战后堕落女性主题的作品为《夜里的女人》,它和沟口健二的《夜之女》形成了呼应,也构成了颠覆。影片讲述了战后从良的妓女无法摆脱命运的残酷、难以融入正常社会。有意思的是,女主在不断被放逐的过程中,自我的意识反而不断增强了,最后拒绝了园艺师的求婚选择独自生活下去,冥冥中似乎意识到了与社会同构的男女关系往往正是女性受苦之源。正是这种女性的自觉自省意识,使影片超越了沟口的《浪华悲歌》和《祇园姐妹》中女性的悲剧宿命。
《漂泊的王妃》以女性的视角回望一段复杂动荡的二战史。日本贵族之女嵯峨浩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因政治原因而结合的婚姻,却在乱世中成就相濡以沫的爱情。影片的重头戏是伪满倒台和日本投降后嵯峨浩带着幼女和傅仪的妃子婉容颠沛流离的漂泊命运。贵族之女嵯峨浩和婉容被还原为俗世的女人,在战争的威胁下命如草芥,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尽管如此,她们仍竭力维持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影片还礼赞了女性在大难来临之时的互助互帮。影片作为史诗片太过于粗疏,却谱写了一曲女性视角的反战悲歌。
《永恒的乳房》被认为是田中绢代的最佳作品,改编自拍片前刚去世的日本女诗人中城文子,讲述了她因癌症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之后的心路历程。中城文子生命的最后阶段不断地经历着丧失:先是离婚,然后是和自己老情人的生死离别,被疾病所缠绕,然而正如作家西西在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后写出名作《哀悼乳房》一样,中城文子也鼓起勇气写出《乳房丧失》,让惨淡的生命在最后的时光里焕发出非凡的激情与欲望。这部作品以其大胆的题材、超前的女性意识,走在了时代的前头,在当下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田中绢代导演的最后作品是一部时代剧《阿吟大人》,讲述的是茶道大师利休的养女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年轻武士的恋爱悲剧,她的出身和恋爱使她的命运卷入了三重压迫:她是利休的女儿,因而成为丰臣秀吉和利休茶道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她对天主教徒的爱情,使她成为政治权力消灭天主教运动的斗争的牺牲品;她的美貌成为丰臣秀吉利用权势性掠夺的牺牲品。阿吟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自觉,最后选择自杀来维护自己的高贵与尊严。
片中阿吟和年轻武士出逃的一段拍得极美,令人想起了沟口健二的《近松物语》和筱田正浩的《心中网天岛》的情侣同行场景,年轻武士为阿吟洗脚并在她伤口上搽抹药膏的温柔场景,以及女性体恤女性命运的场景(阿吟目送岸惠子饰演的、被绑在马上将执行十字架绞刑的不屈的女教徒,满怀敬畏地说:这个女子真有活力!),在沟口和筱田的作品中是不可能见到的,只有同为女性的田中绢代才有这种感性、细腻和温暖的笔触。
田中绢代的六部电影,题材不一,类型驳杂,有温馨浪漫的家庭轻喜剧《月升中天》,有对战后日本社会进行挖掘的现实主义作品《情书》和《夜里的女人》,有类史诗片《漂泊的王妃》,有时代剧《阿吟大人》,还有三幕式悲剧《永恒的乳房》,没有一以贯之的风格,电影语言和技法也笼罩在小津和沟口等名导的阴影下,因此她很难称得上“电影作者”。
但她作为导演,敢于突破界限,将女性声音带入男性当道的日本电影,意义非凡。她执导的电影中的女性,不同于她们在男性导演作品下的形象,她们承受着男权社会施加于女性的不幸命运,但与那些男性导演不同,田中绢代积极地赞美她们的自我觉醒的意识和自我改造、自我革新的冲动,并且,她礼赞女性之间的团结和互助精神。
更重要的是,她作品中的女性,面对不公的命运,没有一个自怜自哀,每一位都挥洒出强大的激情、迸发出强烈的欲望、焕发出坚韧的活力,还有,对自我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