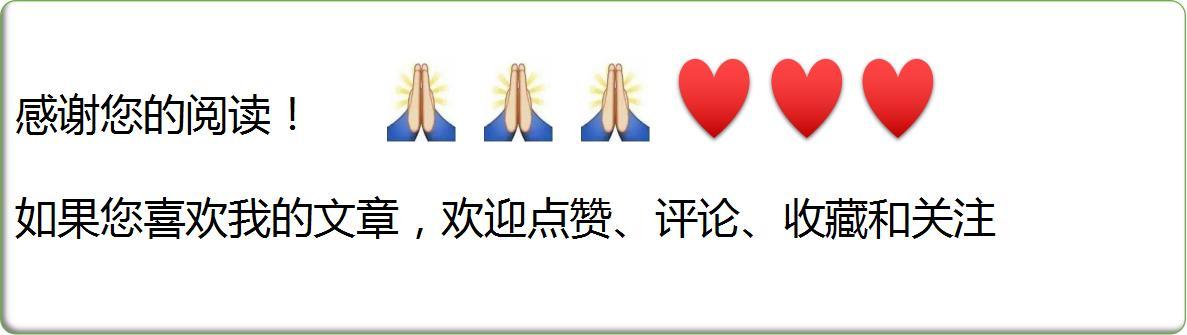郛堤城遗址位于黄骅市市区北部,在 羊三木回族乡 刘皮庄南2公里。该古城总面积为186813平方米,城址已风化残存,城内已辟为农田,城墙呈方形,东南西北各约一华里,四面城墙残存;采集物有绿釉残陶钵、夹砂红陶、三棱铜箭镞、古盔等。
在相关史书记载及研究中,多数被当做战国-汉时期军事防御城池,但现在出现大规模儿童墓葬的发现,对此古城单纯为军事城池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根据所采标本及文献记载初步定为汉--战国。据《盐山新志》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于此置合骑侯国,称合骑城。《长芦盐法志》则称系为防狄卢而设屯兵之所,称伏狄城,当地讹称武帝城,今称郛堤城,1982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言
郛堤城,民间亦称武帝城。坐落于黄骅市城区西北处,过去这里远离村镇,地势低洼,人烟稀少,芦蒲摇曳,蓬蒿丰茂。土城墙上,荆棘丛生,荒草漫顶,多狐穴獾窝蛇洞。白天风吹草动,虫吟蛙鸣;晚上磷火闪烁,鸮叫狐嚎,给人一种荒凉、萧瑟、神秘莫测之感。因而衍生出许多狐仙、鼬精的神话传说。很多人或写文,或赋诗,多有表述。我试图以史学的观点,对郛堤城之名,郛堤城之实,郛堤城仅是一座防御性的军事城址吗?分三部分做一个肤浅的解读。
郛堤城之名
郛堤城之名究竟源于何处、成于何时?无有确解,史学界和民间有多种说法,目前归纳而言大致有一下四种。《黄骅县志》(1990年版)和互联网《黄骅在线》、《360百科》均称:“据《盐山新志》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封公孙敖为合骑侯,于此地置合骑侯国,称合骑城;《长芦盐法志》则称:系为防狄卢而设的屯兵之所,称伏狄城,当地讹称武帝城,今称郛堤城。1982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科学出版社》再版的《长芦盐法志》却记载:“伏猗城, 在盐山县韩村北利国场界,相传筑以防猗卢者。”
关于合骑城就是郛堤城之说
据汉书记载:公孙敖,西汉将领(?—前96年),北地郡(今属甘肃)义渠县人,最初以骑郎的身份侍奉汉武帝刘彻。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匈奴侵犯上谷郡,掠杀吏民,朝廷于是派遣时任太中大夫的公孙敖担任骑将军,与车骑将军卫青、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自率领一万骑兵,出击匈奴。公孙敖从代郡出兵,与匈奴交战,阵亡七千名骑兵,因此被判死罪,后缴纳赎金,免罪为民。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天,公孙敖担任校尉(一作护军都尉),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因战功受封合骑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元朔六年(前123年),公孙敖担任中将军,随同大将军卫青两次从定襄(今属山西忻州)出兵攻打匈奴,但未立战功。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公孙敖担任将军,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从北地郡(在今甘肃环县)出兵,攻打匈奴。汉军出塞后分兵前进,离开北地郡二千多里后,公孙敖在沙漠中迷路,霍去病孤军深入,越过居延海,抵达祁连山,歼灭匈奴三万多人。公孙敖因延误与霍去病约定的时间,再次判处死刑,公孙敖缴纳赎金后,废为平民。元狩四年(前119年),公孙敖再次担任校尉,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没立战功。太初元年(前105年),公孙敖担任杅将军,在塞外修筑受降城。天汉四年(前95年),公孙敖再次担任杅将军,率领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从雁门关出发,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汇合攻打匈奴。汉军进军到余吾,李广利与匈奴单于在余吾水滨交战数日;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失利,损失士卒过多,于是都收兵回朝。公孙敖回朝后,因损失士卒过多,被判处死罪。公孙敖诈称自己已死,逃亡到民间数年。后来发觉,遭到逮捕。太始元年(前96年)正月,公孙敖因受到其妻巫蛊事件牵连,腰斩而死,全家被灭。
我们看到公孙敖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封合骑侯,到元狩二年(前121年)废为平民,不足四年时间,且史书上记载其多在西北与匈奴交战,曾在塞外修筑受降城,在那个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年代,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不大。何况此虽是一座土城,在那个靠肩挑手提的时代,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相当长的时间。不知《盐山新志》“于此地置合骑侯国,称合骑城”此说,依据何来?
关于伏狄城是郛堤城之说
狄卢。狄,古族名。春秋前,主要分布在河西、太行山一带,春秋时,逐渐东徒,活动于齐、鲁、晋、卫、宋、邢等国之间,与诸国有频繁的接触。公元前七世记时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部,各有支系。因主要分布在北方,通称为北狄。以游牧、狩猎为业,善骑射。秦汉以后,“狄”或“北狄”曾是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之一。“狄卢”二字却查无此出。是否是“狄族”之误呢?如此叫伏狄城也有道理,只是史书上却无记载。
但历史上有“猗卢”这个人,是否猗卢与郛堤城有关系呢?猗卢——拓跋猗卢(?-316) 西晋时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力微之孙。其父为拓跋沙漠汗,拓跋猗㐌、拓跋弗皆为其兄弟,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皇帝的先祖之一。295年,当时的鲜卑索头部首领,也是猗卢之叔拓跋禄官将国土分为三部,由猗卢统治西部。猗卢善于用兵,向西打败匈奴、乌桓,并将部落之事,委诸汉人,汉人因此纷纷归附。304年,与猗㐌击败刘渊军,和晋军会师。305年、307年,猗㐌、禄官相继去世后,始完全统领索头部鲜卑。310年,支援晋将刘琨击败鲜卑白部及铁弗刘虎,与刘琨二人结拜为兄弟。刘琨推荐猗卢为大单于、代公。猗卢又向刘琨索取土地,由是猗卢的势力日益强盛。其后数年间,与刘琨联合对汉赵作战。312年,大破汉赵军于晋阳(今中国山西太原)。313年,猗卢以盛乐(今中国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都;平城(今中国山西大同)为南都。314年(建兴二年)被晋愍帝进封为代王。因猗卢欲立少子比延,于是出其长子拓跋六修(xiū)且黜其母,引起六修及其母族反弹。316年,猗卢召唤六修而六修不至,遂率军讨伐,反为六修所败。猗卢微服流落民间,为人识破而暴崩。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称帝时追尊先祖,追谥猗卢为穆帝。若按此说,郛堤城的修建年代当为西晋,但这和权威部门两次勘察认定大相径庭。
关于武帝台与郛堤城之说
至于民间武帝城之名,渊源大概和相传汉武帝东巡观海有关吧?《北魏地形志》载:“章武有武帝台”,《畿辅通志》(康熙版)载“武帝台在盐山东北七十里”。《盐山县志》(同治版)载:“武帝台有二,其一无考,岿然,独存者,惟盐山之一台”。《魏土地记》载:“章武县东百里有武帝台,南北有两台,相距六十里,俗云汉武帝东巡海上所筑”。《大清一统志》载此为南台,北台在今沙井子村,已被夷为平地。《郡国志》记载,汉武帝东巡曾祭祀麻姑神。后人循祠名而居,后村名演变为大麻沽。而武帝城之名,史书上却未见记载。“武帝城”与“郛堤城”读音相近,民间口耳相传,难免产生了谬传。
关于位于浮水之畔得名之说
《津门考古》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至新莽建国三年(公元前109-公元11年)黄河入海地点在今黄骅市境内郛堤城东,其河道即黄骅、盐山之间的古河床。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浮阳县,因在浮水之阳而故名,治在今河北沧县东关。两汉、魏、晋各代均属勃海郡。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析勃海、章武二郡地设浮阳郡,浮阳县为郡治。隋开皇十八年,浮阳县改称清池县。“水经注”中浮水故渎即黄河古道。现黄骅境内有新老两条石碑河,老石碑河元延佑五年(公元1316年)开挖,因河口立石而名。新石碑河为民国(公元1948年)开挖,西起我市大浪白村,因河源于老石碑河故道而得名。据说,老石碑河故道就是原黄河古道,诚然,同一条河流会因上下游所处的地理位置或时代不同而名称各异,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新石碑河就在郛堤城的北城墙下流过。是否是这座位于古浮水河堤边的古城,原本是当地老百姓指认地方的叫法,慢慢地演变成了它的名称“郛堤城”了呢?
郛堤城之实
2011年6月初至7月底,黄骅市邀请保定市文物管理所会同黄骅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勘探队,对郛堤城城址分为古城墙和古城址内遗迹两区进行了勘探。勘探面积30余万平方米,发现遗迹点13处。相关情况如下。城址平面近似方形,城垣为版筑夯成,历经几千年的风蚀雨刷、人为破坏,留存至今,其中南城墙、北城墙保存较好,残高4-5.4米;城址四面环水,其中西、北、东三面疑为早期护城河,因多年雨水冲刷,现已淤满泥土,夯土层分为上、中、下三种不同类型,城墙上层夯土,用黄褐粉砂土夹杂大量陶片、贝壳版筑夯成,陶片纹饰包含素面、细绳纹、粗绳纹、网格纹等,陶质有夹砂红褐、泥质灰陶等,可辨器型包括豆、瓮、盆、瓦当、筒瓦、板瓦等。城内遗迹分为四个类型:河塘、建筑基址、灶、灰坑等。其中,河塘分布在城内四角,中间用水沟联通;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城中部、北部区域;灰坑分布于建筑遗迹外侧。此次勘探共发现建筑遗址9处、年代初步推断均为战汉时期遗迹。详细情况:河塘位于城内四角,水从西北角水门引入河塘,以逆时针方向,流至西南角河塘、东南角河塘、东北角河塘。建筑遗址共计16处,包括建筑基址,局部残存墙体夯层,夯筑方式为灰褐色沙土夹杂大量泥质、夹砂陶片及蚌壳混合夯筑。灰坑:共发现6个,灶仅发现1座,平面近似圆形,直径约1米。未发现手工作坊遗址等工商业区,说明此地居民较少;在南、北城墙外侧,城址内采集到了大量战汉时期的铜箭镞,说明此城在战汉时期发生过战争;东城墙内高台有踩踏面,西城墙内有大面积的河塘,与民间流传的“西边饮马池,东边站兵台”相合。调查小组依据地表暴露遗迹、遗物,将城址年代定位战国-汉。此城的功用是作为防御性的军事城池而存在的。
2014年8月7日至8月28日,黄骅市又邀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会同黄骅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郛堤城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对城址西南角、城址东门及东城墙、和城内7号建筑遗址进行试掘。

通过试掘发现,城墙大致分为墙基、墙体、和护坡三部分。墙基出土遗物极少,墙体堆积则出土较多遗物,如夹砂夹蚌红陶釜残片,泥质灰陶罐、陶豆残片,夹砂灰陶绳纹板瓦,夹砂红陶板瓦以及一定数量的蚌壳,这些遗物以战国时期为主,最晚的陶片为汉代。据此而又未见晚于汉代的遗物,应可初步推断其最晚始建于汉代。
通过对7号建筑遗址试掘发现,探方的地层堆积分为五层。第一层为扰土层,为灰褐色粘土,呈水平状堆积,包含有众多的板瓦、筒瓦及瓦当等建筑构件,大量的陶片,可辨器形有豆、罐、盆等,并有少许青釉瓷片和铁器。第二层为淤积层,为淡黄色细砂土,该层包含物不多,有少许建筑构件残片,还有零星的日常生活用陶片。第三层为隋唐文化层,出土遗物有隋唐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建筑构件,还发现有生活实用器罐、盆、豆等器物陶片以及青瓷碗残片、铁器和铜器等。第四层为战汉文化层,包含有较多的红烧土块和炭粒。出土遗物有战汉时期的瓦当、筒瓦和板瓦等建筑构件,还有大量战汉时期的陶片(陶片多为燕国红陶釜、豆等生活用器),可辨器形有有釜、豆、钵、罐等。此外,还发现一些铁制兵器,如铁剑和铜制武器,青铜箭簇等。各地层堆积中还发现较多的兽骨和蚌壳。
最后考察认定:发现并确定郛堤城为沿海地区一种新的筑城方式。城址最晚初建于汉代,属于一座防御性的军事城址,筑城前该地已存在战国时期生活遗址,至迟沿用到隋唐时期。
通读两次《郛堤城勘察报告》,我同意保定文物管理所和黄骅博物馆的第一次结论,郛堤城的初建年代,应为战国时期或者是战国早期。因为郛堤城的墙基部分,基本没有遗物,墙体夯土层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墙体堆积中发现大量战国陶片集中在上面部分,(多为燕国红陶釜、豆等生活用器)。郛堤城如果初建于汉代,根据郛堤城的地面埋藏遗留物情况,其墙基部分也应有大量的战国时期遗物,而墙基部分仅为素土,遗物极少,这说明郛堤城的初建应为战国早期,而墙体堆积中的大量战国陶片,基本都在上面部分,证明是后来汉代对城墙加固,增高,修补所为。
据有关史书记载,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古黄骅境南部属齐国,无棣邑。北部属燕国。黄骅正处于齐、燕两国国境边防之地。说起齐、燕两国,作为邻邦,使我们想起了一段历史佳话。据《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载:“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致与燕,······诸侯闻之,皆从齐。”对齐桓公所割之地,燕国曾经筑城以示纪念,后世称为“燕留城”。 唐《括地志》称“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故名燕留。”唐代的长芦县在今沧州市,燕留城位于长芦县东北,说明燕庄公时期燕、齐两国的分界线在沧州东北一带。正是我们黄骅境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燕留城”的具体位置,现今有人说在沧县境,《黄骅县志》载:我市的大闫台村因地处燕、齐界阕,取名燕齐台,后演变为大闫镇台,而燕留城遗址究竟在哪儿呢?当年的孤竹国位于现秦皇岛卢龙县和唐山滦南一代,齐国的国都临淄就是现山东淄博市。至今,从秦皇岛、滦南去淄博途径黄骅是最便捷的交通路线。当年燕庄公送齐桓公入齐境,肯定两国边境线上既没有边防长城(有的历史学者误把被人称为“齐堤”亦称“齐长城”的古黄河大堤当作了齐国北界的边防长城)也没有边城和标志性的参照物,这非常符合黄骅一代的地形地貌。在郛堤城遗址发现的大量当年燕国时代的陶片来看,郛堤城是否是当年的燕留城呢?然而,在两个国家之间,正像有人所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据《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第二十》记载:“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战国策·燕策二》昌国君乐毅篇又载:“(燕)惠王即位,用(听信——编者)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欺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所以把郛堤城定位为一座防御性的军事城址还是准确的。笔者在挖掘现场,曾看到一灶坑和临近的陶井旁边,留存着一堆蚌壳和兽骨,仿佛一队士兵在金戈铁马的战争硝烟中,匆匆吃了点东西,来不及清理现场、打扫一下环境卫生,就赶忙追击敌人或弃城而去了。
郛堤城仅是一座防御性的军事城址吗?
继2016年5月份在郛堤城西北角发现六座瓮棺墓葬后,又在紧邻的郛堤城西北角和郛堤城西面发现面积较大的瓮棺墓葬群。据黄骅博物馆张宝刚馆长介绍,根据探测,已知瓮棺墓葬群面积达一百余亩地,瓮棺的具体数量还不详细,截至目前现已挖掘近百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介绍说:“这个瓮棺墓葬地应该说在全国来讲规模比较大,非常有特色。讲特色一个是它类型很多样,再一个分布很密集,年代很清楚。尤其是它除了儿童瓮棺葬之外还包含了一批成人瓮棺葬,这对我们研究当地两千多年前的丧葬习俗是极为重要的。”葬具除了有专门烧制的瓮棺外,主要是一些生活器具,由陶罐、陶盆、陶釜、板瓦、青砖等等一些生活用具组成。这些瓮棺墓葬的年代根据现场清理、查看,初步判断为战汉时期墓葬群。
瓮棺葬,古代葬俗之一,中国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但日本在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有成人瓮棺葬。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常有儿童瓮棺葬,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居住面下,也有专门的儿童瓮棺葬墓地。
郛堤城脚下瓮棺墓葬群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郛堤城做一个新的解读。
白云翔所长介绍说:“瓮棺葬墓地实际上是郛堤城的一部分,城说明人的存在,墓地的存在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城的时代和这个城当时的繁荣。”这些瓮棺墓葬的发现,足以证明,从汉上推到春秋战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郛堤城周围聚集、居住着大量的古代先民,这就推翻了郛堤城仅是一座防御性的军事城址的推论。据张宝刚馆长介绍:通过挖掘瓮棺墓葬群得知,战汉时代郛堤城附近的土地,板结、坚实,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据此判断,当时聚集,居住在这里的先民肯定不是以农耕为生。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民国十四年《无棣县志》载:“昔太公之封于齐也,赐履步疆,北至于海,课鱼盐利中国,富厚甲天下”。可知,自春秋战国到现代社会,黄骅就有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是渔业。一个是盐业。而经济的繁荣必将引起运输业的兴盛。可见,这座城址的出现,除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外,肯定担负着保卫这一方百姓安全从事渔、盐和水运业的重任。如此推断,郛堤城是那时的港口重地兼为防御性的军事城池也是非常可能的。而作为古黄河的入海口,通过近年来对海丰镇遗址的发掘,大量瓷片和遗物的发现、出土,通过论证,“黄骅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基本上已达成共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黄骅是海上丝绸之路北起点的时间提前的汉、战国时代呢?据报道,最近海丰镇考古挖掘现场附近相继发现了唐、宋的遗址、遗物、
在郛堤城下现已清理出土的近百座瓮棺葬类型多样,既有专门特地烧制的瓮棺也有生活所用陶器,且面目各异。这就足以证明这些瓮棺墓葬所用陶器是在当地烧造的,不是购买的外地运来的批量生活陶器。据介绍,在郛堤城周围及附近村庄很多人发现过窑址的存在,我们期盼着这些窑址的再被发现。
白云翔所长介绍说:“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环渤海地区有类似的发现,从山东到天津,到北京,一直到辽宁。那么这种瓮棺葬它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仅在于埋葬本身,而在于在战国晚期和汉初的时候,这种埋葬的习俗和文化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由此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很简单的瓮棺葬,而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现象,文化交流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的移动,因此,我想这批瓮棺葬的发现,一个进一步证明了城的年代和繁盛,也证明了在战国末年,最晚到西汉初年,汉王朝对这个地方已经是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开发。同时,我们通过这批瓮棺葬也可以(发现),环渤海地区的文化沿着渤海一直到黄海的北岸,然后向东北地区扩展,我想它的重要意义应该是在这里。建议今后加强这个地区的保护,同时展示好、利用好”。
其实,早在2011年,热心黄骅古文化和陶文化研究的姬成强先生在其文章《黄骅有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陶文化》中,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话题“黄骅文化”,可惜当时没有发现有力的佐证以引起有关领导和文保部门的重视。
我国在8000年前发明了制陶技术。商代陶器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制陶业以实用器皿为主,建筑用陶有了新的发展。秦代的陶器品种繁多,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曾经震惊了世界,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汉陶俑和砖瓦制作技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黄河文明的形成期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黄河古文化也可以说成黄河陶文化。通过近现代有关专家的发现、考古、论证,黄河古文化有分布于黄河上游甘肃、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唯独缺少的是没有黄河入海口地区的文化。
姬成强先生在文章中说:“黄骅是古黄河与海水相通的重要口岸,古代的先人们主要依靠水路的交通,不会忽略黄河水运与海上水运的连接处。一条河流不能也不会没有入海口的文化。”姬成强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请有关专家和读者研究和思考的几个问题:“黄骅有陶文化吗?它开始于多少年前?结束于多少年前?黄骅是陶器集散地还是陶器窑区?这里的陶器是本地烧制运往外地,还是外地烧制后运到本地?黄骅的绳纹陶与黄河上游很多地区出土的绳纹陶及台湾、日本出土的绳纹陶外形、绳纹、造型非常一致,如同窑烧制,由此能联想到什么?郛堤城有可能是春秋战国至汉代时期黄河入海口的重要港口及食盐等物资、物流的集散地,也是丝绸之路的北方港口”?最近黄骅大型瓮棺葬墓群的发现、发掘,姬成强先生在几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似乎越来越好回答了。也为解释郛堤城如果仅是一座军事城址为何却埋存着大量战国时期的生活陶片提供了新的思路。
越写越觉得解读郛堤城是一个大工程,不是才疏学浅的我所能做得到的。写此拙文,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更大的关注,我愿足矣。文中谬误,敬请有关方家批评指正。
2016年7月12日 姜梦麟
此文发表于9月19日《渤海新区报》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联系,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