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审定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四年级上册语文第11课《蟋蟀的住宅》第五自然段第二句是:“隧道顺着地势弯弯曲曲,最多九寸深,一指宽,这便是蟋蟀的住宅。”(第39页)最后一段第二句是:“洞已经挖了有两寸深,够宽敞的了。”(第40页)这两句中用“九寸”和“两寸”表述很不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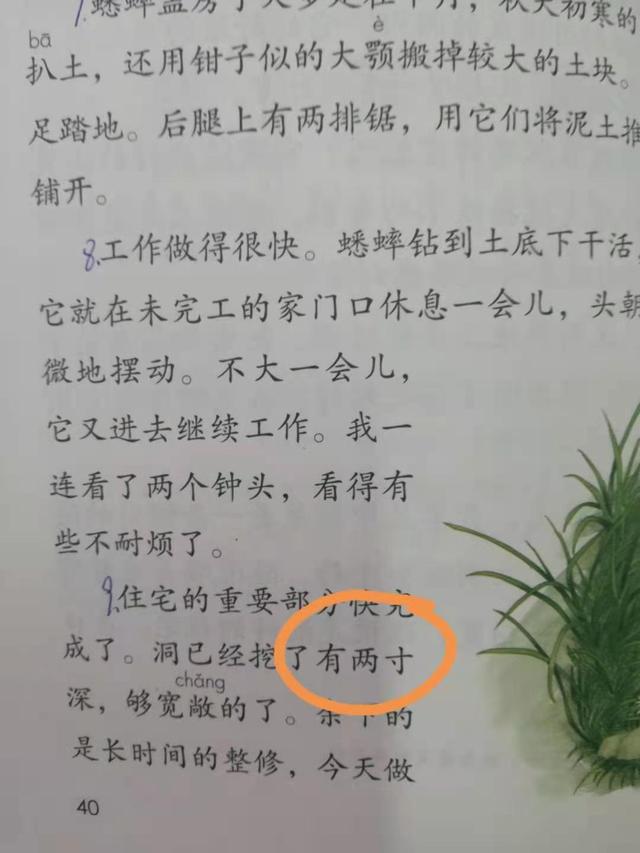
《蟋蟀的住宅》选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100多年前的法布尔恐怕根本就不知道“寸”这个中国独有的长度单位,我一开始猜想他更可能用的是1790年由法国科学家确定,后来成为通行的国际单位制的长度单位“厘米”“分米”“米”。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真正全译本《昆虫记》中,用的是法国传统的计量单位:“法寸”。1法寸约等于0.02707米,12法寸=1法尺,1法尺约等于0.32484米。这样看来,1法尺跟一市尺差不多,但1法寸跟一市寸有明显的差距了。9法寸约等于0.244米,九市寸约等于0.300米,两者相差近6厘米,超过两法寸了,比得上一只蟋蟀的身长了,如此翻译“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上查阅资料显示,《昆虫记》最早的中文译本是在1927年出版,不知道该译本中是否选入与《蟋蟀的住宅》相关的篇目,也无从查证是否用了“九寸”“两寸”这样入境随俗的译法。不过可以想象,较早的中文翻译可能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大多还不知道尚未引进使用的国际单位制,为了便于中国读者对文中描述有比较清晰的感知,而把原文中的长度单位直接转换成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长度单位“寸”。翻译入乡随俗,过去也是常有的事,一些文学名著翻译的早期译本就有把原文中度量衡单位换成我国传统市制单位的译法。当然也有便于人们区分而另外造字的,如把给英寸造一个“吋”字,给英尺造一个“呎”字这样的。
所以,我推测,编入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蟋蟀的住宅》译文应该是至少40年前翻译的。不过事实上1959年6月,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统一中国计量制度,全国开展推广米制,这也是跟国际接轨吧。据我的印象,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更广泛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制”度量衡单位,中小学教科书中逐渐放弃了我国传统的“市制”度量衡单位,比如不再使用“斤”“里”“尺”之类单位,而改用“公斤”“公里”“公尺”之类相对中文化的国际通用的单位名称,后来又进一步统一规范为“千克”“千米”“米”之类单位名称,明确要求中小学教科书不再使用市制单位,也不使用不规范的度量衡单位名称。现在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市制单位“里”“斤”还时常有人用,但“尺”“寸”就极少用到了,在中小学数学教科书,市制计量单位基本销声匿迹。
这篇编入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蟋蟀的住宅》没有注明选文出自哪个译本,我随后去书店翻看了十几种《昆虫记》,有几种封面上还有“新课标推荐阅读”或者“新课标必读”之类的字样,大多都没有标明译者,只有“主编”“编译”,大概是投机取巧从别人的译本里选编或者改编,仅有三种标明了译者名字,还是同一个译者。这些译本中只有一种没有选入《蟋蟀的住宅》,其它各种译本中都有相关内容,译文差别较大,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无一例外都用了“九寸”“两寸”这样的译文,甚至还有“0.75寸”“四分之三寸”这样别扭的翻译。
我还特意查看了各个译本的出版时间,全都标明是“第一版”,而最早的是商务印书馆“新课标必读名著”《昆虫记》,2012年7月第一版,第131页最后一行“大约有九寸深”,第132页倒数第5行“四分之三寸”。最晚的是浙江摄影出版社《昆虫记》,2018年9月第一版,第82页。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昆虫记》,2014年2月第一版,第146页;
江西美术出版社《昆虫记》,2016年8月第一版,第176页;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昆虫记》,2016年8月第一版,第138、139、143页;
北京教育出版社《昆虫记》,2017年4月第一版,第49、50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昆虫记》,2017年5月第一版,第93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昆虫记》2014年8月第一版,第121页;
中国文联出版社《昆虫记》,2014年7月第一版,第77页。
(最后三种译者为同一人。)
以上各本译文都用了“寸”这一中国特有的长度单位。
这真是咄咄怪事!
早期翻译篡改原文或许有情可原,但国家推广米制单位已经60年,国际统一计量单位在我国早已得到普遍使用,跟国际接轨正在成为我们的生活现实,这么多翻译作品还在篡改外国作品原文意思使用不符合当前国情的的长度单位表述,我严重怀疑,目前市面上的《昆虫记》译者根本就没有认真研读原著,且有抄袭早期译本的嫌疑,否则何以如此食古不化?
更不能原谅的是,这样篡改原文又有违国情,犯了常识性错误的译文竟然堂而皇之进了义务教育教科书!相关教科书的编审究竟是无知,还是太马虎?
这些年不断有人指出教科书的错漏,几乎每次都是“实锤”。因此,我建议,教科书编审必须更严谨,有必要引入公示制度,凡是拟定入选教科书的各种内容,都应该予以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努力避免教科书再出现常识性错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