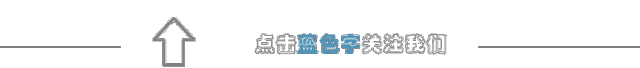
信天游不仅陕北人喜欢听,美国人也喜欢。信天游为什么好听呢?
一是各民族精华的积淀。历史上有三四十个草原民族在陕北繁衍生息,比如匈奴、鲜卑、突厥、白狄、党项等,这些民族都是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民族有个特点,就是能歌善舞,你看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蒙古族、新疆各族、藏族,以及西南苗族、壮族、彝族,都是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而中原汉族歌舞就不很发达,最有名的民歌是《茉莉花》,山东最有名的民歌是《沂蒙小调》和《弹起心爱的土琵琶》。陕北是汉民族的一枝独秀,有数不清的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个欢天喜地,分别对应三首民歌——《红方红》《哀乐》和《春节序曲》。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其实,陕北历史上是多民族聚居区,著名的杨家将、李自成都不是汉族,陕北人成为汉族是后来的事。
中原汉族为什么歌舞不发达呢?
这和农耕属性有关。农耕民族,讲得是秩序,要顺应四时,社会结构较游牧民族复杂而有规律,有朝庭,有百官,有等级,注重礼仪,循规蹈矩,端个架子,目不斜视。你看皇帝面前挂一串冕流,大臣帽子两侧有一对翅膀,就是为了端庄,防止你交头接耳、摇头晃脑。在这种格式化的生活中,只能产生程式化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戏剧。戏剧正好能弥补汉民族对艺术的渴望,那怕是位县委书记,在群众中间唱一出京剧,也是端庄的,不会有轻浮之虑。

冕流
北方草原民族则自由得多,他们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规矩,没那么多清规戒律,他们率性而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谈女人,活的洒脱,活得奔放,活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创造需要自由的空间,就像小鸟需要新鲜空气,戴着镣铐是不可能跳舞的,奴隶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而在陕北生活过的这三四十个民族,正是这样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民歌。这个民族迁徙远去,新来的民族会自觉吸收原来民族的精华,通过一代代的传承、吸收,沉淀下来的陕北民歌就是精华中的精华,不可能不好听。
特别说一下龟兹。龟兹人原来生活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能歌善舞,精通音乐。汉宣帝元康年起,龟兹人陆续内附,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米脂境内,也有人认为安置在榆林上盐湾或古城滩,也许这一带均有安置。龟兹人给陕北带来了唢呐,这也许可以解释今天绥德米脂一带唢呐好的原由。老一辈人称吹手为龟兹儿,音“guīzir”,是蔑称。
二是民族性格使然。民族的天性就像少年的天性一样,是不可能否定和抑制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性格,生活在陕北土地上的人们有自己的民族性格。陕北人就喜欢唱,喜欢闹,爱红火。东北有个词——“得瑟”,陕北也有个词——“特擞”,发音差不多,意思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来源的两个词。陕北人就爱“特擞”,听见锣鼓响,浑身就筛了,饭碗也撂不办,忙得趿拉上鞋,硷畔里往下逩。他们的口号是,“穷乐活,富忧愁,穷人不唱怕个毬”“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在许多文艺表演场合,关中道上的人互相推辞,说自己不行,唱不了,需要再三邀请,才客客气气地登台表演。陕北人还不等主持人说完,早跳上去三四个抢话筒,不管水平怎么样,拦羊嗓子回牛声,唱上不住气,也不怕丢人。唱过瘾,说“这下唱美了”,才像喝酒喝美了一样,满足地下台。“大大画个圐圙(音若“库连”),命交给老天”“死了的毬朝天,没死的又一天”。

三是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信天游直接承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方面王六先生有许多论著,我就不多赘述,我说说中学时学习赋、比、兴手法的一些感受吧。中学时,老师反复讲解什么是赋、比、兴手法,“比”好理解,就是比喻嘛,“赋”和“兴”,越讲我越糊涂,都快把老师讲哭了。其实这位走头拾路唱信天游的老师,用现成的信天游讲,秀才学阴阳——一拨就转。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这些红歌一睁眼就唱,恨不得吃饭也唱,这就是“比”。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 三十里铺村,四妹子爱上个三哥哥,你是我的心上人。”
这就是赋,铺陈直叙。

三十里铺村
“兰格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咱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那达想起我那达哭。”
“打碗碗花儿就地开,你把白脸脸掉过来。”“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着那好光景。”
这就是“兴”,前一句与后一句没半毛钱关系。
就这么简单,用信天游解释,憨汉也“害哈烂”。
有一首汉乐府《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上郡就在陕北榆林。我们看看歌词:
大冯君,小冯君,
兄弟继踵相因循,
聪明贤知惠吏民,
周公康叔犹二君。
你用《东方红》的调试着唱,好像有所感触。
还有一首,唐代诗人李益的《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
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
云中征戍三千里,今日征行何岁归?
无定河边数株柳,共送行人一杯酒。
胡儿起作本蕃歌,齐唱呜呜尽垂手。
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
回身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
蕃音虏曲一难分,似说边情向塞云。
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
不见天边青作冢,古来愁杀汉昭君。
夏州就在陕北榆林横山县西,诗歌描写的是陕北土著居民欢送戍边官兵返回中原的场景:军民正在进行告别联欢会,畅饮离别酒,陕北人唱着悠扬的信天游。队伍集合,整装出发,望着将士们远去的身影,陕北人站在高处,齐声唱起了高亢的信天游,让士兵们泪眼婆娑,不能自已。
这场景完全能拍成电影,胡儿唱的“蕃歌”,谁说不是信天游呢?
本文来源于乂南风过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