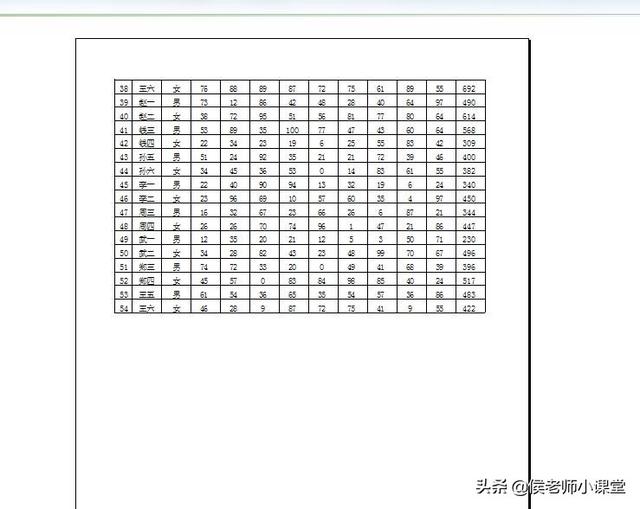打开这篇文章的你,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个场景。
你可能因为工作、学习或兴趣的需要阅读一篇文章,但当你开始前,手机屏幕上方飘过了一条未读信息:“新冠疫苗政策已在我市开放预约,名额……”这显然是一条乍看很逼真的诈骗信息,却诱使着你点开查看详细内容。紧接着,你因此希望了解最新的疫情动态,于是打开了几则推送的新闻。阅读时,你注意到其中一则新闻的下方浮动着一条广告视频:“冬天穿大衣必备丸子头。”想到刚刚入手的大衣,你随手打开了视频。
观看视频时,你发现这个发型自己并不喜欢,但App自动推荐的其他相关视频已经开始播放。你注意到其中一个视频的音乐非常好听,于是打开搜索软件找到完整的音乐。在下载音乐的同时,你又顺手点开了另一段视频……这一切都衔接的非常流畅,当你再度想起需要阅读这篇文章时,时间已经悄悄溜走了半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
在人人都离不开手机的当下,类似的场景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在移动互联网,保持“随时在线”的我们,所有体验可能是比较雷同的,一方面既可以轻松与朋友、家人和同事联系,并获取信息、游戏、音乐或视频,另一方面却可能失去耐心,在社交媒体上纷乱、撕裂的观点中变得浮躁、焦虑乃至“虚无”,而这些恰恰构成了社交媒体的流量基础。我们或许认为只要能用知识对此反思、批判,或重新融入现实生活,就可以逃离“随时在线”的。

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系教授。曾出版《速度帝国》(Empires of Speed)和《信息社会》(The Information Society)等。图为他和他的手机。
然而,这并没有那么容易。有一位传播学家罗伯特·哈桑就认为,他作为一位学者可能有能力反思甚至逃离这一切,实际上最终却没做到。他转而观察这一切,在他的《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一书中,从哲学和传播学的交叉领域对数字生活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随时在线”让人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在下降,无法进行长阅读,无法深入思考。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感叹“随时在线”让人无法静下来阅读思考时,可曾想到,书籍在印刷普及之初也被视为一种导致注意力下降的“毒药”。罗伯特·哈桑在接受书评君采访时,提到歌曲《保持沉默》的一句歌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刺激的时代。如果你很专注,你会很难接近。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可以被找到。”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通过专注让“大数据”“算法”找不到?
采写|何安安
“时间飞逝,令人沮丧。”
——歌德,1848年
一、没有人能幸免于“屏幕”

《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澳]罗伯特·哈桑 著,张宁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新京报:是什么促使你写下《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这本书?
罗伯特·哈桑: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我在数字生活中的处境,进行一种环境疗法(或者说这至少是一种自我分析和诊断)。作为一名研究数字媒体进程的教师和理论研究者,我一直认为,我可以免疫于那些自己向学生和读者所描述的网络成瘾、疏离感、商品化,企业、政府监控和操纵等弊病。作为一名学者,我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凌驾于这一切之上——因为我知晓它们都是如何运作的,比如,我知道硅谷的商业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但是,从2016年开始,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幸免,社交媒体的力量日趋强大和成熟,我也被纳入其中。前面我所列举的种种症状,实际上就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慢性注意力分散”。在针对注意力分散的研究中,我注意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脱离了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进入了数字模拟的世界之中,而这也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以自我反省的方式,使自己可以从那些已经成为严重困扰的东西之中解脱出来。
新京报:你提到当我们可能无法跟上互联网的速度,而且可能越来越跟不上其发展速度时,原有相对稳定的、由机械时间所奠定的社会与心理秩序就开始动摇了。在社会层面,数字媒介带来的持续加速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机器以持续增加的速度处理信息,将个体、社区、商业、政府和社会不由分说地裹挟进其迅速而难以预测的轨道,没人知道它将会驶向何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注意力分散?
罗伯特·哈桑:我们越来越多地理解那些和互联网有关的商业模式,它们针对我们的兴趣点进行了精心设计,使得我们易于接纳。不管是脸书、微博、谷歌还是百度,它们的商业模式都是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以及将这些数据出售给第三方(通常是广告商)。
不管是你还是我,让我们尽可能保持在线状态,对他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工程学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吸纳了从心理学、哲学到生物化学和神经科学的各种专业知识。在寻找利润的过程中,他们联合起来,对全人类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实验,没有人知道这将走向何方。

“人们认为,多巴胺会令人上瘾。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再次进入到沮丧之中。”(图为电视剧《黑镜》(第一季)剧照)
不过,这一过程中也得出了一些暂时性结论,比如所谓的“多巴胺循环”——它让我们陷入到不断检查手机、查找消息、阅读通知或者进行更新的状态之中。当我们接收到一条新的信息时,我们会在大脑中得到一点点多巴胺(数据公司知道这一点),而这会让我们得到微小的愉悦感。
人们认为,多巴胺会令人上瘾。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再次进入到沮丧之中。因此,我们会不断地检查手机,再次登录并保持在线以便寻找新的乐趣——当然,工作也会让我们保持这些状态,对于数据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奖励。总的来说,上网、追热门或工作(在一天的任何时刻都在增加)是一种零和游戏,这意味着,你的时间从你一天的其他部分中扣除,而你永远不可能将它再拿回来。
在线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意味着我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减少了——而这是在我们进入数字时代之前,一种更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个世界给了我们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而这些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建立在我们身体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物质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能够以触摸、感觉、嗅觉和味觉等无数种方式所感知。
当我们的眼睛盯着一个玻璃屏幕时,这一切都被封闭起来,我们与原本充实的生活脱节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设计师、社会主义活动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认为,“艺术是人们对于生活兴趣的具象化表达,它源于人们对生活的愉悦”。从这个角度而言,照片墙(Instagram)和脸书无法成为或者替代任何一种具象化的表达方式。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年3月24日—1896年10月3日),出生于英国沃尔瑟姆斯托,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
二、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会被大数据找到
新京报:学者哈特穆特·罗萨所说的“加速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现在的机器,尤其是计算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奔跑的更快。正如你所说,“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更加自由的机器,却在时间上奴役着我们。”同时,赫伯特·西蒙指出,丰富的信息可能会导致注意力不足。那么,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加速的社会”,又该如何面对因此导致的“慢性注意力分散”?
罗伯特·哈桑:西蒙说,从本质上讲,信息丰富是对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的挑战。我们可以选择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集中注意力的环境之中,让自己被互联网及其应用程序的设计方式所驱动;或者我们也可以拒绝这样做。

“抉择意味着在网络的控制下保护自己。”(图为2016年电影《玩命直播》剧照)
我们需要认识并理解在这个巨大的实验之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并对此说:不。然后,我们需要尝试控制我们的数字生活。这可以从抉择我们在网上看到、听到、消费的东西开始,在自己访问的网站,使用的应用程序,参与的网络社群中找到那些真正重要的内容。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个或者那个吗?它对我有什么用?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吗?它对我来说“好”吗?这是在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吗?如果你花费太多时间刷照片墙或微博,我们就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抉择意味着在网络的控制下保护自己,进行反击并夺回控制权。这并不容易,因为网瘾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我们也离不开数字生活。但不管怎么说,除非我们想任由数据公司摆布,像他们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样行事,我们都应该去尝试摆脱这种控制。
新京报:但更多的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危机。正如你所说,这些危机隐藏在阅读、写作和认知中。
罗伯特·哈桑:有数以十亿计的人们从未经历过数字时代之前的生活: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西方有着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则更久,由印刷文化主导着教育、政治、媒体等领域。但这些人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对他们来说,线上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网络的商业模式:娱乐、社交网络、教育和工作。

电影《社交网络》(2010)剧照。影片讲述了天才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创建日后名声大噪的“脸书”(Facebook)的故事。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网上获得的。但对于数据公司而言,这些设计都是为了收集他们所需要的数据而建立的。数据公司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出售给第三方。所以,线上生活是商业化的,以消费化和货币化为导向。
十多年前,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告诉我们,这样的数字生活让我们变得愚蠢。它让我们专注于生活中琐碎的、当下的、非本质的和非反思的方面。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并不是坏事,但它们正在日益主宰我们的行为、生活和思考方式。
卡尔的观点有一个相当有趣的推论。在硅谷,有一所学校,所有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计算机行业的人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当然,这是一所私人学校,费用昂贵,但这所学校不使用电脑,也不鼓励孩子在家里使用电脑。他们用艺术、工艺品、表演、阅读、辩论和个人表达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这些孩子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知识体系和基本价值观。
硅谷的精英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些地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销售给我们的产品的态度。这涉及到知识,以及获取知识的途径。我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但数据公司、世界各地的商业和政治精英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而获得知识意味着拥有主权。能够分辨出真相和谎言、信息和谣言、数据和垃圾、科学和科幻小说,对于操纵、推动和控制他人并保持领先地位而言至关重要。我们花在照片墙或TikTok上的时间越多,或者漫无目的无休止地浏览,我们就越容易受到攻击。
新京报:既然数字生活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更“肤浅”。那么,是否意味着“持续在线”的状态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罗伯特·哈桑:英国“野蛮人”乐队(the savage)的歌曲《保持沉默》(Silence Yourself)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刺激的时代。如果你很专注,你会很难接近。如果你心不在焉,你就可以被找到。”注意力难以集中使得我们很容易被数据公司操控,让我们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提供利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愚蠢,但这显然是一种轻信。我们轻易地把自己的信任放在了并不了解的数字网络进程之中——甚至数据公司自己也不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超出了他们的短期目标。

在移动互联网兴起前,手机通过短信已经产生人际影响。(图为2010年电视剧《手机》剧照)
三、“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你就是产品”
新京报:信息传播技术加速了时间,也加速了社会运行,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成为了连接世界的纽带,也推动了全球化的发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全球化媒介产业的语境之下,媒介总是迅速地转移焦点,去追逐下一个头条故事,新闻的保质期越来越短——即便是重大政治事件也不例外。你对媒介、时间、政治和技术领域都有研究,它们交织在一起,对我们的生活到底带来了什么?
罗伯特·哈桑:这些领域的融合可能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动力,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数字技术将政治与全球化捆绑在一起,并导致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马克思创作这本书的年代,这一进程的发生几乎可以用悠闲来形容,因此,他将此看作是一件好事,认为这将推动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也将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
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进行着,它并不会赋予任何阶级以权力,这是一个剥夺和解除社会纽带及阶级认同的过程。仅占全球社会阶层中极小一部分的亿万富翁和世界级企业正在塑造和引导着当下绝大部分的政治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恰恰是因为绝大部分人被排除在有效决策体系之外。
我所作的工作,不仅仅着眼于如何理解当下,还着眼于如何引导个人和集体进行反击。我们需要做出有益于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政治选择,使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受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大数据公司,需要研究他们为何没能提供有用的社会服务,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对人们更为负责的部分。
新京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为,看似免费的互联网世界实际上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时间代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无薪雇员。全新的“网络时间”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掌控,我们怎么才能有更多的选择呢?
罗伯特·哈桑:这个观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确实如此:“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你就是产品。”
如果我们沿着免费应用程序的道路前进,这将会缩小我们拥有的选择和可能性。商业互联网(或者说表层网络)只是我们每个人所能访问的信息,以及进行通讯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仅仅去简单追随TikTok、脸书、微博等数据公司的商业趋势,我们的个人和社会视野就会越来越小。
我正在创作两本书。其中一本有关于模拟技术的性质和功能。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模拟技术是成为智人的核心。二十五万年前,我们用工具进化,不仅如此,我们还进化成为了技术模拟生物。

“我们创造并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地技术……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图为2012年电影《断线》剧照)
而在很多方面都与模拟技术相反的数字技术正在迅猛地向我们袭来,并在技术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创造并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地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仅次于模拟技术的第二种技术。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能完全理解这对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文化、社会和文明的意义,以及对与物种起源密切相关的模拟技术意味着什么。
四、冲突、撕裂,是社交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新京报:从写作开始,科技的发展让我们读写越来越快,书写和阅读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紧张的、充满焦虑的阶段。在加速发展的世界里,这种媒介节奏对我们的认知和思维能力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罗伯特·哈桑:首先你必须要明白,写作和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作为我们思考和表达自己的一部分,作为我们思考过程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原本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必须去学习的东西。
识字社会的文化(即写作社会),是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它的希望、梦想、意识形态、宗教、技术和科学成就,都是通过报纸、书籍、杂志、期刊、地图、漫画等形式而得以实现的。这种文化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时钟上的时间,以及印刷媒体生产、发行和消费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问题是,它是随着识字率的提高,以及被称为“阅读大脑”或印刷文字大脑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核磁共振(MRI)扫描显示,“阅读大脑”是通过阅读纸上印刷的文字以某种方式构成的。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这些扫描结果可以与那些主要在屏幕上阅读文本的人进行比较,后者显示出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结构。
这要如何理解呢?“阅读大脑”是由纸上的印刷品雕刻而成的,它的特点是突触的形成更加牢固,突触是让神经元相互传递化学信号的连接点。这些突触连接构成了深度记忆和长期专注的能力。换句话来说,阅读纸上的文字可以提高记忆力和注意力。相比之下,数字屏幕上界面的作用恰恰相反。主要从屏幕上阅读实际上削弱了突触连接,使大脑在记忆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方面发展不足。因此,“数字大脑”比“阅读大脑”更加肤浅,对任何具有深度或长度很长的主题把握能力也较低。这些方面都是坏消息。
幸运的是,实验表明,因为屏幕阅读而削弱的突触连接可以被逆转。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基于屏幕进行文本阅读的阅读者将屏幕切换为印刷品,那么突触连接,以及他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可以得到快速提升。不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数据公司迫使我们不断进入数字世界,我们变成了只拥有短期记忆的“掠夺者”。如果你就想要生活在一种“持续存在”的在线状态中,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要进行反思、进行历史性的思考,并拥有透过表面进行学习和理解的能力,这就有点不太好了。

“我们阅读到的东西更多了,但是能够被记住的却更少了。”(图为2012年电影《断线》剧照)
新京报:在数字时代,阅读、写作和交流之间的新关系是什么?
罗伯特·哈桑:阅读和写作已经数字化。我们阅读到的东西更多了,但是能够被记住的却更少了。这是因为信息量过大,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我们所依赖的记忆是工作记忆(是一种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消耗和使用的东西,但这种记忆事后很难进行回忆。因为我们的大脑中的突触连接——那些通过近距离和深度阅读而增强的突触连接,在我们通过屏幕进行阅读后就会开始萎缩。
写作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具有短信特征的表达,以推特或新浪微博等短格式应用为例,这些应用程序保持了我们的工作记忆并且缺乏反思能力,而其导致的结果是交流的退化。正如我们在脸书和推特上看到的那样,这种交流会退化为消极、虚荣的言论,或者谩骂、党派之争、诽谤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导致冲突的交流情感——因为冲突正是社交媒体赖以生存的根本。
采写|何安安
编辑|石延平
校对|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