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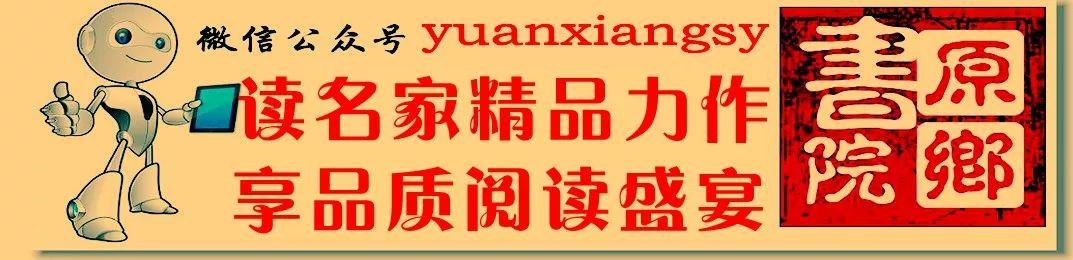

牡丹
张巧慧
1
知己有恩。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为故友张先作《张子野墓志铭》,谈及“平生之旧,朋友之恩”。近千年后,寓居京城的齐白石刻下一枚印章“知己有恩”,并在边款记下“欧阳永叔谓张子野有朋友之恩,余有知己二三人,其恩高厚,刻石记之”。齐白石印风粗犷,取法汉代急就的将军印。齐白石早年在京师卖画,价格低于一般人还少有人问津。后来陈师曾劝他自出新意,大胆革新技法,又亲自带着齐白石的作品到日本举行画展,助力白石显名中外,展览作品全部售空。陈师曾称得上是齐白石的知己。
无独有偶,翻阅西泠八家的印谱,翻到丁敬的一枚白文印“只寄得相思一点”,读到边款发觉并非寄给女子,而是给好友金农:“老友冬心先生。好古拔赏。与余有水乳契也。客维扬不见者三年矣。书来。作此印答之。戊寅三月,丁敬并记于无所住庵。时年六十有四。”陈豫钟(号秋堂)曾治一枚印章“此情不已”,流落民间。边款是庚申五月作于汤氏之宝铭堂,秋堂。算来应该是在一八六O年夏季。令我感怀的是同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号曼生)的补款。大致意思是因陈曼生常向孙古云称道陈豫钟的印章好,孙古云某次在地摊上看见此印是陈豫钟所刻,花重金买来,特别珍惜。只可惜那时秋堂已经辞世数月了,秋堂去世后还能交到古云这样的印友,可以无憾了。二陈之间的情谊确实如印文所言“此情不已”。

高山流水,生死不渝,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杭州下天竺法镜寺旁,莲花峰东麓,有三生石。早年我抄经习书时曾去参访。三生石在山腰,从下天竺后门出,拾一段清幽小道,偶有大树斜出枝条半拦着山路。并不远,几百丈路,转过一角亭子,祈福的红绸与木牌便映入眼帘。大树蓊郁,几株古树间,三块巨石,石高三丈许,中间那块,向内的石面上额刻有篆书:三生石。不知是谁所镌。边上有刻民国时期《唐·圆泽和尚·三生石迹》的碑文。据说石上曾有唐末五代高僧贯休的楹联题刻,然我并未看到,许是唐宋时远,题词石刻大多已模糊不可辨认。倒是查到在清初《西湖佳话》和张岱的《西湖梦寻》中都有涉此石之记载。
三生石的故事,其实是两个男人的三生践约。有说典出唐代袁郊的《圆观》,又说苏轼的《僧圆泽传》也记录了这段传说,我所阅信息中多数道是圆泽禅师。讲的是他与居士李源的故事,两人性情相投情谊深厚,互为知己好友。禅师明知陪李源走水路赴峨嵋,会遇到生死劫,依旧顺了李源的心意。所谓行止固不由人。
果然在荆州遇到宿命,水路相逢一个怀孕三年迟迟未生的女子,就是禅师下一世的母亲,禅师只能坐化投胎,这一世的缘分终了。灭度前禅师说十三年后,在杭州下天竺寺门外相见。生死离别,李源悲悔不及,怪自己坚持走水路害得好友丧命,从此天人相隔。
十三年后的中秋夜,李源自洛适吴,赴其约。至约所,听闻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果然是禅师转世。一个真信士,守时守信去赴约;一个隔世践约,穿越前世来到今生见前世的友人。
我喜欢这个故事的中性叙述,不流俗于男女情事,更是人与人的信义。人间情谊有很多种。两肋插刀是一种,知己有恩是一种,此情不已也是一种。

2
己未年过姑苏,夜来独往万卷堂听曲。万卷堂旧为宋代藏书家史正志的藏书楼,清后改网师园。网师园几易其主,多为文人雅士,遗有诗文碑刻,亭台轩榭花木扶疏,是古典山水宅院的代表。姑苏人有心,组聘了一支演出团,沿着参观路线依据宅院布局移步换景地安排琴瑟歌舞。入夜,月色盈盈,倚在美人靠,隔着脉脉水波,听箫声若隐若现。
步行至濯缨水阁,避不开一段《惊梦》。现代全息手段,灯光朦胧,实景园林的古韵,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长长的拖音,缠绵秾丽。斯人唱的《牡丹亭》,原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惊梦片段,相遇,相爱,太美。然而又哪里会有完美?杭州女伶演到寻梦一折,忿惋而死,命断祭戏。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还魂一章。杜丽娘梦见柳梦梅,相思成疾,伤情而死,又因柳梦梅深情而起死回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重点在死亦可生。殉情之事古已有之,然而死可复生不见实证。《牡丹亭》全名是《牡丹亭还魂记》,又称《还魂梦》。所爱还魂,谁人不想?又焉能做到?汤显祖做到了,他说: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对爱情的期冀,也是我们的。

闲步庭院,见一对年轻演员在天井说笑,女子正在试身段,男子打扇,不觉竟痴了痴。此时此景,多像旧时的少年夫妻两情相悦举案齐眉,多么好,多么美。一切就像刚开始那样。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那个时候,一位年轻的美籍华裔翻译家,正在翻译我的诗歌。她给一个加拿大诗歌出版社投稿,他们有意向出版她的诗歌翻译小册,里面包含最近两年翻译的代表作品。(这种小册的英文名叫chapbook,在北美和欧洲文学圈流行,为四十页或以下的手工制作限量版小诗集,除了阅读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小册中会有她翻译的五位诗人的作品,分别为废名,秋瑾,戴望舒,小西和我。其中每人会选入三首诗歌,包括我的《举着鞭子的手停不下来》《独白》和《天一阁》,前面两首是重印,最后的那一首是首发。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女性与少数性别文学杂志Room希望能够发表几首我的小诗。另外有个美国的亚裔文学出版社(叫Singapore Unbound)也有兴趣在他们的网上发表我那首《举着鞭子的手停不下来》的英文译文。问我有没有其他类似题材和风格的诗歌,希望考虑一起发表。她们说很喜欢这首诗,讲家庭而又很诗意,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残酷。而美国的一个网络杂志也希望能发表我的诗歌《独白》,并能和她交流一下创作的感受。这个网络杂志喜欢发表描述各个国家地区的诗歌,所以译者写了短的介绍,强调了我所生活的宁波背景。我陆续签署了翻译权授权书。

《独白》这首诗歌终于从我的诸多诗歌中被发现了。译者有敏锐的诗感,问我诗中的“教场山”有否独特意义?“喧嚣的集体自尽”和“独白”是否存在对比,是否有类似于埋没、逐大流,放弃个性与独立思考的意思?
那首诗已经写了八年了,写的是生命意识,岁月给每一个人带来的苍茫。那时我还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少妇,四十岁的女人和二十岁的女人,她们所经历的与心态皆不同。那个时候,我正在读《过于喧嚣的孤独》。因为外祖母百岁冥寿,民间风俗过了百岁就转世投胎去,后辈可以不再祭祀。忽然觉得自己来处更空了一点。外祖母对我有煦伏之恩,恩逾慈母,是我最爱之人,二十多年前她离世之际,我曾觉得这世上再无亲人。

生命的意义与归宿在哪里?你知晓祖母葬在哪里,但却不知道祖母的祖母在何处。对大处的茫然。但具体的生活仍在继续,爱恋,欲望,桃花,姑娘,青草从石板缝中生长出来。石板之硬与青草之柔软,永无止境。究竟什么是恒久?究竟谁是主宰?所以就写了《独白》。
教场山是城中的一座小山丘。早的时候叫晒网山,因为这片地方从前面临大海。明时山上有烽台,俗称烟墩,为抗倭之用。山的东南面开辟教场基地,作为操练兵马之所,也是斩首示众的地方,故后人称为教场山,并一直沿叫至今。教场山上从前是墓园,历代人们的安葬之地。我读书的时候,有时会一个人去墓园里静坐,想到历史、战乱与繁华、死亡。时间的神秘性。
现在教场山上的墓已经迁走,四周越来越热闹,已改成公园。沧海桑田。这样一个意象进入诗歌,虽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是偶然的但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后来者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就站在古人的墓址之上,就像生建立在层层的逝去之上,就像青草长出来。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翻《中国历代篆刻集粹》,翻到赵之谦。其所篆印文“俯仰不能弭,寻念非但一”“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两面印)。四面长跋,白文楷体《亡妇范敬玉事略》,间有界格,工整规肃。赵之谦所撰,门人钱次行刻之,也就是钱松的儿子钱式索篆代刀。
据年谱记载,赵之谦十六岁母亲殁,兄为仇诬,以讼破产。十九岁娶妻,妻子范敬玉读遍五经,喜为诗,书宗率更(欧阳询)。同治元年,战火烧至绍兴。范敬玉避难至母家,幼女夭折。不久范敬玉病殁,年仅三十五岁。家中所藏文物俱被战火吞噬。因战事阻隔,数月后赵之谦才得知妻女去世的消息。家人死徙,屋室遭焚,赵之谦悲痛欲绝,刻了“我欲不伤悲不得已”“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等印,从此改号“悲庵”并刻印,边款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
同年夏,赵之谦感怀七世祖赵万全千里寻父金蝶扑怀的故事,再刻“二金蝶堂”斋号印,汉铜印风格。边款中流露出对先祖孝行懿德的追念和对自身遭乱离、丧家室的遭遇的悲怆,当年先祖遗骨尚有后代走寻而负归,如今自己剩一身、险以出,潦倒天涯,惟有泪下。
刻此石,吿万世。
我更相信,他的内心,盼着妻女亦能化为金蝶扑怀归来。

3
连着几年去看牡丹。城南,山下。一个四合院的南边。周围有矮墙与世相隔,散落的豆萁,青菜畦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一丛丛的,高高低低,分外野趣。有雅士芳兄从洛阳移植牡丹八百株,只一色,白,单瓣,浓而不艳,艳而不俗。
我喜欢牡丹是自遂昌看《牡丹亭》之后,文化与美色的相融,那种美,竟有了脱俗的意味。我还为汤公园的牡丹作了一首诗发在《诗刊》里。有老友乔迁画室,自号宽庐,我曾赠牡丹一盆,老友作画以答,在一张民国旧纸上画两浓一淡牡丹三枝,落款题:吾自幼习画常随性而发不入时赏不画牡丹也。时以丙申三月吾居宽庐作新画室,极目远望,阡陌纵横,背倚峙山而翠色欲滴。时小友来访赠余牡丹一株以添雅色遂作此。读来犹觉满室生香。
匆匆韶华,春之将尽。
访名苑名花,八百株洛阳白牡丹,藏于青山与闹市之隙,花叶蹁跹,单瓣,清气,我著一身白衣,流连于千百朵牡丹之间,仿佛自己也风姿绰约。
莫名却想起捷克作家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说:“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写这本书。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它推迟了我的死亡。”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一个废纸打包工的独白,地下室、书籍,珍视与销毁。耶稣和老子的对话,暗喻,意识流,哲学与终极思考。这生的喧嚣,这孤独。
在书中,他最后一次回到地下室,将自己和书一起放入机器中,按下按钮,开动压力机,在最爱之处结束生命。那一刻,他看到了年轻时爱过的姑娘。一九九六年底,赫拉巴尔因病住院,在即将出院时,他从病房窗口坠落身亡。

生命难以承受之重。最残忍不过是对美的毁损,因为我们爱得深切。
去年春,传统花朝节,再赴芳兄小园赏牡丹。芳兄家父沈老先生,善工笔,十余年前在我所在艺术馆举办过展览。那时就可见芳兄孝心。彼时其母尚健,芳兄感慨母亲一生默默扶持父亲,成全了父亲写字作画的雅兴,在展览中特意要致辞向母亲表示谢意。逝水流年,其母病逝之后,留下老父亲。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这数年来,素来喜欢游山玩水的人足不离乡,陪老人颐养天年。厅堂间所见皆是老先生的工笔花鸟,有线描稿,有墨稿,有重彩,松枝茂然,鸟羽纤毫毕现。
芳兄尊父,已是入杖朝之岁,又小动手术,芳兄忧愁之心言语难表。不想术后两日能自然行步,如此高龄目力尚能作画,也是奇事,想起赵之谦的二金蝶堂,或许真是父慈子孝之感应吧。问及前园牡丹,可有开否?不意芳兄答:他早已无意身外之物,只求与父亲相伴终日,能搏父亲宽心一笑为乐。全然已抛却牡丹。遂唤来嫂子陪我共探牡丹园,但见满栏花开,独立东风。
便无限想起我的外祖母。我曾尝过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又尝过知己先往之痛。谁能阻挡时序的更替。美,终究是要败的,要碎的。
外祖母落葬之后,不知缘何墓前的野松柏枯了一株。十年之后,外祖父归葬,趁着动土之际,重修坟茔。我又另购了一株松柏上山,劳表哥手植。有一年好友陪我去扫墓,我老远指着那两棵树说,外祖母的墓最好认了,远远就能见到一株高一株矮的松柏。未料隔年,好友也辞世了。人生聚散信如浮云。

十年生死两茫茫。外祖母去世二十年,我仅梦到一次;故友亦是。此生不会再相逢。为外祖母写过诗,也写过散文《外祖母的床》,收录于《散文选刊创刊30年散文精选集》。然而我既不曾等来《圆僧泽传》的三生践约,也不敢妄想《牡丹亭》的死而复生。人世间多的是黄土埋幽,与生俱尽。那些传说实则是因为不可能而美之。
看着满屋子老先生的笔墨,看着友人与老父亲寸草春晖,扇枕温席,分外羡慕。朋友说,牡丹是富贵花,寻常人家是舍不得剪的,更不肯赠与外人。我心既已视富贵如烟云,你若喜欢牡丹,我也舍得。一下剪了五枝,取五福临门之意。
有许多美是建立在冷峻的死亡之上。所谓向死而生。比如牡丹插在汉富贵砖改磨的花器中,组成花开富贵。却少有人知晓,这些吉语砖大多是墓砖。
“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想起那年去看牡丹……白牡丹,干净得像个谎言,她开得那么白,让朗诵祭文的语调慢下来,让灵魂暗下来。
我们都有过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那年牡丹花开的时候,我正在抄《春江花月夜》。
那时我们最爱的人都还活着。

张巧慧,宁波慈溪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作家》《十月》《青年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几十种文学杂志。著有《朔风无辜》《缺席》《与大江书》《走失的蝉衣》等,曾获2015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