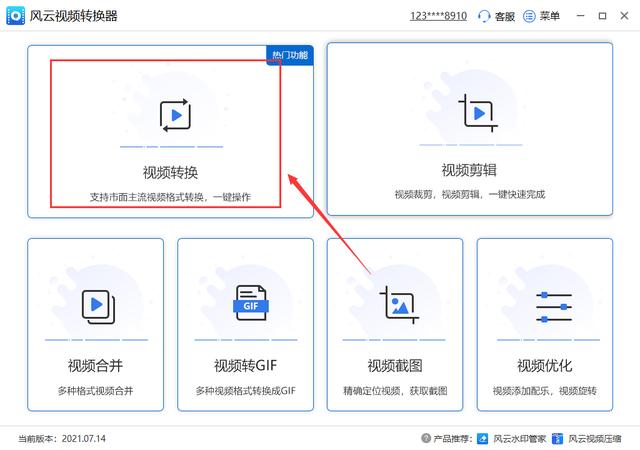1
我第一次见到小D是在西安的一家网吧里。他坐在我的几个朋友之间,眼神专注。也许是因为在电脑前消耗太久,他的脸好像盖上了一层油光。从他们专注的表情看,游戏应该正是关键时刻。紧接着有人喝彩——小D在游戏里击杀了对方的英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他们开始大笑。小D也一样,只不过有些腼腆,尽管看起来这场战役的胜利是由他促成的。
我走到小D身后,看到一张陌生的War3自定义地图。小D操纵着一个白色的胖子走来走去,它肚子破开,肠子与内脏的混合物拖在地上。他把鼠标伸向敌方英雄,钩子从胖子手中射出,回来的时候上面多了一具尸体。我的朋友们再度发出欢呼。我激动不已,跟着他们喊了起来。
“嘿。”我敲着着小D的椅子,“不管你们在玩什么,总之,带我一个。”
2
嘉禾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游戏高手。在知道电子竞技的人寥寥无几时,他就已经立志成为职业选手了。作为同班同学,我们两个被打上了相同的烙印:差生、逃课,不务正业。但作为游戏玩家,我们的游戏趣味却大相径庭。
2004年,玩《魔兽争霸3》和衍生地图的男孩、沉迷在《劲舞团》里的女孩,构成了网吧玩家的主要群体。我在网吧里玩着鲜有人知的《大航海时代OL》——我得携带U盘,先将游戏拷贝到硬盘里,通常这个过程要花15分钟。而15分钟,足够嘉禾在浩方平台上结束一场《魔兽争霸3》的对抗——时间甚至绰绰有余。鲜有对手能在他的攻势中坚持10分钟,如果比赛超过20分钟,会令他异常兴奋,那说明遇到高手了,尽管通常仍旧以他取胜告终。

那时候还没有完善的天梯制度,对手水平的高低全凭运气,网络竞技制度并不完善的某些时期,线下约战比线上更为靠谱。
BBKinG在《中国电子竞技幕后史》里这样描述那段时间:
西安当时网吧已经开疯了,今天开个200台的,明天开个300台的,后天有开800台,上下3层楼都是电脑,全是最新配置最好的电脑,网吧老板为了吸引生意,对电子竞技的拉拢无所不用其极,每个网吧都养着一支半职业战队,进去会看到一面墙,上面贴着该网吧战队主力队员的大幅照片和介绍。
嘉禾的梦想就是成为照片墙上的一员。当我俩在教室外罚站时,他会变得深沉起来。他背靠墙,用脚后跟有节奏地敲击墙壁,然后问我一些比较早熟的问题。有时他会问我有没有梦想,并配以看向远方的深邃目光,我忍不住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里除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以及水泥跑道上扬起的灰尘,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幻象眼前的场景变成了大海斜阳。
事实上,我从未坐上去往任何港口的船只,嘉禾也并没能成为一名职业电竞选手。第二年,伴随SKY从新加坡传来华人首次夺得WCG世界总冠军的消息、电子竞技在中国即将掀起惊涛骇浪之时,嘉禾却突然从学校退学了。“2万美金,2万美金啊!”这是那一年嘉禾在我的QQ上最后的留言,他指的是SKY在夺冠后获取的冠军奖金——也是当年全世界电子竞技最高额度的奖金。
■ 3
“打DOTA吗?”
这是我和小D的聊天记录,可以被概括为他持续半个月的自言自语:“什么时候上线”,“来开黑”,“打不打”。小D习惯了我的拒绝:不回复就等于不上线,但他仍旧对此孜孜不倦,他后来称之为碰碰运气。这些留言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他任何时候都在打游戏。
我输入:“你干嘛呢?”
大概10分钟后,小D回复了我的留言:“上线。”看得出他激战正酣。
在某个对战平台的天梯界面上,对天梯积分有如下描述:
2000-2199:高端玩家,地区性冠军选手
2200-2399:路人王,国家性冠军选手
我和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人永远也达不到2000分,而小D的积分始终徘徊在2200左右,换句话说,他游离在官方定义的职业选手之外,但却远超常人。在等待小D游戏结束的间隙,我浏览他的游戏记录,小D进行过1200多场比赛,其中800多场使用的英雄都是那个“白色的、可以射出钩子的胖子”。
我曾问过小D有没有想过去打职业,他对我说:“那不可能。”小D的家庭条件很差,他爸爸在西安附近的某个县城里开了个小型饲料厂,每天的工作就是送货、看门,“小D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饲料厂里面喂狗。”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并且不忘配上夸张的笑容。
还是听他们说的,小D平时的零花钱很少,唯一的来源是父母每日发的买菜钱,那是为了给待在家里的爷爷奶奶做饭用的。他们告诉我:“如果小D去网吧缺钱了,就跟他妈妈说,爷爷奶奶想吃鲍鱼。”说完,他们大笑。
高考失利之后,小D想要复读,但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父亲认为,家里不富裕,小D也不聪明,复读一年成绩应该也没什么区别,还不如“早早工作,早早赚钱。”——这话我听起来极为耳熟,作为我校教职工心目里的眼中钉,我的班主任对我说过一样的话。不过她会在结尾补充:“毕业证有什么用,你拿来擦屁股还嫌硬呢。”为了让自己显得幽默,她会同时把手放在臀部的位置,做出一些看起来十分可疑,但她认为很滑稽的动作。
我们偶尔在网吧玩到半夜,直到饥肠辘辘,必须回家不可了,小D仍然会不舍地坐在座位上,用近乎祈求的口吻对我们说:“再打一把吧?”通常他的要求会遭到我们的无情嘲弄,于是他只得勉强起身,和我们一起在深夜里寻找一个食摊。这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聊聊——我是指游戏以外的事情。
小D想作一个画家,他如实说,最好能到一间游戏公司里做个原画师。“你有学过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摇了摇头,接着拿出手机,给我看他拍下来的照片。我对着那个不足3英寸大小的屏幕,努力辨认着用100万像素摄像头拍摄的照片,言不由衷地称赞了起来。
那是一些难以归类的铅笔涂鸦,大多数以游戏人物为题材,有与巨龙争斗的勇士,也有满脑肥肠的商人,长相离奇的怪物与御剑飞行的少年激斗正酣。小D真诚地希望我评价他的美术水平,作为一个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造诣的人,我给出了自认为最安全的答案:我建议他报一个美术班学习一下。他神色不安,把双手垂放在腿上,很快地搓弄起手指。“不行,我家人不同意。”
我想起小D父亲甚至不允许他复读的言论,欲言又止。
■ 4
07年对我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父亲为我买了一台电脑。就像宣称购买随身听是需要学习英语一样,购买电脑也是为了学习。至于我用这台甚至无法上网的电脑能学到什么,我的父亲不以为意,我认为他的真实意图是,至少知道我以后在哪玩游戏了。
我买的第一款游戏叫做《仙剑奇侠传4》,当我将它带回家时,我母亲立刻认为我早恋了,原因是游戏包装上印着两对古装俊男美女。她不知道的是,这款游戏的确讲述了一段在“架空历史的古代中国”所发生的男女爱情故事。
那一年暑假,当我沉迷在这款游戏的迷宫里无法自拔时,嘉禾背着书包,披头散发地敲响了我家大门。我上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06年WCG西安赛区的魔兽争霸赛场,嘉禾获得了第四名——那意味着他与全国总决赛失之交臂。
“我爸妈要送我去戒网瘾”,他点起一支烟,躺在我的床上说,我默默地拉开窗户。
多年以后,我仍旧对嘉禾父母的先知先觉感到吃惊,毕竟被无数父母视为救星的“战网魔”在那一年还没有开播。
为了躲避被送去山东接受治疗的命运,嘉禾躲进网吧。整整一周时间,除了上厕所,他几乎把自己固定在了座位上。嘉禾的父母花了一周,翻遍了西安市区里的每一家网吧,据目击者声称,嘉禾的父母找到他的时候,他的父亲面色铁青,母亲则抱着他,失声痛哭。
这件事情的结局和大部分人想的不太一样,嘉禾没有被锁到家里惨遭殴打,也没有被秘密送到位于临沂的某处网戒所。他的父母无法接受二次失踪的可能性,于是做了妥协:决定让他出去工作。几天以后,我又在那间网吧里见到了嘉禾——他成为了一名网管。“这下上网不用花钱了”,为了掩盖悲伤,我只好假装幽默地说。
■ 5
我见到小D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半个小时,赛场里只剩下最后一排还有零星几个座位。2014年8月,Dota2中国区预选赛,我在华西村的赛场外见到了小D。他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白色T恤,胸前印着Dota2的官方Logo,背后则用古怪的字体写着“神秘商店”。由于火车晚点,小D没能赶上直达赛场的班车。迟到也没能削减他的热情,因为坐在隔音室里比赛的,有一个是他的偶像。
我跟小D的交流很少,当然,我指的是游戏以外。有时候他在我们常去的网吧见到我,会像陌生人一样站在身后,企图让我自己慢慢发现他,如果过了很久我还没有察觉他的存在,他就会掏出一支烟,突然放在我的键盘上——这种独属于小D的、独特的打招呼方式,令我从认识他起就印象深刻。
小D说,他的爸妈带着爷爷奶奶回老家了,留下他一个人看厂,所以他得以花2天时间进行这次秘密行动。“那谁来喂狗呢?”我耳边回荡起朋友的笑声,突然略带不怀好意地问。“我女朋友。”他羞涩地说。
我对“女朋友”的事情一无所知,但小D紧紧盯着大屏幕,容不得我开口再问。一场团战正在激烈进行,片刻后,Ultra kill的标语响彻全场,与此同时,小D和我周围的观众一起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
两场比赛的间隙,选手走出比赛专用的隔音室,站在舞台边缘,与前来观战的粉丝们进行互动。我怂恿小D前去合影,他的身体显得跃跃欲试,表情却有些退缩。我站起身,拽着他穿过拥挤的人群。人潮涌动之际,我抓紧机会为他完成了一张合影。
1个月后,他搂着的那名比他还小几岁的选手,在西雅图一举斩获ti4总冠军,并率领他们的队伍豪夺500万美元奖金。
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发给嘉禾,并附上留言:“你的两万美金呢?”
■ 6
“666666……”,弹幕布满了我眼前的屏幕,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30秒前,我面前的这个直播间在线人数只有20余人,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4位数,并且仍在疯狂增长。这一切只是因为我面前的这个人给主播送了一枚火箭——一枚价值人民币500元的火箭。
我正在嘉禾位于成都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放着一只造型独特的狐狸:带着面具,表情妖娆。他说这是吉祥物,也是他们正在运营的手游logo。嘉禾已在这所工作室工作3年,他现在的身份是制作人。
然而这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
嘉禾在当网管期间,以我无法想象的毅力自学编程。他的第一个作品是利用网吧服务器架设了一个局域网私服。坊间传闻,该私服深受网吧常客欢迎,并最终闻名几条街区,帮助该网吧坐上了客流量第一的宝座。
网吧老板刚开始并不拒绝,直到嘉禾开始从中牟利。有客人想花钱让嘉禾在游戏里给他发放一套顶级装备——他也照做了。这件事导致的结果,和嘉禾想象中相去甚远。并没有更多购买装备的顾客出现,与之相反,事情败露后,嘉禾与其他顾客发生口角,继而产生了肢体冲突,于是他被开除了。
嘉禾认为自己从中看到了发财致富的机会。1个月后,他跟某个来路不明的香港人合伙,开始了专职开设游戏私服的营生。他的合伙人提供资金、服务器和场地,而且还能带来源源不断的玩家——嘉禾需要的只是提供技术,以及调试游戏体验。这里面唯一的难题在于,那个香港人提供的场地在深圳。
不满20岁的嘉禾向父母表达了希望去深圳工作的愿望,然后被断然拒绝。嘉禾的父母无法接受他跟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去做听起来疑似非法的勾当。但嘉禾不管,带着当网管时攒下的2000块钱,他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坐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嘉禾的父母一觉醒来,在他的枕头上发现一张留言:我走了,再见。
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嘉禾只见过所谓的香港人一面,香港人每个月固定给他打一笔钱,以维持他的生计跟日常开销,他们约定,每半年分成一次。“有一段时间,你在百度上搜索这款游戏,排在最上面的是我们,第二个才是游戏官网。”
他们的嚣张行为最终惊动了对方的法务部门。警察在某一天突袭了出租屋,收走了所有服务器,嘉禾被当场抓捕。而他的香港合伙人就此人间蒸发。
“房不是我租的,服务器也不是我买的。”嘉禾点起烟,“我就说是被人雇来看房的,他们没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嘉禾在警察的询问中坚决不承认,最终逃过一劫,但他同时也一无所有了——他跟香港人约定的半年时间还没到,而对方显然是个老手。
接下来的两年,他去了很多地方。有时候是旅行,有时候是工作。他在云南逗留超过半年,那段时间,他拒绝与任何人联系,我至今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只声称又要开始做起私服了,并坚持认为自己的电话有可能被窃听。但我始终怀疑,也许又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离开了这片土地并越境去了泰国,而后面发生的故事,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嘉禾回过一次西安,他父亲找人帮他办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他后来跟我讲:“父亲把那张红封皮的毕业证拿回家里,已经盖好了学校的印章。我母亲在空白的地方填上我的名字,她一边笑,一边抹眼泪说,儿子,你上了10年的学,没想到你的高中毕业证,竟然是妈妈给你写的。”
嘉禾撑着脸,陷入沉默。
他面前的屏幕上,一个兽人正走出地堡,面对大法师所带领的人族军团以及水元素,极力维修着主基地,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很快,所有的兽人都被大法师屠戮殆尽,屏幕上打出“GG”,游戏结束。
“我现在过的挺好的,”嘉禾又点起一根烟,“我现在每个月寄回家的钱,比我爸赚的还多。”他一边说,双手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直播间里本已变少的弹幕再次激增起来——他又送出了一枚火箭。
在嘉禾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我见到了一个荣誉陈列柜,里面摆放着大量游戏手办,以及企业荣誉证书。在这个透明玻璃柜的另一侧,有三个人的照片被放置在显要位置,其中一个正是嘉禾。他穿着西服,头发齐整,笑容干净。在这张照片的上方写着:明星制作人。
■ 7
微信里的小D,和一个陌生女孩站在一起。她靠近他的胸膛,两人双手紧握,围在身前。大红色的喜服包裹着他们,就像两个过年时的福娃。
小D结婚了,但没有通知任何人。他说,在老家结婚,太远了,大家都忙。他的妻子是父亲介绍的,我没法分清他们俩婚前是什么亲戚,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之间存在遥远的血缘关系。
在他发给我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在新房拍摄的,我的注意力被放在桌上的一幅绘画所吸引:那仍旧是一幅说不清风格的铅笔涂鸦,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拖着腐败肚皮的胖子,它面目狰狞,但却惟妙惟肖。
你要守着你美丽的姑娘与工厂,在猎狗跟DOTA的陪伴下好好活着。我在心里想,这就是我对你的新婚祝福。小D像我心里的一张“缺省地图”,那些黑暗的、我还没来得及探索的故事。主角无一例外都是他的父亲。他就像是一个被支配者,而支配者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与游戏绝缘。
希望儿子与游戏绝缘的还有嘉禾的父亲。
尽管被拒绝了无数次,今年春节,嘉禾的母亲还是给他打了电话,而嘉禾仍旧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这令他没有看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我接到嘉禾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赶回家的路上,这是他6年来第一次回家。
在嘉禾的家里,我没法找到任何游戏存在过的痕迹:没有游戏机,没有电脑,甚至连文曲星也不曾出现。这里几乎是一个典型的上世纪照片:遥控器被塑料纸包裹的结实而严密,电视机在不看的时候用布罩遮住。甚至连电话都要被雪白的方巾盖住——尽管这看起来意义不明。
唯一看上去和我们有关的是一部手机。它像是充话费赠送的廉价智能手机,大概由于频繁使用的缘故,机身已经大面积掉漆。它静静的躺在嘉禾父亲的书房里,还保留着接通电源的状态。
嘉禾打开手机,看着屏幕。
他愣住了,脸上渐渐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在定格了几秒钟后,变成一种巨大的痛苦,令他想要吼叫,想要痛哭。我越过他的肩膀,看向屏幕:那上面只有一个软件:一只带着面具,表情妖娆的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