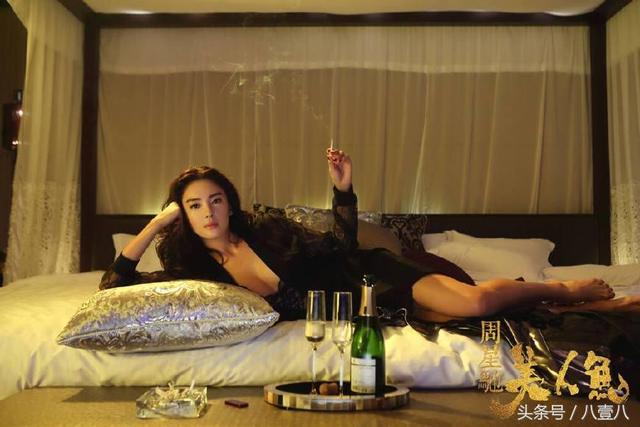李白(701年—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纵观李白一生,既经历了“开元盛世”的繁华,又尝尽了“安史之乱”的颠沛;即曾居于庙堂之高,与天子吟诗作对,与贵妃月下唱和;又曾处于江湖之远,与贩夫走卒为伍,身陷牢狱之灾。李白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一生被裹挟于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与其意象宏大、绚丽多彩的名篇佳句相比,更凸显出其个人命运的悲凉。乾元二年,随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低声唱吟,年近六十、两鬓斑白的李白最后一次乘舟东下,那时他不会想到,距离他人生的落幕,已经不到三年,而那个藏在诗人骨子里的盛唐气象,也已一去不复返了。

1
少年时的李白,仗着良好的家境,也曾怀着对未知世界的一腔热血四处游历,在疏狂中放浪着自己的青春,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资深“驴友”。20-30岁间,李白已然游历了中国南方著名的名山大川,并写下了诗赋多首,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面对年少成名,李白飘飘然,炫炫乎,当然,不可否的的是,他有飘的资本,有炫的底气。当时正值开元盛世,国家财力强盛,物产富足,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游历途中,李白一手持剑,一手持笔,幻想自己是东方侠客,行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之道,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如果说金庸先生早生千年,活与盛唐,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中的种种奇妙武功定能招得诗仙大人开怀大笑,将其引为知己了。
彼时,国家科举已然兴盛,寒门子弟拥有了与宦门之后同场拼比学问的机遇,无数学子恨不得将庙堂三尺门槛踏破,以求一日乌鸡变凤凰,成为衣不携泥、参与军机的士大夫。而李白狂浪放任的性格断断不会俯下身段,日日浸淫在四书五经里,有这个时间,我们的诗仙大人早不知在黄山上饮酒作对几个日夜了。于是,李白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找到了一条不需要科举而照样能当官的“潜规则”——终南捷径。说起终南捷径,不得不提到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则天大圣皇帝作为女人中的“异类”,选人用人也是不走寻常路。话说当时有个叫做卢藏用的人中了进士,却得不到重用。郁郁不得志的他,就写了一篇《芳草赋》,然后跑到了终南山之上做起了隐士。在山中的时候,他跟随道士修习道术,还将辟谷练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以几天几夜不吃饭。可是武则天到了洛阳的时候,他又跑到了离洛阳城很近的嵩山隐居,因此也被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后来,武则天居然听说了他的名声,便将他请出山,任命了一个左拾遗的职务,没有几年他又升到了吏部侍郎,比正常中举的人,升迁更快。后来,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对人说:“此中自有佳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开元十八年(730)夏秋之交,三十岁的李白抱着“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心情离开湖北安陆,经南阳来到长安。李白到达长安后并没有直接进入长安城,而是隐居在距离长安城不远的终南山。李白隐居终南山的目的,《赠裴十四》中说得明明白白:“身骑白,不敢度,金高南山买君顾”,说明了李白隐居终南山的目的是以隐居为手段,自抬身价,以便有朝一日得到君王重用,完成功业。为了实现“买君顾”的理想,李白隐居终南山,并以此为据点四出活动。在长安,他结识了崔宗之,拜见了宰相张说,并结识了宰相的两个儿子,在他们的帮助下李白两次登上终南山楼观台谒见玉真公主。玉真公主作为李白人生路上的第一名“贵人”,也确确实实在唐玄宗面前举荐了他,这才有了之后的奉诏入京和赐翰林供奉。可是,李翰林还是把做官想得太简单的,对厚黑学知之甚少甚至嗤之以鼻的李白,注定在骑鹤扬州的路上碰得头破血流。

2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天,李白时年42岁,在不惑之年除了写下几首小诗供人消遣,入朝之路仍然看不到转机,人到中年而一事无成,不知道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李白大诗人,是否也有怀才不遇、李广难封之叹。然而转机就在此时出现,道士朋友吴筠此时恰在为唐玄宗作法,趁此机会向玄宗举荐了李白,恰逢玄宗听玉真公主多次提起,心生好奇之意,决定宣召李白入京一探究竟。虽然功名并没有如他所愿地“早著”,但是他还是特别兴奋,离家时禁不住吟诗一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长安后,当时的诗坛领袖贺知章一见面就惊为天人,称赞他的诗能够感天动地泣鬼神,并赠雅号“谪仙人”,有了重量级的粉丝加持,李白的名声就此传遍京城。入京伊始,李白的确很受唐玄宗的器重,唐玄宗甚至曾亲自调羹赐死李白,并授他翰林供奉的职位。李白也确实很兴奋,甚至在半路上遇见朋友还表示“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360度无死角地拍了拍唐玄宗的马屁。正当李白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为国家发展作贡献、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李白却发现一切跟他所想象得并不一样。首先,李白发现唐玄宗已经不是那个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的皇帝了,现在的唐玄宗过的是声色犬马的帝王生活。其次,李白发现自己的职位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也不打算让自己施展“经世济国”的才能,唐玄宗看重的只是自己在作诗方面的本事,自己只是皇帝装潢门面、粉饰太平的一个工具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花瓶和摆设。最重要的是,李白在朝廷中呆了一段时间后,明显地感受到了宫廷的中黑暗腐败的一面和权臣之间勾心斗角丑恶现象,这令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李白的性格本来就非常清高孤傲,当当皇帝的花瓶虽说滋味不大好受,还是可以容忍的,毕竟皇帝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但是要他去巴结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皇帝身边的权臣,那是他这种平交王侯、傲视权贵的人所做不到也不屑于去做的。李白的这种高傲的姿态遭到了这些权臣的嫉恨,因此受到了这些人的排挤,他们开始向唐玄宗进谗言毁谤李白,而唐玄宗也就渐渐地冷淡了李白。李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也深深觉得这样的生活跟自己的理想相距太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便主动上表请求退隐,唐玄宗也毫不犹豫的马上批准,赐金放还。于是,三年后,李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玄宗朝廷,当时,他可能仍寄希望于皇帝的挽留和回心转意,殊不知,随着他的离去,他“出将入相”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碎,而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能认为唐玄宗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无数活生生的历史都说明,治理国家还是需要现实和理性,说到底,政治永远是一种博弈和妥协的艺术,而李白作为一名感性大于理性的艺术家,永远不会理解和接受这一点。
在被赐金放还的那一年,李白在郁闷中写下了《梁甫吟》“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山儿屼当安之。”其中,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与春秋时齐相晏子写的“二桃杀三士”的意思相近。看到这,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扑面而来,原来,我们的诗仙大人,也是一个活在世俗名利圈里的俗人啊。从京城出来后的三年,李白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一大批千古名篇均是当时所作,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与艺术魅力,李白盛唐诗坛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就此确立。如果时间的航船就此风平浪静的一步步往前走,那么李白的人生也未必会如此悲催,甚至他可能在诗坛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未可知,可是,命运就是如此喜爱捉弄人,公元755年,一个叫做安禄山的胡人在盛唐强盛的躯体上狠狠地剜了一大块刀疤,而我们心存报国志向的大诗人,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3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中原大地生灵涂炭,遍地狼烟。
此时,李白刚刚续娶了继室宗氏。面对着叛军风卷残云般攻陷了除关东外整个大部分北方重镇,此时,寓居在河南的李白别无他法,携妻子颠沛流离、多方避难,最后隐居于庐山屏风叠。
此时,千年古都长安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唐玄宗携贵妃出走,把大好河山白白扔给叛军。走到半路上,亲兵哗变,高力士在唐玄宗的默许下,用一根弓弦勒死了杨贵妃,那个李白被李白赞誉为“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贵妃经历一世繁华、万千宠爱,终于在马嵬坡这个穷僻之地走到了人生尽头,化为一抔黄土、几处新泥。在马嵬坡,战战兢兢当了几十年太子的李亨面对着国破家亡,再也忍不了一颗悲愤的心:“要走你走吧,我要和唐朝子民在一起,跟叛军决一死战。”至此,父子分兵,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好像无数人生命的轨迹,在此刻相交后,终于渐行渐远,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灵武,李亨登基称帝,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赤裸裸夺了老子的权,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玄宗没有硬扛,在默认被儿子夺权事实的同时,不忘施展一点帝王心术——他下诏让除太子外的三个皇子出任节度使,带兵平叛,这实际上是要利用其它皇子来制约李亨。因玄宗诏令下达时,已经有了新皇帝,有两个皇子就没有奉诏就任,但永王李璘却真的就任了,他被授予的职务是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使。如果一心一意打叛军也就罢了,但永王的举动很不正常,他没有北上平叛,反而带兵东进。明眼人很容易判断出来,永王是想利用这个乱局割据东南,与肃宗南北分治,而这背后是不是玄宗的授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永王要做大事,需要拉拢人心,李白是大文人,很有影响力,自然是拉拢的对象。而李白呢,我相信他面对安史之乱,应该是兴奋多于恐惧,毕竟他跟赵蕤学的那套纵横之术,就是适用于这乱世的。但为什么前面说李白这帝王术学得并不好呢,因为他对局势看得也太不清楚了。咱们也搞不清李白有没有看出永王的反意,但他自己在这期间做的《永王东巡歌》,简直比永王的反意还明显:“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往东去本来就不对,你还来个“东巡”。什么“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这是要干嘛,要勘察定都地址吗。自我感觉也一如既往地良好,“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自比谢安,那么你辅佐的不就是割据的帝王吗?几乎句句都能被人找出把柄来。
放在和平时期,兄弟之间为皇权之争兵戎相见很正常,不至于放到道德层面来批判,玄宗的太皇爷爷李世民,不就把他哥哥的首级割下来扔到了太祖皇帝面前,把李渊吓个半死么。但政治要放到国家大势上面去看,国家都要亡了,你们还兄弟阋墙,为争当皇帝打个你死我活,说到底是不讲政治,况且安史之乱早已把玄宗在人民群众中积累的好印象败坏的干干净净,全国上下巴不得换个领导换种气象,你永王此时此刻带兵东进,那就是枪打出头鸟,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批判唐玄宗的活靶子。当年曾与李白杜甫炼过大半年仙丹的高适,头脑就清醒得多。他跟随玄宗入蜀,受到重用,但在玄宗下诏任命皇子为节度使时,高适是劝阻过的,劝阻不成,玄宗让他去辅佐永王,但高适没去,而是投奔了肃宗,为肃宗分析形势,判断永王必败。于是肃宗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前往江淮平叛。高适还真是不含糊,几个月就打败了永王,李白自然作为叛党成员也被抓了。唐朝四大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只有高适最终以军功封侯,成为一方大员,他后来任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期间,对旅居四川的老朋友杜甫关照有加。但同样是老朋友,高适却并没有关照李白。李白被捕后曾专门给高适写信,请他帮忙,但高适并未回信,反而将自己与李白来往的书信都烧了。我们感慨于世事难料,但对于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高适,或许也有他的苦衷吧,总之,这两位的交情算是断绝了。
好在李白还有最后一丝运气,他最终没有被判死罪,而是流放夜郎。走到四川,正好赶上关中大旱,肃宗大赦天下,李白被无罪释放了。就在归途中,李白写下了文章开头引用的千古名篇《早发白帝城》 。然而,经过多年来的折腾,李白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了他仍然旺盛的精神,仅仅两年之后,李白就病逝于安徽当涂。与他的身世一样,李白因何去世也是一个谜,有说病亡的,有说酗酒醉亡的,民间另有一番颇具浪漫主义风采的传说,说是李白在当涂采石矶饮酒赋诗,酒醉后跳入水中捉月,结果溺水而亡。然而,无论如何,那个“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诗人,还是带着他的不甘和抱负走了,如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李白就是那个捉月而逝的癫狂之才,他用他的诗、酒、江、月,为缓缓落幕的盛唐挥笔写就了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最美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