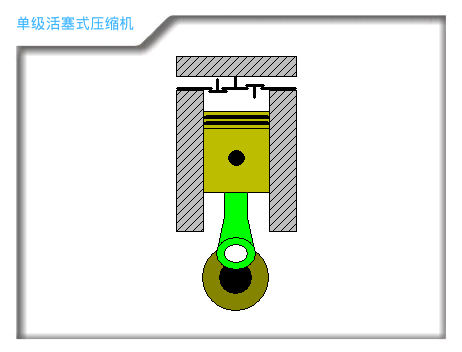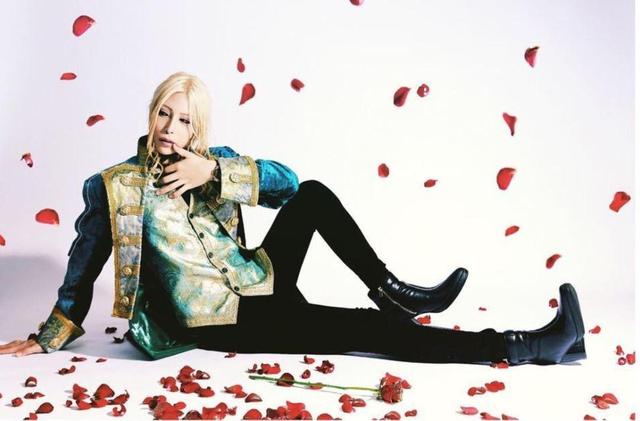分析的时代与时代的分析
20 世纪的英美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 哈佛大学的怀特教授(M . White) 干脆就把20 世纪称为“ 分析的时代” 。 分析什么? 分析语言。 如何分析? 用逻辑进行分析。 那么, 为什么要分析?我们知道, 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于一些基本问题: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本体论、 形而上学的问题; 人能知道什么? 这是认识论、 知识论的问题; 人应该成为什么? 这是伦理学、 人性论的问题。 每个哲学家都想创造一个哲学体系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每个哲学家都自认为自己的体系解决了这些问题,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自是而非彼, 美己而恶人, 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哲学园地简直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 历史终于等到最大体系制造者黑格尔出来收场了:“ 你们都别吵了, 你们的体系都收容在我的体系中了。” 不幸地是, 这也不过是一个体系而已, 费尔巴哈、 马克思起来反对它的唯心主义, 基尔凯郭尔、叔本华起来反对它的绝对主义、 理性主义, 当然反对它的诸体系又成了其他体系反对的对象, 哲学的争吵还有没有完?反观数学与自然科学, 欧氏几何的三角形内角和是180°是无人争吵的, 牛顿定律是无人争吵的, 水的分子式是 H2O是无人争吵的。 一个科学问题解决了,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新的问题解决了, 更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科学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 研究生物学的人不必再去亚里士多德那 里 讨 个 说 法, 但 研 究 哲 学 的 人 呢? 怀 特 海 (A ·Whitehead) 说, 整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真的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早在19 世纪30 年代以孔德(A · Comte) 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就提出了哲学应当以自然科学为楷模, 以观察与实验的实证知识取代传统哲学的抽象、 思辨的知识, 那些超出人类实证知识范围、 专以探讨现象背后的物自体为己任的传统形而上学必须被摒弃于知识之外。

到了70 年代, 以马赫(E · Mach) 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更一步发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是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 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领域, 在现象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自体, 人类知识的范围就是感觉经验的范围。 这样, 哲学家逐渐从认为哲学问题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到怀疑或许就根本不存什么哲学问题的领域。 科学问题之所以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之所以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最后人们怀疑到了语言的头上, 是的, 哲学问题的表达是有问题的, 这一步就是分析哲学家迈出的。分析哲学家拿起逻辑分析这把剃刀, 对传统哲学问题一一进行解剖。 他们不再去问“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而是要问“ 世界” 是什么意思?“ 本质” 又是什么意思? 这一问不要紧,结果发现许多哲学术语, 许多哲学命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哲学家之争原本不是什么事实之争, 全是语言之争; 他们也不去问“ 我能认识什么?” 而是问“ 我能表达什么?” ; 他们也不去问“ 我应成为什么?” 而是问“ 我应成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它和我是什么意思一样吗?” 分析语言便成了分析哲学家的首要任务, 分析哲学家是哲学家的哲学家。这些运动的先驱人物当推数学家、 逻辑学家、 哲学家弗雷格 (G · Frege, 1848—1925) , 分析哲学的三位巨头罗素、维特根斯坦、 卡尔纳普都承认受到他的直接影响。 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 一书的序言中坦承“ 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 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的” , 维特根斯 坦在其《逻辑哲学论》 中也真诚地表示是弗雷格的著作“ 激发了” 他的思想, 至于卡尔纳普他是弗雷格在耶拿大学任教的学生。 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在生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他讲课经常使用一大堆符号, 因此前来听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 学校对他的教学评价也不高。

一直等到他死后, 思想界才真正发现了这位思想家的价值, 他被认为是现代逻辑的奠基者, 是分析哲学的精神先驱。 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可归为以下三方面。一是他的反心理主义思想。 他在《算术基础》 第一次提出要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 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区分开来, 意义与逻辑的客观性质完全不同于心理过程的主观性质, 他认为应将判断的内容与判断的活动区分开来, 1 十1= 2 这是判断的内容, 它是完全客观的、 公共的, 可以交流的; 但每个人进行的1 十1= 2 的判断活动则是主观的、 个人的, 一个小孩子在进行1 十1= 2 的判断活动时, 可能心中想的是1 个苹果加另1 个苹果是2 个苹果, 另一个小孩子可能想的是1 个布娃娃加另1 个布娃娃是2 个布娃娃。 逻辑并不研究人们如何作出如此这般的判断, 它只研究思想本身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这就与笛卡尔以来将一切还原到人的内在心理过程的心理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了。 从此分析哲学从传统认识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研究转向了对意义、 对客观知识的研究。二是他的命题函项理论。 2· X3+X 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其中X 是自变元, 如果把这个自变元除掉, 这个表达式就成了2· ( ) 3+ ( ) , 因此, 任何一个函数解析式都可被分析自变元符号与函数式两部分, 函数式本身是不完整、 不饱和的、 需要补充的。 弗雷格把这一函数理论运用到概念与命题的分析之中, 比如说“ 凯撒征服高卢” 这个句子就可分析成“ 凯撒” 与“ 征服高卢” 两部分, 其中第二部分是不饱和的, 它带有一个空位“ —— 征服高卢” , 只有通过代入一个专名或一个代表专名的表达式, 才会出现一个完整的意义, 这个不饱和的部分称作函数, 自变元是凯撒。 又如“ 德意志帝国的首都” 这一表达式即可被分析为“ —— 的首都” 和“ 德意志帝国” 两部分。 “ X 的首都” 这一函数表达式, 如果我们以德意志帝国作为它的自变元, 我们就会得到柏林这一函数值, 如果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它的变元, 我们就会得到华盛顿这一函数值。 命题函项论对于后来分析哲学分析命题、概念启发颇大。

三是含义和指称的区分。 这一思想表达在1892 年发表的《含义与指称》 一文中, 这里分析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章,它开了分析哲学意义理论研究的先河。 问题始于同一性命题所产生的困惑, 比如a= a 和a= b 显然具有不同的认识价值,说“ 弗雷格是弗雷格” (a= a) 和说“ 《含义与指称》 的作者是弗雷格” (a= b) 毕竟不是一回事, 尽管《含义与指称》 的作者确实就是弗雷格。 为什么? 弗雷格认为我们必须在含义和指称之间严加区分。 名称的指称是它所指涉的对象, 名称的含义则是它所表达的意义, 我们用“ 月亮” 这个词指称月亮这颗卫星, 而含义则是一种表达式, 通过含义名称告诉我们它指称什么。 比如说“ 《含义与指称》 的作者是弗雷格” 在这个句子“ 《含义与指称》 的作者” 与“ 弗雷格” 这两个表达式指称同一对象就是那位在耶拿任教的弗雷格本人, 但两者的含义不同。 又比如, “ 晨星就是暮星” , 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晨星和暮星确是指同一个星(金星) , 因此两者的指称是相同的, 但两者的含义却不同, 晨星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在早上什么时候什么方位才能找到它, 而暮星这个名字则告诉我们在晚上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它。 一旦将含义与指称加以区分, 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名称只有含义没有指称, 如“ 最小的收敛级数” 这一表达式就只有含义而无指称, 因为对每个收敛级数都可以发现一个更小的而且还不断收敛的级数。 不同的含义也可以指称同一个对象, 暮星与晨星含义不同但却指称同一个对象(金星) 。 弗雷格还进一步将含义和指称的区分运用到命题上面, 认为句子的含义是它表达的思想,命题的指称是它的真值, 真值就是句子是真或假的情况。“ 晨星是晨星”“ 晨星是暮星” 这两个句子真值相同, 即指称相同,但意义不同。弗雷格早期在进行逻辑研究时就发现日常语言的不完善性与模糊性, 他提醒人们“ 语言很容易引导我们去错误地看待事物” , 并宣称“ 哲学家的绝大部分工作在于—— 至少在于—— 同语言作斗争” , 在于“ 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 , 他的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科学和哲学的理想语言。

这种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以及对理想语言的追求, 在分析哲学运动中颇有影响, 它直接开启分析哲学中的“ 理想语言学派” (又称“ 人工语言学派”) , 罗素, 早期维特根斯坦、 卡尔纳普即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 与这一学派唱对台戏的是“ 日常语言学派” , 它坚持日常语言是值得信赖的, 哲学问题的产生恰恰是因为违背了语言的日常用法, 因此与此诉诸华而不实的人工建构的语言, 还不如诉诸日常语言, 摩尔、 后期维特根斯坦、 剑桥学派、 牛津学派即持此种观点。
摩尔: 如何用手反驳唯心主义
摩尔(G · Moore, 1873—1958) 可能是哲学史上最质朴的思想家, 这当然是指他的思想。 他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但他从不喜欢卖弄哲学的大道理, 更不会用怪诞的术语冒充深刻。 当唯心主义者装模作样怀疑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时, 摩尔教授就立刻伸出手来加以证明, 他举起自己的双手, 用右手作了一个手势说: “ 这是一只手” , 接着, 再用左手作一个手势说: “ 这是另一只手” , 于是凭这双手就证明了外界事物的存在。 唯心主义者当然不会买摩尔的“ 手帐” , 他们会问:“ 摩尔教授你真地认为你是伸出两只手吗?你难道敢保证你不是在梦中伸出两只手?”当黑格尔主义者宣称“ 时间是非实在的” , 摩尔老老实实地说:“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事件在另一事件之后或之先, 那你肯定搞错了; 因为午饭之后我去散步了, 散步之后我又洗了一个澡, 洗澡之后我还喝了茶。”下面是摩尔哲学的专家马尔科姆(N · Malcolm) 为摩尔反驳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设想的一张清单。哲学家: “ 空间是非实在的。”

摩尔:“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在别的东西之右或之左, 之后或之上, 那你肯定是错了; 因为这个墨水瓶是在这支钢笔的左边, 而我的头是在它们的上面。”哲学家: “ 没有人感知过物质的东西。”摩尔: “ 如果你所说的‘ 感知’ 是指‘ 听’ 、 ‘ 看’ 、 ‘ 感觉’ 等等, 那么你这个说法就是再谬误不过的了; 因为我此时就在看和感觉着这支粉笔。”哲学家“ 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不被感知而存在。”摩尔:“ 你所说的是荒谬的, 因为昨晚在我睡觉的时候并没有人感知我的卧室, 然而它肯定存在。”哲学家:“ 人在视察事物时所看到的一切乃是人脑的一部摩尔:“ 我俩此时都看到的这张桌子决不是我的大脑的一部分, 而且事实上我也从未看到过我自己的大脑的一部分。”哲学家: “ 你怎样证明认为你自己的感觉、 感情、 经验是唯一存在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呢?”摩尔: “ 我的证明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正在看我, 听我讲话, 而且我还知道我的妻子正在患牙疼, 因此我就得出结论除了我自己的感觉、 感情、 经验之外还存在着别人的感觉、 感情、 经验。”哲学家:“ 你并不确实知道除了你自己的感觉经验之外还有任何别的经验。”摩尔: “ 恰恰相反。 我知道你正在看我, 听我说什么, 这是绝对确实的, 我的妻子正在患牙疼, 这也是绝对确实的。 因为我知道除了我自己的感觉经验之外还存在着别人的感觉经验, 这是确实的。”哲学家:“ 我们并不确实关于物质的东西的任何论断是真是假。”摩尔:“ 我俩都确实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几把椅子, 认为我们并不知道而只是相信这一点, 认为情形也许不是这样, 该是多么荒谬啊!”哲学家: “ 所有的经验的论断实际上都是假设。”摩尔:“ 我在一个钟头前吃了早饭这个论断肯定是一个经验的论断, 把这个论断叫做假设是可笑的。”……摩尔就这样靠老老实实的诉诸“ 常识” 来揭示某些哲学命题的荒谬性。 在捍卫常识、 拒斥唯心主义方面他表现出的坦率与天真在哲学史上的确别具一格, 令人难忘。

他反复声明每一个正常的人, 只要他是真诚的、 老实的, 他就会承认他有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出生在某个时候, 从此一直存在着,当然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化, 自出生以后, 它一直同地球表面接触或离得不远; 在它出生后的再一刻, 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具有三维形状积大小的东西, 身体离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距离(在身体现在离壁护和书橱都有一段距离而且离书橱比壁炉要远这种大家熟悉的意义上) , 还存在一类和身体接触的别的东西 (身上穿的衣服、 手上戴的手表这种大家熟悉的意义上) ; 从它出生的每一刻存在着大量其他活的人体, 它们每一个都和它同样在某一时间出生, 出生后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出生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和地球表面接触或离得不远, 而且许多这些身体已经死去, 当然在这个身体出生之前, 地球就存在了很多年……最后这个身体从出生之日起就拥有各种各样的经验, 它能看到壁炉、 书橱这样的物体, 它还会做梦、 还会想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幻想, 其他人的身体也有自己的经验。总之, 宇庙中存在着大量的物质客体, 人有一系列的意识活动, 人实际也完全知道存在着物质客体和意识活动。 这些命题是人们确确实实知道的, 它们是确定无疑的, 是每一个人不加思索就相信的, 是常识的。 但是很多人过去相信而且现在还仍然相信上帝肯定存在, 上帝的存在难道也是确实无疑的常识吗? 摩尔的答复是, 上帝的存在对一部分人或许是确定的信念, 但还有许多人现在相信即使上帝存在, 我们也确实不能知道有一个上帝, 因此应该说, 常识对我们是否知道上帝存在这个问题没有看法, 它既不断言我们知道, 也不断言我们不知道, 关于“ 来生” 的信念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 常识乃属于人类普遍同意的确定无疑的信念, 这样一些信念我们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 真可谓心照不宣, 用不着饶舌, 也用不着给出什么理由或论证, 实际上很多常识的信念是如此确凿以致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它们, 也不知道去如何证明它们的。如果事实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那么哲学的怀疑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哲学家在怀疑苹果是否是实在的, 牙齿是否是实在的之时, 他在用牙齿的感知咀嚼苹果的感知之时, 难道会比平常人用牙齿本身去咀嚼苹果本身有什么不同比如在营养吸收方面、 味道品尝方面? 哲学的怀疑与解释的价值究竟何在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摩尔老是唠唠叨叨一些人人皆知的大实话就认为他或许根本就缺乏从事哲学分析的能力所以才拚命嘲弄那些善于哲学思辨的里手, 就像那位希腊的女仆嘲弄沉思天外之事的泰勒斯掉进井里一样。 早在1903 年摩尔就发表了《驳唯心主义》 一文, 这篇文章对柏克莱“ 存在就是被感知” 命题做了细致、 深入的分析, 学术界通常将该文章的发表视作英国分析哲学运动的开始。 也就在同一年他的《伦理学原理》 一书也问世了, 这是一本直觉主义伦理学的经典之作, 也是现代元伦理学的一个源头, 在这本书中, 摩尔表现了高度细致的分析技巧。该书把传统伦理学中将善定义为快乐、 定义为可欲的对象、 定义为善良意志等等种种企图用自然事物或超感觉事物来为善下定义的尝试统统斥为“ 自然主义的谬误” , 对于每一种为善下的定义, 我们都总可以问它本身是不是善的。 比如有人将善定义为快乐, 我们就可以完全问他:“ 快乐本身就是善吗?” 这就说明所要求的定义语和被定义词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确实如果有人以杀人为乐, 我们能说杀人就是善吗?善是简单的、 非自然的、 不可分析的, 它不能用任何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来定义它, 比如给马下定义, 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四条腿, 一个头, 一颗心, 一只肝等等, 它们之间结成一定的关系, 但善呢? 善是没有组成部分, 是非自然的, “ 如果问我‘ 善是什么’ ? 那么我的回答是, 善就是善, 这个问题即使追根究底也是如此。 或者如果问我:‘ 怎样给善下定义?’ 那么我的回答是, 它不可能下定义, 这就是我对此所能说的一切。” 善是不可定义的, 但它可以被直觉到。

比如说“ 黄” , 是难 以给出定义的, 有人指着某些黄的东西说“ 这是黄的” ,“ 这不是黄的” , 这样人们就知道了黄, 同样, 善也是完全可以被直觉到, 人们也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善这个词。 由此看来, 善是一个规范词, 不是一个事物词, “ 应当” 就是“ 应当” , “ 是” 就是“ 是” , “ 应当” 与“ 是” 不可混淆。 摩尔以后的分析哲学的伦理学, 不再去思考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权利、 人生的义务, 反而去分析“ 目的” 、 “ 权利” 、 “ 义务” 这些词的意思是什么, 去考察伦理学命题与事实命题的逻辑形式有什么不同等等, 这一切都是由摩尔开了头。 他在《伦理学》 一书的前言断然宣称: 在伦理学如同在一切哲学学科中一样, 充满着种种困难和争论, 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 即由于没有真正先发现你所希望回答的问题时什么,就试图作答……有了摩尔的这句话, 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们变得乖巧多了, 他们再也不忙于回答问题了, 相反对于人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都要先问一下, 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它真的是一个问题吗?用手反驳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者当然不会接受; 只分析伦理命题, 而不回答伦理问题, 传统伦理学家也不会满意。 但是分析语言, 诉诸常识, 仍不失为一种从事哲学工作的方式。当人们对激进的理想主义失去兴趣, 对晦涩的术语、 繁琐的论证、 抽象的体系失去耐心之时, 朴实无华也就显得愈发可贵了, 摩尔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罗素: 世纪的智者
在世人的心目中, 哲学家不外是托着下巴的“ 思想者” ,他们孤独、 忧郁、 内向, 或许还有些贫血或消化不良, 既能在哲学的躺椅上进行哲学沉思又能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一下身手, 既能在时代哲学中弄潮又能在数学、 自然科学中露出几式绝招而不是花拳绣腿, 既能准确地表达自己艰深的哲学思想又能使行文不失文学家的流畅甚至还因此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牌, 这样的哲学家在20 世纪只能推罗素 (B · Russell,1872—1970) 一人而已。罗素的创造力非常惊人, 他如一头多产的奶牛, 几乎每天都能挤出一些新鲜思想来, 他一生留下了上百部著作和上千篇文章, 哲学、 数学、 逻辑学、 物理学、 生物学、 心理学、政治学、 民族学、 教育学、 军事学、 伦理学、 神学, 文学——几乎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 他的生命力也非常旺盛, 他活了整整98 岁, 一生结过四次婚,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天性使他在肉体上喜欢一个女人不能超过七八年; 他的著作也非常畅销, 其行文严谨而又不失幽默, 如行云流水, 欢快清新, 爱因斯坦说“ 阅读罗素的作品, 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 罗素是名副其实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是世纪的智者。他曾说过: “ 我的一生是由三种单纯而强烈的热情支配着: 对爱情的渴望, 对知识的探究以及对人类苦厄的难以遏制的同情心。” 他在17 岁时就爱上比他大5 岁的艾莉丝, 几经曲折在22 岁时才与她结婚, 但婚后6 年便开始分居。 这时他的同事怀特海教授的夫人走进了他的生活。 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 一书正是他饱受爱情折磨, “ 发泄无法控制的感情的产物” 。 不久有夫之妇奥托琳又成了公开的情妇。 9年之后, 他又“ 同时爱上了” 海伦、 柯丽和陶娜三位女郎, 对其中的每一位都“ 依依不舍” , 但最终与有8 个月身孕的陶娜结成良缘, 柯丽以后成了他的情妇。 他们本想在伦敦安家, 但房主拒绝租房给这位现代的唐璜。 又是9 年之后, 牛津大学的女学生柏翠霞成了他第三任妻子。

芬斯则是他八十高龄时的第四任妻子。 罗素一生对性一直抱着自由主义的开放心态,爱情是自由的, 不应受任何感情之外的东西的影响, 一旦感情上出现裂痕, 爱情就应中止, 这是他在《婚姻与道德》 一书中表达的思想, 他这样说了, 也这样做了。 他还著有《快乐之道》 大力鞭挞禁欲主义, 认为蔑视快乐就是蔑视他人的幸福, 同时也是对人类仇恨加上一层虚伪的糖衣, 任何矫情、抑情都会使人格扭曲, 人生应自然而然, 率情任性, 他这样说了, 也这样做了。罗素也是世界闻名的政治活动家, 他的祖父曾两度出任英国的首相, 但罗素本人从事政治活动却不是为了作官, 他是出于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心, 早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他就积极投入反战活动, 他发表的十分动人的反战演说堪称反战演说方面的典范:“ 作为一个真理的爱好者, 我对参战国所做的宣传感到恶心; 作为一个文明的爱好者, 这种回复到野蛮人的战争举动, 使我震惊; 作为一个有父母之亲情的人, 看到年青人被屠杀, 使我心痛如绞。 我并没有期待反战运动会有什么成果, 但为了人性的尊严, 没有被潮流卷走的人, 都应该坚强地站起来。” 反征兵协会的传单据说就是出自这位大哲学家之手, 他也因此以“ 制造不利于英王陛下军队之征兵及军律之言论” 的罪名而被监禁了两个月, 他在三一学院的职位也因此被免掉了, 这时哈佛给了他一个教授的位置, 但政府拒绝给发护照。 在服刑期间他撰写了《数学哲学导论》 一书。 在60 年代, 他提出了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 为此他说服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共同签署了一项支持为和平而协力合作的宣言即“ 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 , 并一度担任废除原子武器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1961 年, 年近九十的罗素又一次因静坐示威、 煽动市民反抗政府的罪名而被法院判处两个月监禁。 古巴危机、 中印边界纠纷、 苏联犹太人问题他都要插上一手, 肯尼迪被刺后, 他又做了英国“ 谁杀了肯尼迪委员会的主席” , 越战爆发后他出版了《越南战争的罪恶》, 就在他去世的前两天, 他发表了他一生中众多声明中最后一份声明, 谴责以色列发动的中东战争。现在我们就看看罗素又是如何追求哲学知识的。

罗素的哲学往往被称为“ 逻辑原子论” , 但要理解它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们还得把目光转向19 世纪以前。 我们知道, 传统哲学都是以建立形而上学的体系为己任, 到了康德, 他用批判的大手敲响了思辨形而上学的丧钟, 然而后继的费希特、谢林、 黑格尔依然如故地建构自己形而上学的体系, 仿佛老康德不曾来过这世界一样, 这一崇拜体系的时代最终贡献出了哲学史中最大体系的制造者黑格尔。 我们已重复过别人已说过无数次的老话, 现代哲学是从反黑格尔开始的, 罗素反叛黑格尔主义的武器就是逻辑原子论。原子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早在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那里就产生了, 他将世界上的东西分到不可再分的终极存在物即原子, 世界最终是由这些种类不同的原子构成的。 在数学与逻辑学方面造诣颇高的罗素则把逻辑融进了原子论之中,或者说尝试建立一种原子论的逻辑, 并以此来消解黑格尔的绝对一元论, 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事物, 草是绿的, 天空是蓝的, 太阳和星星即使没有人知觉它们时也会存在, 当然还有数学定律这样一些超时间的理念世界,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绝不是一个什么唯一不可分的实在的假象。 在逻辑原子论的语汇中, 构成命题的语汇除了“ 或者” 、 “ 非” 、 “ 如果” 、 “ 那么” 这些逻辑常项外, 都是与外在相应的事实相关联的。 对应于每一个简单的对象, 有且只能有一个词与之相对应, 这就是“ 逻辑原子” ; 对应于每一个简单的事实; 则有一个“ 原子命题” 与之相对应, “ 这是红的” 、 “ 这个在那个之前” 都是原子命题, 它们与其断定的外部世界中的原子事实上是一一相应的, 原子命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从一个原子命题无法逻辑地推出另一个原子命题, 从“ 这是红的” 并不能推出“ 这个在那个之前” 。 原子事实也不是通过推理得来的,原子事实是感性知觉的事实, 它和纯粹逻辑无关, 纯粹逻辑和原子事实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完全先天的, 一个是完全经验的。 借助于逻辑和原子命题就可构建分子命题, 分子命题的真假最终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逻辑原子论成了20 世纪的奥卡姆剃刀, 有了这把剃刀,就可以剃掉一些不必要的术语, 以获得“ 最少词汇量” , 获得最少量的实体、 要素、 前提(即逻辑原子) , 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术语(如“ 绝对精神”) 便因此失去了本体论的意义。 最少词汇量原则的核心就是在讨论任何复杂符号或观念体系时,在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时, 应先弄清楚构成这些符号或体系的最少的真正的组成部分或要素是什么, 这套哲学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法, 逻辑原子论充分体现了分析哲学的精神。

按照这一原则, 罗素对我们的语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并提出了确定的摹状词理论, 这一理论是罗素对现代分析哲学的一大贡献, 被评论者认为是现代哲学的“ 典范” 。 “ 这个穿黑衣服的男人” 、 “ 这些黑色的狗” 等等,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解决确定摹状词问题的, 比如说“ 金山不存在” , 什么东西不存在? 金山不存在。 仿佛金山又成了某种东西一样。 如果金山不存在这个陈述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没有金山这样的东西, 而如果金山一词有意义的话, 那就应存在某个为该名称所指的东西。 这一难题在哲学史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奥地利的哲学家迈农(A · Menong) 就首先提出一种对象理论,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谈论像“ 金山” 、 “ 圆的方” 这样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是因为它们作为对象在逻辑上是存在的。 罗素当然不会对这种增加实体的做法满意, 摹状词理论就是来解决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命题的主词。 又比如“ 现在的法国国王是个秃头” , 根据排中律A 是B和A 不是B 必有一真, 因此它与“ 现在的法国国王不是个秃头” 必有一真, 但我们先列举所有的秃头, 然后又列举所有不是秃头的人, 在任何一列中都找不到这个现在的法国国王,喜欢综合的黑格尔主义者可能会有了结论: 他戴着一头假发,惯开玩笑的罗素在此也忘不了讽刺一下黑格尔主义者。 另外还有一种同一律的普遍适用问题, 如果A 等于B, 那么任何适用于A 的东西也必适用于B, 反之亦然, 假如“ 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否是《瓦弗利》 一书的作者” , 而且事实上司各特就是这位作者, 那么我们根据同一律原则, 就可以用“ 司各特” 来替换这位“ 《瓦弗利》 的作者” , 这样原来的陈述就成了“ 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不是司各特” , 乔治四世这位在欧洲受过头等教养的人在此只对同一律发生兴趣, 这是无法让人相信的。解决这些混乱的关键在于区分专名与谓词表达式。“ 司各特” 、“ 乔治四世” 这些都属于专名, 它代表一个特殊的个体,它的意义即指称一个具体的对象, “ 司各特” 这个专名即指司各特这个具体的人; “ 《瓦弗利》 的作者” 、 “ 中国的首都” 、“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这些是确定的摹状词, 它指述某一特定事物某方面的特征。

确定的摹状词与专名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一但经过逻辑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 确定的摹状词不过是一个“ 不完全的符号” , 一个不饱和的X, 因而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 还是让我们回到罗素的例子上来。关于“ 金山不存在” , 金山只是一个摹状词而不是专名,它可被分析为: 就X 的一切值而言 (1) X 是金的 (2) 有且仅有一个对象与X 等同, 并且(3) X 是金的。 这样原来作为主词的“ 金山” 就已不再作为主词而成了谓词了; 同样, 关于“ 现在的法国国王是个秃头” , 经过逻辑分析“ 现在法国国王” 这个摹状词也不再处于命题中的逻辑主词的地位, 经过分析的句子应是这样: 有一个对象譬如说X, 使得(1) 有一个对象是现在法国的国王(2) 有且仅有一个对象与X 等同并且 (3) X 是秃头。 关于“ 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否是《瓦弗利》 的作者” , 其中“ 司各特是《瓦弗利》 的作者” 的真正的逻辑形式是“ 有一个且仅仅一个对象写了《瓦弗利》, 并且司各特与这个对象是同一的。” 这样“ 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否是《瓦弗利》 的作者” 实际上是指, 乔治四世想要知道,是否有一个且仅仅一个人写了《瓦弗利》 并且司各特就是这个人。 这样一分析, 整个子虚乌有的领域诸如“ 圆的方” 、“ 太阳神” 、 “ 木的铁” 等等都可以得到妥善地处理了。我们不要小看罗素这一近乎语言游戏的小小变动, 它可启发了整整一代人的思路, 哲学家们从此真正意识到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往往与其真正的逻辑结构并不一致, 所以才有必要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 逻辑才是哲学的本质。 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问题, 比如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 按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专名和摹状词在逻辑地位上根本不同, 摹状词不能作命题的逻辑主词, 只有专名才有资格作主词, 而一旦专名作主词出现, 它的指称物的存在已不言而喻地蕴含其中, 因此在严格的逻辑句法中, 专名与存在是不能连在一起的, “ 存在” 根本就不是一个谓词。

为了严格起见, 我们还得指出, 罗素后来认为上述例子中的专名都是些“ 普通专名” , 如果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 这些普通专名往往也不过是一些改头换面的确定的摹状词而已。 比如说“ 苏格拉底” 看似一个专名, 但我们今天使用苏格拉底这个词时, 实际上是在使用一个摹状词, 我们无非是说“ 这位柏拉图的老师” 、 这位自愿喝毒酒的哲学家” 、“ 这位为逻辑学家断定为会死的人” 等等, 真正的专名只能是逻辑专名, 它特指那些不能用确定的摹状词来表述的东西, 这种意义上的专名或许只有“ 这” 或“ 那” 这样纯粹的指示词。这里牵涉到罗素的知识论的看法, 比如说“ 故宫在北京市” 这样一个命题, 我们可以问你知道故宫在北京市吗? 一个人可能说, 我当然知道, 我对它很熟, 我就在里面当清洁工, 我还在里面住过几夜呢; 另一个可能说, 我当然知道了,小时候历史书上就讲过, 以后在《末代皇帝》 的电影中又看见过。 前一个人的知就是“ 亲知” , 后一个人的知只能算是“ 摹状的知” , 是道听途说得来的, 是由他人的描述得知的。 一切摹状的知最终依赖于“ 亲知” , 复合命题都最终可以分析为原子命题, 而“ 亲知” 最终的形式就是当下的感觉, “ 这是红的, ” “ 那是蓝的” , 等等。罗素另一个重要的哲学建树是“ 类型论” 这涉及到著名的罗素悖论问题即“ 由所有不是自身的分子的类构成的类” 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技术表达比较抽象, 我们且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表示它, 一个理发店的理发匠就说是A 吧, 他给自己定了一条严格的规矩: 他只给那些不亲自动手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设若B 从不动手给自己刮胡子, 那么按规矩, A 就给B 刮胡子; 设若C 天天自己动手刮胡子, 那么按规矩A 就不给C 刮胡子。 罗素的悖论是: 这位老A 给不给自己刮胡子?如果他亲自动手给自己刮胡子, 那么按规矩他就不应给自己刮胡子; 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胡子, 同样按规矩, 他就应给自己刮胡子。

这个悖论难倒无数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它的原型就是著名的“ 说谎者悖论” , 一位克里特人恩披美尼德说“ 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悖论表达得更简单一些: “ 我现在在说谎” 这到底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罗素的解决方案就是类型论。 他认为, 说谎者之类的悖论的关键在于恶性循环的推理, 在于不合性全体的关涉, 说到那种不是作为本身成员的类是或不是它本身的一个成员,其实既非真亦非假, 而是无意义的。 当说谎者在说“ 我在说谎” 时实际上是在断定“ 我断定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 , 而这一断定本身涉及到了他的那些断定的全体, 而且同时又把这一断定包含在这一全体中了, 于是才有悖的产生。 罗素的建议是, 我们必须把涉及某个命题全体的命题同并不涉及这一命题全体的命题区分开来, 那些涉及某个命题全体的命题决不能成为这个全体的分子。 换言之, 我们必须把命题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如果他说, 我正在断定一个第一类型的假命题,那么事实上, 既然他这个陈述涉及第一类型命题的全体, 这个陈述本身就是属于第二类型, 因此, 他说他正在断定第一类型的假命题就不真, 因而他仍然是一个说谎者。 同样, 如果他说他正在断定第30000 个类型的假命题, 那么这个断定本身就是第30001 个类型的陈述, 因此他仍然是个说谎者, 悖论因区分不同的逻辑类型而消失了。罗素本人曾说过, 哲学价值的大部分在于问题本身, 而不在于问题的答案。 这句话用于评价罗素本人的哲学思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他的逻辑原子主义、 他的知识论、 他的摹状词理论、 他的类型论都受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判, 但他提出的问题本身, 他提出要区分命题表面形式和真正的逻辑形式, 要区分不同的逻辑类型等等, 却整整影响一代分析哲学的发展, 他是无愧是时代的巨人。值得一提的是, 与许多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哲学家不同。 罗素对中国充满着浓厚的感情。

1920 年他应北京大学之邀, 携自己的情人陶娜访问中国, 当时英国政府一直对罗素的行踪加以秘密监视, 并明确表示如果罗素在中国散播破坏英国政府利益的言论就应采取坚决行动, 其中包括建议中国政府驱逐他出境。 他的名字很快就被英国军事情报当局列入了“ 凶手、 特务和不光彩分子” 的名单中的第6 名, 罗素在上海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杭州之游则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给奥托琳的信中说“ 这个国家比意大利更古老, 更富有人情味, 这里风景如画, 人民乐观, 和蔼可亲, 比任何我知道的国民都更爱笑……” 在长沙他会见了当时来中国讲学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 在北京他对1500 名学生发表演讲, 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了听讲。 中国学术界对罗素的兴趣甚高, 专门组织了“ 罗素研究社” , 发行《罗素月刊》。 不巧的是在一次去保定的演讲中, 由于他不穿大衣而患了重感冒, 等到到北京时已奄奄一息, 日本的报纸误传他病死在中国, 在英国的报纸上, 罗素离婚的消息和他病死在中国的消息同时登出,一家宗教性报纸说, 他们听到了这位反基督教的罗素已死的消息感到松了一口气。 罗素事后恢谐地说, “ 我想他们发现我还未死时, 也会再叹一口相反的气了。”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罗素活下来了, 当时中国人告诉他, 如果他真死了, 中国人会在中央公园给他举行一个盛大葬礼, 然后把他安葬在西湖边,并盖一座庙纪念他。“ 我真有点遗憾这事竟不得实现, 不然我就变成了一个神, 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 那该是多么有趣啊!” —— 罗素如是说道。 回到英国后罗素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英帝国主义在中国》、 《英国在中国的愚蠢行为》 抨击包括英帝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与侵略。 他还多次盛赞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勤奋好学的中国人民。 在他著的《中国问题》 一书中, 他建议中国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 他还提醒中国人民, 应该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以防备日本的侵略势力, 他同时还指出, 中国老百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可能会有一天转化成炽热的盲信, 这种盲信会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后来的历史证明, 罗素所说的这一切都一一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