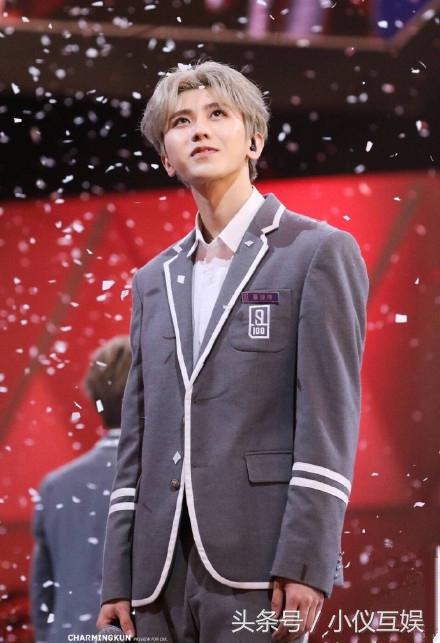邓建华
“你这个业务我不想接。”我对老朋友陶海音说。跨度30年,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时事评论、新闻报道等,这样用情、用心、用力的作品集,摆在这里一大堆,你要我从哪里下手?
海音几个哈哈盖了过来说:“我还不知道你,这样吧,我不为难你,你想怎么策就怎么策,反正就你来搞几句话。”
我头皮发麻,想再推,一时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理由了。我自叹命苦,怎么偏偏和这些勤快人做了朋友。我把自己关在书房,看了一天书稿。我们家的小人儿不时来问,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不能够被他打搅,就说,天书。是的,我被这本彻头彻尾不按常理编织的书绊倒了。
安静下来后,我细细揣摩,终于窥见了一个中年男人求学、就业、履职、成家、圆梦的踉跄足迹,也隐约听到了一管孤独的陶笛在拼命吹奏大海的声音。
陶海音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生命的符号,是我毫不犹豫抓住不放的三个特别意象,如同在池塘边扑到的三只红蜻蜓。
望城人对陶不陌生,陶是望城的名片。神秘的“黑石号”冒出来后,许多的陶艺家顺着时空隧道退回去,鼓捣起老祖宗的柴烧窑来了,拉、捏、刮、刻、镂,杯、盘、碗、碟、罐,十八般武艺用尽。窑门一开,喝彩一片。我看海音这本书,就一个活脱脱的柴烧窑。作者当过临时工、做过小科员、干过大记者、任过一官半职,生活场景不停变换,但不变的是他对生活本质的体悟,对生存趣味的文化场域、人际关系以及漫漶出来的精神气息进行的不懈解读。饮食起居、喜怒哀乐、进退留转、春夏秋冬,熟稔的一切在他的笔下张弛有度、左右逢源、跌宕生姿、风淡云清。“经过这么多年沙漏的过滤,这些字成为一种不灭的材质。”(王安忆语)尽管这是众多文体的集合,但其思想内核、人文精神、斐然文采糅合在质感丰富的文字里,隐形的力量犹如火烧制的陶凸显在最妥帖处,可以实实在在去触摸。
人到中年,经历的东西多了,纷纷汇聚起来沉淀下来,成为不可多得的宽阔阅历。海音是个稍缺小情趣、却有大情怀的人。他的爱好不是太多,平时的业余时间都花在阅读上,善于吸纳各方面如涓涓细流的知识,他是个有准备的人,是正儿八经在为有可能来也有可能不来的机遇蓄势。在现代生活烟波浩渺的大潮里,无论在风风火火的记者岗位奔波,还是在忙忙碌碌的县直、省直单位打拼,海音都能够接触到一般人可遇不可求的海量信息,难能可贵的是,他永远抱着一颗好奇心和责任心去接收、去包容、去思辨,善于用文学的视角,去发现和开掘生活里那些被遮蔽的美和情感。面对碎片化、混沌化的现实生活,他一脸憨笑,从不畏惧不放弃对整体性的把握和接近,凭借越来越广阔的视野和能量来消融和梳理。
海音是资江边长大的孩子,走出家门多年却乡音无改,常常同一件事说三四遍才能勉勉强强让人懂。但他的文字却不含糊,他一直在努力传递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声音,一种张扬着不肯轻易改辙的个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为情感发声,为梦想发声。文字、文体、文集,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就像一张琴,一面手鼓,或一管七孔陶笛,反正就是为发出一种声音,一种金属的声音,一种阳光的声音,一种让人心甘情愿停下来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他的初衷了。他没有说,他的文字也没有这么说,是我读过他的人,读过他的文后,记住的牢靠印象。
一管孤独的陶笛能否吹奏大海的声音?我也不知道,想想都有累的感觉,但我知道的是,他,陶海音,在尽力而为。
你若能够感受他的寂寞,不妨一起来。众多声音合在一起,就可以歌哭,可以海啸,可以荡涤地平线。我想,这也是我为他写这段话的初衷吧。
(《约会布达拉》 陶海音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