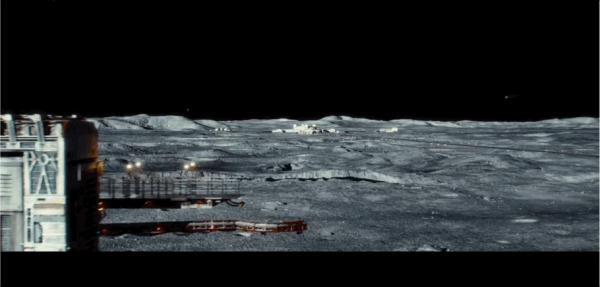“我叫陈熹,26岁,沈阳人。文中说的书店是沈阳市和平局中华路的新华书店古籍店,我当时在东北育才学校念书,那家书店2006年被拆迁,这篇文章是2011年写的”。
近来读到关于东北的文字,颇为感念,此间搜索到这篇,征得作者同意首发于此。
"书店故事"订阅号开办至今,这是一篇让我感慨,让我难过的文字。时代变化,书店变迁,所谓读书,到底还是一个人的精神进阶之路。
沈阳的书店,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回到过去,去看一看。(文中所述书店今已不存,配图来自网络)。
书店故事
一
中华路好像永远是这么热闹,热闹而喧嚣。热闹得叫人心思旁逸,喧嚣的叫人头脑混乱。
这实在不是什么开学校的好地方,可我的初中偏偏就在这条路上,透过西楼教室的窗户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百货。也怪不得当初开学校的人,他开学校的时候一定无法预见未来。学校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当沈阳还叫奉天的时候就这样,当中华路还叫“千代田通”的时候就这样。所以主楼的外壳是历史建筑不能更改或者破坏,所以这里的学生和老师们必须接受这热闹和喧嚣。
路旁林立着巨大的联营公司和密集的小店铺,绍承着前段商业街的余韵。道路狭窄而破碎,所以任何一个周末都可以轻易地创造一场令人窒息的漫长的交通拥堵——这大部分是驾车来接孩子的家长造成的。最令人抓狂的是路边店铺门口伫立的音响,永远不知疲倦地轰炸着整条街路。学校对面有一家老是放《第五元素》那高亢怪异的插曲,而地下通道口的音响则永远循环邓丽君婉转古旧的《雨中的回忆》——对此我非常无语。这些高亢或者婉转的歌交叉汇合,裹挟着呜呀的人声和尖锐的车鸣,笼罩着教室窗外的世界,敲击着窗里眼巴巴的我们。热闹而喧嚣,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六的上午,在我们认真地周练小考或者上课溜号的时候。这真是种复杂的心情。
然而这里曾经有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我升入这初中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这间书店,因为它离学校近。这是片陌生的街区,跟我家或者我的小学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小学门口就从来没堵过车,因为家长都骑车或者步行去接孩子。这是个陌生的学校,我只有一个小学同学,然而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部。上课之余我总感到很别扭,老师和课程我都是这么不熟悉。匆匆结束午饭后就有点无所事事,于是乎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就常常会穿过马路到古籍书店去看看。
穿过学校和联营公司之间狭窄的过道,过马路,右转,正对学校的位置是一排连续的二层小楼。这小楼古旧而突兀,跟周围很不搭调——今天再看起来就显得更加不搭调。这颜色暗淡的安静建筑看上去有点日式风格,没准就是小日本占沈阳的时候留下的,反正稳定有年头了。我一颠一颠地快步向前走,心里开始兴奋和期待。我记不起来是第几间了,我从来就没注意过,因为我从来没预防过以后要回忆它。
我径直走向半开的透明大门,抬头看,就是这块大红的招牌,“新华书店”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下规整地印着小字:“古籍店”。
二
很明显,这家书店的买卖非常不好。
走进门,这是间宽阔低矮的屋子,没有装修,陈设简单,至于显得局促而简陋。四壁靠着大书架,中间有小书架,也有几张堆着书的大方桌。没有例外,屋子里所有都是特价书,半新不旧的大多是对折,而定价几毛几分的旧书干脆用铅笔在书后写着新价格。
大方桌上堆着大量岳麓书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廉价古籍和古典小说,呆板土气的精装外壳,混浊斑驳的劣质用纸,虽然年头很近,一翻开那味道却浓烈得叫人窒息。这些生锈的黄纸内容种类齐全得令人惊讶,从《穆天子传》到《李卫公问对》全都找的到。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则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旧书,七八十年代的,五六十年代的,扉页上印着“内部参考”的,字句圈画批注的。有初版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文革”时代印着语录的鲁迅选集。打开一本,过去时光的味道就在头脑里开始晕染,伴着宁谧的暗黄,心思就开始沉静,开始飘逸。
店员很少,也很清闲,因为顾客总是少得数的过来,连我同学也很少看见——所以我说这里买卖不好。离古籍书店几百步就是新华书店马路湾店,人家那永远有鲜亮的新书和盈门的读者。我刚上初中,我非常奇怪:“新华书店”怎么还能是这么一副模样?
在屋子的尽头,另外有一间小屋,那里有转上二楼的狭窄楼梯。从知道这家书店我来了好几次,可是我从来没想过上二楼,因为我没见过有人上二楼。我猜那里一定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闲人止步”。
直到这一天我发现了二楼的秘密。
深秋的时候作业开始多起来,我也已经融入了新生活。这一天中午我又突然想起古籍书店来,于是快步过马路,右转。一切和以前的那些次没什么两样,还是疏寥的读者,还是古旧的书本。我到各个书架浏览,靠近,慢慢检查上次看到的书是否还在。偶然发现一点新货,也稍稍有点发现的欣喜。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预备回学校。就在放回书而转身的时候,我又瞥见了通向二楼的楼梯。在这一刻,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上去看看,不管那是不是“闲人止步”。我慢慢走过去,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非常狭窄,狭窄而陡峭,仅容一人通过。我慢慢地向上,每一步都发出轻轻的沉闷的美妙的回响。我的心突突地跳,有点紧张有点兴奋。强烈的好奇心使我抬着头,注视着视线里缓缓出现的一切,警觉着随时会有人出现把我撵下去。这楼梯发挥着这房子的风格怪异,显得那么不安,显得那么幽深。那逼仄的通道仿佛完全把热闹而喧嚣的外面隔绝,奇妙地通向另一个世界。
仿佛若有光,二楼的景象在最后一级台阶豁然开朗。这一刻我完全惊呆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种景象。分隔出的这一间小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悄然无声,只听见我的心跳和呼吸。天光从墙上的大窗户径直铺到暗红色的地摊上。四壁都靠着一直通到天花板的高大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我从没见过的奇珍。我愣了一小下缓过神来,开始慢慢分辨书脊上的名字,从黑暗里走入光明的眼睛重新适应世界。窗前立着“中华书局直销部”的牌子,大部分书是中华书局出的。脚步在地板上沉闷地发声,我轻轻抽出一本书,捏着书页打开,天呐,居然是竖排的繁体字。以前我只在旧书摊上见过,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居然还有繁体的古书,这真够新鲜刺激。淡绿色壮观的二十四史,淡黄色惊人的《资治通鉴》,庄严的十三经,恢弘的“诸子集成”,《全唐诗》、《太平广记》以及更多我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一切的目不暇给使我确定,这是个异于课本的世界,这是个我从来没看过的世界。
还有什么比新鲜迥异更能使少年着迷的吗?
这端的是座好洞府。
这屋子里大部分是保存完好的旧书,不过和一楼那些不同,很多看上去好像从来就没有被翻开过,似乎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任时光在字里行间晕染沉淀。正对门通顶的书架上有二十四史和《通鉴》,这两种最吸引我,因为我喜欢历史。面对这些庄重的大部头,我忽然自惭形秽。我开始默数我看过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杨家府演义》,还有,嗯,哦对还有 《英烈传》。我兴奋地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轻轻地把立在旁边的梯子搬过来,慢慢爬上去,在书架最高层捏出《史记》第一册。封面上繁复的淡绿色花纹是那么庄严大方,原来在我熟悉的今天之外,还有一个古代。我的心跳很快,脸开始发热。我慢慢把它翻开,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印刷,那纸张的颜色令人安静,那新奇的感觉令人兴奋。繁体字叫人陌生,陌生却散发着奇异的亲切。我慢慢开始念,我感到脑袋嗡嗡直响,在这无人的小屋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我的自言自语:五帝本纪第一,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然后想象从头脑中淙淙地向外盈溢,神奇开始弥漫在每一个角落。
慌忙赶来防偷的店员气喘吁吁,目送我满脸迷醉地下楼离开。
我在车流中穿过马路,身边的景物开始黯淡,一切的声响褪色。我得怎么才能重新投入到下午的英语课呢?此刻我多想向全世界宣告,今天中午,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三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头,我就成了古籍书店特别是二楼的忠实顾客,也许是最忠实的一个。虽然我没怎么买书。
我融入了中学生活,充实地忙碌,去古籍书店转转成了一种重要的课外活动。初始的新鲜惊讶开始慢慢退去,但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永远涌动着新发现。我知道了除了老庄孙子还有个人叫“抱朴子”,我知道了除了编年体和纪传体还有个体叫“纪事本末体”。我开始买书,便宜的旧书我时常会捡点,比如两块一册的初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碰到有点贵的也会当机立断地拿下,比如一百八十块的《历代纪事本末》。二楼那些令人激动的书大多价格不菲,所以更多时候得找我妈资助。我清楚地记得那套十册的《史记》一百二十五块我攒了好几个月,回家的时候在马路牙子上摔了一跤都没敢把书掉在地上;我记得二十册的《通鉴》三百多块可是店长把那有点破损的一套给我打了八折,她指着一九九五年惊人的印数对我说:“你看他们印得多着急啊,也不知道当时出了什么事。”作为初中生我只是对中国历史故事和古代文学有一点粗浅的兴趣,所以我买了《庄子集释》和《列子集释》,可是对《四书章句集注》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还记得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中国画。有时候书架上的样书太久了,店长阿姨就伸手去推那面墙,那居然是一扇旋转门,而画的背后是一间存书的密室——所以我一直怀疑那以前是小日本的房子。我从这件密室里拿走了《世说新语校笺》和《三国志》。
然后我开始艰难地阅读,适应文言文和繁体字,还有对我来说有点吓人的卷帙。新鲜很吸引少年,可是新鲜没法抵挡难懂的文字和繁浩的卷帙。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因为好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确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奇世界,当然不只因为它是竖排繁体的。这个世界跟我认识的今天完全不同,跟他们讲述的过去也完全不同,它梦幻又真实,典雅和粗放都令人着迷。
除了书,书店里还另有可看。一楼隔壁是卖字帖和文房四宝的,有时候我会买字帖看。虽然我不会写毛笔字,但是黄庭坚的潇洒风骨或者赵孟頫的秀美凝丽任谁都会陶醉。在楼梯旁的空地和二楼,还经常展览着日本东京二玄社的书画复制品。从冯摹《兰亭序》到《清明上河图》,虽然每一幅都是明目张胆的假货,但是在这热闹而喧嚣的都会,它们都是稀世之宝。
中华路依旧车水马龙噪声四溢,但是走进书店,上二楼,一切都被隔绝在外面。这是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觉,这是种令人难忘的温馨记忆。它是书店,它是古籍书店,这就足够了。在盛夏,从窒息的太阳下跨进阴凉的书店,一切的焦躁都消失在那安静里,心灵开始平和,开始向往典雅;在冬天,二楼的窗外是整个白色的城市,呵开冻手,有点麻木的脑袋重新运转,开始阅读过往,开始体味智慧。那楼梯永远狭窄幽深,真正成了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当脚步在楼梯上发出低沉的欢悦,每一声都充满了期待和满足。小屋里往往只有两三个人在,很多时候只有我一个,只有我一个在另一个世界里逸兴遄飞。
我可以感受到世界的变化,可是好像它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屋子里没有过畅销书,好像它永远都会坚持不改变。我带着少有人看的书走出书店时总会有点幼稚的虚荣和自负,但在书店里我必须得谦逊。它局促狭小而永远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它永远也不法效那些高大华丽的书城去迎合时代,或许它所承载的古典注定使它永远庄重平和又朴实无华。
世道茫茫,这真是一种可贵的慰藉。谢天谢地。
所以我说这好像是桃花源,深深藏在这热闹而喧嚣的都会里,却能随时给人心一个诗境。然而我想想这比喻又不太恰当,因为桃花源给人的诗境叫做梦幻和逃避,而这里给人的诗境是高贵和追求。
一个人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都会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
四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一转眼到了初三的夏天,我终于通过考试直升了高中部。这个夏天是令人难忘的,因为大家从来就没这么身心放松过。有时候我还去书店,在里面我会很感慨,因为高中部在市郊,以后就不能老来这了。三年来我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个地方,真要算是天幸。
然而还没等到我们照毕业照,古籍书店居然被赶走了。
虽然买书交款的时候曾经听店长阿姨说起效益不好,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书店会搬走或者停办,在繁华地段在重点中学旁边,这不正是书店应该存在的地方么?所以那个夏天的某个中午,当看到店里贴着因迁走而要清仓甩卖的告示的时候,我实在是大吃一惊。
除了惋惜和不舍,那时候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上了二楼转转,安静依旧,明媚的阳光透过窗照进来。反正它只是搬走,我想,以后还可以去。一楼新添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的《战争与和平》,四册才卖二十块。二十块对于初中生来说还不是很小的数目,但是我买了它,面对这样的机会是不能犹豫的。
这成了我在古籍书店买的最后一套书。
古籍书店没了,听说搬到了怀远门。我没去过那,所以那是个很远的地方。我上了高中,学习很忙,我更加没时间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逛书店。它所在的那栋小楼被掏空了,来了新的店铺。然而我非常不解,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在这个日式风格的历史建筑里,为什么容不下一家古籍书店,却容得下一家全部货物都两元的小商场。
或许怀远门更适合它吧,我想。我希望是那样。等我有了时间,我就还能去那。
不久我听说古籍书店好像又搬到了新华购书中心的四楼。新华购书中心在我每周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我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高兴。某一个周末放学后,我迫不及待地乘着电梯到了四楼,然后看到一块刻着“古籍书店”的木牌。除此之外是文房四宝、打折画册以及一些杂牌仿古线装书。再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家的路上我沉浸在深深的失望里。我以为它只是搬走了,可是古籍书店没了。
我是多么想念它呀。我们家没有一个读书的人,学校里没有几节有意思的课,教给我最初的思想和知识的,只有这么一家小书店。现在,连这么一家小小的书店都被夺走了。
或许我早就该明白,像那样一家小书店,根本就少有人去,只有打折的时候才会顾客盈门,它迟早是要黄的。它对于我曾经很重要,可是我只是它漫长生命里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
我安慰自己,也许那只是我的一种情结。路在变宽,楼房在变高,大批的人口和车辆“魔法般地被从地底唤出”,这城市本来就无法停顿或者保留。连我自己也不停地长大。
其实“古籍”还有,“书店”也还有。古籍在各个大书店都找得到,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正续《通鉴》,而且都出了新版,比以前更精美。可是它们都用纸盒包着或者被锁在玻璃柜子里,不摆在书架上或者好像根本不让人动。书店也不少,越来越漂亮,而且里头还有了咖啡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古典名著”架上挤满了什么朝的那些事儿却容不下几本正经书。那些被幽闭了的古典成了被隔绝的异类,这巨大的厅堂和不息的人潮成了盛大的展览会。
可是古籍书店没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上了大学。假期再从中华路经过,是一种荒诞的怀旧。古旧早就变了样子,这个时代不可能看得见过往。马路湾的东宇书店早就黄了,托经济危机的福,联营公司的对面建起了地铁。学校在建新楼,绿网罩住了操场。西楼的同学们再也不用担心像我们一样被窗外吸引而溜号了,因为挨着窗户长起来隐天蔽日的“富丽华大酒店”,压根什么也看不见了。曾经令写着卷纸的同学们心思飘逸的所谓“外面”,现在只不过是一面高墙而已。
中华路依旧是这样热闹,热闹而喧嚣。热闹得叫人欣慰,喧嚣得叫人迷惑。我回头看看当年熟悉的位置,那古旧的小楼,“两元店”还在那里。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终于没有人再单曲循环《雨中的回忆》了,谢天谢地。现在放的是Justin Bieber 和Katy Perry。
二〇一一年八月作,二十一岁
-END-
许多城市,都有各自的古旧、古籍书店,西安,石家庄,青岛,均有。沈阳,是这个名字击中了我,是这份文字带着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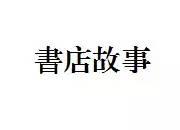
书店·故事·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