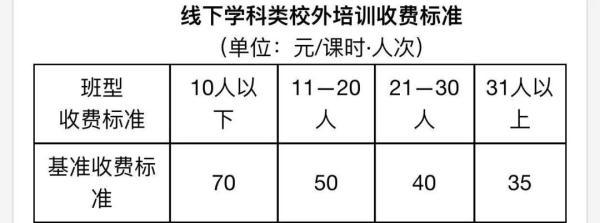很早以前,思南被称为“荒徼之外”,南蛮之地,是土家、苗、仡佬等民族杂居的地方。禹贡时属梁州地域,殷商时又属荆州,春秋初属巴黔中地,后为楚境.三国时为蜀南中地。后来虽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土司制度统治,但中原文化实际上也早已影响到了这片土地.正如《寰宇记》载:“蛮獠杂居、言语各异”。嘉靖《思南府志》载:“在荒徼之外,蛮夷杂居,语言各异。居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有客语,多艰鴃不可晓。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务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皆不同。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
由于历史沿革和地理因素,思南古代文化既有自己文化的特征,又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痕迹,这就使得思南文化的内涵显得十分丰富。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思南文化的不断改进,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更加辉煌灿烂。

在思南,众多的文化艺术形式中,流传至今的最古老而又最具特色的莫过于土家族傩坛戏、打闹山歌、花灯和苗族高台戏了。
傩坛戏 又称傩戏或傩堂戏。
傩,是我国古代驱鬼逐疫的一种仪式。《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意思是说:本乡人举行迎神驱鬼的仪式时,孔子总是穿着朝服站在东面的台阶上。)何晏注:“孔曰:傩,驱逐疫鬼”.《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令人腊月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吕氏春秋·季春》中还记“国人傩,九间磔禳,以毕春气”.高诱注:“命国人傩,索宫中区隅幽暗之处,击鼓大呼,驱逐不祥,如今之正岁逐除是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第二”中对“乡人傩”的情节曾作过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也还有不少诗人对这种情景作过叙述。如唐代孟郊《弦歌行》写道:“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宋代陆游《岁暮》中也写道:“太息儿童痴过我,乡傩虽陋亦争看”.由此可见,傩这种民间艺术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
东汉王逸在他的《楚辞》辑本的《九歌章句·序》中写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思南与沅、湘不至千里,傩的活动也是十分频繁的。明嘉靖《思南府志》:“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客至,击鼓以迎”。清道光《思南府续志》亦载:“祈禳 。各以其事祷神,逮如愿则报之,有以牲醴酬者,有以彩戏酬者。……各时,傩亦间举,皆古方相逐疫遗意。迎春,则扮台阁,演古戏文,沿街巡行,以畅春气”。
至今,思南县内尚有百堂以上的农民傩戏班子。过去,傩戏是被当作封建迷信的东西而否定的。1983年,县内开始民族识别和恢复民族成份工作,同时对思南傩戏进行发掘和搜集。1985年1月10日至15日,铜仁地区第二片区(即印江、石阡、德江、沿河、思南五县)民族民间文艺调演在思南举行,思南县民委组织民族民间艺人演出了思南傩戏部分剧目,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使不少专家、学者看后如痴如醉,把它称之为“中国戏剧活化石”。
1986年6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在贵州东北部边远的思南山区民间,发现了原始面貌保留最完整的傩坛戏,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剧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群居时期。7月上旬,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贵州日服》等均对这一发现作了报道。

1987年11月,贵州省民委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贵州民间滩戏面具展览”,思南县民委带着30多具傩戏面具参加了这次展览会,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参观后说:“奇迹!中国又多了一个奇迹”。
思南傩戏的发展经历傩歌傩舞、傩夹戏和傩戏三个阶段。傩戏中为首的称掌坛师,他既是傩坛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驱鬼酬神的法师,同时又是傩戏表演的主角,其成员有开荒师、接法师、过法师、传牌师、保具师、封牌师等(这些又俗称土老师).
傩戏请神驱鬼法事较多,其中以“冲傩还愿”规模最大,“威力”最强。因此,在群众中有“一傩冲百鬼,一愿了千神”之说。冲傩还愿的程式庞杂,少则一天一夜,多则十天半月。法师们把祭一日者称作“跳神”、祭三日者叫“打太保”、祭五日者谓之“冲大傩”.不管当时怎样的气氛肃穆、一派森严,但因毕竟是戏,即使是在祭祀中也仍然充满着戏剧的娱乐性,可以说是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祭仪完毕之后,才是正式表演.
戏分正戏和外戏两大类。正戏是“还愿”仪式中戴着面具表演的二十四个戏,这些戏全由装扮之鬼神在起伏变化的锣鼓声中作哑剧式表演,除了彼此声名表姓与冥冥祭语之外,大多没有道白和对话。傩戏外戏则不同,它是不戴面具且在舞台上表演的戏,是在正戏表演结束后才演出的,祭的成份很小甚至没有,而故事性、戏剧性和娱乐性则增强了,与近代传统戏有了很大的相似之处。
另外,傩戏中还有最令人叫绝的一招,那就是傩技,也就是法术表演,如踩刀、溜铧、翻叉、悬碗、钉牛角、隐身、接舍身刀、过天桥、下油锅等.这些只有技艺十分高超的艺人才能表演。
踩刀 分“踩地刀”和“踩天刀”两种.“踩地刀”,是将十二把装在刀竿上的大刀,刀刃朝上放于地面。而刀刃一定要锋利。表演时,土老师神情庄重严肃,不
苟言笑,打着赤脚,从刀刃上一步一步地踩过去。“踩天刀”则要把十二把或二十四把、三十六把锋利的大刀,刀刃朝上装于刀竿上,再将刀竿竖起,于下置一磨盘,象征八卦之神案,上摆供品。土老师身着法衣,手执牛角,一边划讳念咒,一边打着赤脚踩着刀刃沿级而上,至顶端后又迎刃而下,有多少把刀就要上多少次,最后,在顶端鸣角三声。此时,早已准备好的刀斧手,迅速将刀竿砍断,土老师面不改色迅速撑开随身携带的雨伞,在一片激越的锣鼓声中,轻松自如地降回地面。
溜铧 又叫杀铧。事先将犁田用的铁铧用炭火烧得通红,土老师念完咒语后,用手、脚去摸、踩烧红的铁铧。表演中,土老师向烧红的铁铧喷上烈性酒或桐油,通红的铁铧顿时燃起几尺高的火苗,土老师赤手端着正在燃烧的铁铧向四周冲杀,嘴里发出尖厉的吼叫声,其气氛既紧张、热烈,又惊险、恐怖。
翻叉 是傩坛正戏表演中比“上刀梯”、“溜铧”更惊险的一种法事。表演时,其中一位土老师用十二把钢叉向另一位土老师迅猛地投刺,或对准喉头,或对准胸口、脑门、胯下,对方则只能用单手一一将钢叉准确地接在手中,稍有不慎,就会有丧命的危险。不过,这种法事现在是很少表演的。
以上这些法事,在思南傩坛戏里的土老师中能表演的则不乏其人.
1992年初夏的一天,思南县六井一家土家小院里,傩坛神案,庄重肃穆,前置竹扎彩楼牌坊,“三宝殿”内设案桌,神案前竖着刀梯,上面横插着36把锋利的大刀,折光闪闪,寒气逼人。一阵爆竹和牛角声之后,傩戏艺人刘盛扬,打着光脚,一步一刃向上攀登。三十六把刀梯上完后,人们在惊讶之中,突然发现刘盛扬不见了。此时,一位手持牛角、身背挂包的老者从室内走出来,捋了捋胡子,“哈哈”笑了起来,这就是刘盛扬的父亲刘凡昌老艺人,“我把他(指刘盛扬)使了隐身法,你们怎么会看得到他呢?”说着将手中的牛角向墙壁扔去,牛角的一头便稳稳地巴在光光的墙壁上,随后他又将身上的挂包挂在牛角上,顺手又用竖插在米斗里的秤杆提着盛满大米的升子信步走向围观者,而待把米倒光后,才发现提着米升子的只是一把光杆杆的木杆秤.接着,刘盛扬父子还向观众表演了“悬空吊碗”、“油锅捞钱”等绝技。这些连当地观众百看不厌的“绝活”,使在场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小城镇”赴思南拍摄组的杜宪一行数人目瞪口呆,暗暗叫绝。

几年来,思南傩戏艺人不仅赴北京、广州、深圳等地演出,还接待了美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友人十多起,并为他们作了精彩的表演。1996年5月22日,中央电视台1抬“中华文明之光”摄制组王一岩一行还专程到思南来拍摄思南傩坛戏。
1996年,贵州将在全省范围内开辟7条文化带,其中就有“贵阳—铜仁—梵净山—思南—德江”的民族民间文化、傩坛戏、上刀梯等为主的文化带。随着这条文化带的建设,思南傩坛戏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思南傩坛戏也必将大放异彩。
打闹山歌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薅草锣鼓(亦名薅草山歌)。它是农民在集众锄草时为热烈劳动气氛、降低疲劳程度、提高劳动效率、配合劳动节奏所应用的一种演唱艺术形式。演唱时以锣鼓伴奏,表演者一般是二人相伴,一人击鼓,一人敲锣,随着薅草队伍边唱边走,有时站在队前,有时走到队后,有时是哪里落后就追到哪里。边敲边唱,即兴发挥,时领时合,十分有趣动人。薅草山歌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集地方山歌之大成。从清晨到日落,各个时辰都有相应的唱腔曲牌。因此,长期以来,在群众中有“九板十三腔”之说。如清晨有《清晨号》、出工有《出工号》、《上田号》、中午有《凉风号》、休息有《茶号》、收工有《收工号》,还有即兴发挥、内容广泛的《花花号》,还有若干变奏唱法,且曲调十分优美。休息的时候,通常还要对歌.对唱之前要加上类似绕口令的“说口号(亦称说白、聊白)。如:哎!锣鼓一到,口号来了。鼓得双脚跳,歇下锣鼓说口号.口号口号,随口就到;口才口才,随口就来。若还不来,不成口才;若还不到,不成口号.干狗屎,隔墙撂;干豆腐,上推刨;牛尾巴,顶枪炮;马尾巴,戴铁帽。老子打儿子双脚跳,儿子打老子,现有现报;火烧竹子拦腰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或不报,时候未到。管他三八二十四个工程,齐不齐,到不到,二位歌郎,我们打个(接唱)“齐头号”。
薅草山歌的伴奏十分独特,虽然只用一锣一鼓,但由于节奏多变,强弱得兼,使人毫无单调之感。尤其是一些老歌手,敲击技术高超,时而重击,时而轻击,时而闷击,时而放击。在演唱《快号》一类情绪热烈的曲调时,鼓点由慢到快,最后密如连珠,加上锣声相伴和众人“哦火、哦火”的欢呼声,漫山遍野,彼伏此起,将众人薅草的劳动情绪推向高潮,其气氛之热烈,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
思南,除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而外,在经、政、文、史方面的创作、著作也是较早较多的。元代,思南人陈致虚就编著了《金丹正理大全》;明代以后,著作较多的就有理学家、嘉靖云南左参政李渭,各种著作近30卷;还有明弘治中宪大夫安康,明思南首中进士、广东布政使田秋,进士肖重望等.清代著作较多的有陈葆光,其作品有《孔子世家》、《六经注解集》、《说文通例》等部,还有肖琯、程棫林等。
思南,在明嘉靖间就编纂了第一部《思南府志》,万历间又重修了《思南府志》,清康熙、雍正、道光都编修了《思南府续志》。民国时期,思南何淮分别在重庆《新政治》月刊和南京政治大学季刊陆续发表了《管子政治思想述评》、《管子法制思想》、《中国古代学派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导论》、《诗经时代的社会与政治》、《老子的政治思想》、《韩非子的政治思想》等论著。
解放以后,思南的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不仅有电影院、书店、图书馆、文化馆,还有剧团、报纸、广播、电视等等。县文联下面分别有文学艺术、戏剧曲艺、新闻、美术摄影、音乐舞蹈等各种协会。县报向全国公开发行,电视覆盖率达到70%以上,业余文艺创作队伍近200人,有近20人分别加入国家及省各种艺术协会,每年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获奖)作品达30多件,在省级刊物发表、演出作品达100多件,获奖达20多件,在地级刊物发表(演出)作品达200件,获奖达30多件.特别是文学创作,基本形成一个“思南乌江文学”创作群。1984年以来,县直各部门共编纂了近60部部门专志;199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姚敦睦主编)的思南解放后编纂的第一部新志《思南县志》还获得全国修志成果三等奖。第二部县志《思南县续志》又在编纂之中.思南县民委编辑出版了《思南苗族高台戏》、《思南傩堂戏》,县文化局编辑出版了《思南傩堂戏概观》,原文管所所长汪育江编写、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号军起义》,曾令华编写、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了《白号军起义故事集—巍巍荆竹园》;有关单位还编印了各种业务书籍数十种。

文化,是一个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象征,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效应。思南的知识分子是刻苦的,思南的文艺工作者是勤奋的。他们不仅曾经为思南人民赢得了荣誉,而且还在继续用心血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谱写更新更美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