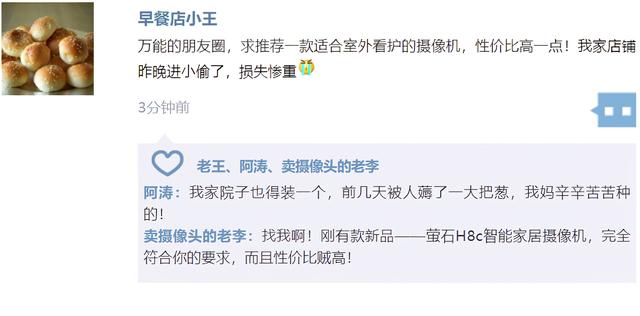低处的飞——读青年诗人张二棍诗集《旷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什么飞得低?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什么飞得低
低处的飞
——读青年诗人张二棍诗集《旷野》
钻探和写诗无论从“神”和“形”上都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钻探是一种深度挖掘,是寂寞的期待,是企图发现,是从大地上萃取,有寻找的枯燥和获得的快慰。写诗依然,写诗也是一种探索,一种孤独的体验,一种沉淀的汲取。所不同的是,钻探指向大地,写诗指向灵魂。
张二棍是一名钻探工,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其实,这两种身份是可以模糊的,是可以不加区分的,是可以相互贯彻的,是能够合为一体的。因为诗人张二棍用诗歌将两者密切地无缝隙地糅合在了一起。是的,我们的灵魂只有安放在大地之上,和大地融为一体,才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才是可以永远直立的。
诗集《旷野》是诗人张二棍在野外作业之余的内心独白,是交给大地的第二份作业。他独特而独立的生命和情感体验,表现了一个地质人,一个钻探工,对自身的深度探寻,一些新鲜的思想和个性的表达,丰富了我们诗歌阅读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和层面领悟了地质人的生活。
“束手无策”
苦难是诗人张二棍诗歌的底色,同时也反映了诗人成长的经历。苦难与死亡的相互交织,一度成为诗人反复咀嚼的话题,成为诗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噩梦。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苦难时刻存在,时刻被提醒,时刻在进行。那些苦难的记录不仅仅让诗人刻骨铭心,也让我们读之动容,读之心碎:
那夜,姐姐早早就躺下了
她用手轻轻地掖住被角,抽泣
而灯下,母亲做着针线活
她要为我短于现实的衣衫
续上,瘦长的灰布条。还要
等到姐姐睡着,在她的枕头下
掖进几角钱
———— 《 春天,姐姐失手打碎了心爱的小镜子》
仅仅是打碎了一面小镜子,就让姐姐那么伤心,可是对于一个爱美的女孩来说,小镜子又是多么奢侈啊,因为,这个家庭,除了能够通过它来照见自己青春秀美的脸庞,把自己的容颜稍稍拾掇一下,就再也没有可以用来照见自己脸庞的物品了。物质的高度贫乏,令姐姐对生活的祈求降到了最低点,一个镜子碎了,就好像生活碎了。然而,对于整个家庭来说,这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父亲疯子般吼叫,向天空
甩着破褂子。我学着他的样子
挥舞着一小片褂子,我学着他的
慌乱,愤怒,和破嗓子
蝗军过境后,土地如末日
一片杯盘狼藉的荒凉
父亲坐在田埂上,一言不发
他混身沾满了禾木的碎屑
和蝗虫的残肢
————《那年蝗灾》
屋漏偏逢连夜雨。缺衣少食之时恰又碰上蝗虫闹灾的年景,“父亲疯子般的吼叫”定格在了诗人年少的心中,多年之后,成为张二棍的诗歌图景。此刻,姐姐打碎了镜子的悲戚也打碎诗人的心,完全无法捡起,无法拼接完整。对于张二棍来说,生活完全就是碎的,人心在某一刻已然扭曲,现实的残酷完全让人束手无策:
你肯定理解什么叫束手无策
但是你,可能不会理解
一个束手无策的人
你也不会理解他
茫然,无助的样子
他蹲在街角
一遍遍揉着头发,和脸
像揉着一张无辜的报纸
······
母亲病了多久,也躺了多久
他却没有一点办法
他卖水果,刚收了假币
又得交罚款
他只有呆呆地,蹲在那里
没有一点办法
————《束手无策》
一个进城卖水果的农民,何时才能筹到给母亲看病的钱呢?沉重的生活,尴尬窘迫的生存境遇让许多普通人束手无策,也让张二棍束手无策。有时候面对命运的不公,我们完全没有抵御和化解的能力,只有束手无策,只有坐以待毙。或者,束手无策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命运,一种习以为常的对策。张二棍的诗歌是疼痛的呐喊和呻吟,是一面烛照当下底层社会的镜子。显然,这本身也是一种束手无策。
“ 我根本就不愿意出生”
苦难有时候会让死亡变轻,会让死亡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谈论死亡似乎有些遥远,有些不真实,然而对于张二棍来说,苦难有时候正是一种濒临死亡的人生体验。张二棍的诗歌始终贯穿着一种不经意的死亡意识,我想,这必然与他沉重的少年记忆和特定的生活阅历有关。
虽然死亡在诗集中占据了相当比重,甚至成为张二棍诗歌的一个母题,但我相信,这绝不是诗人刻意为之,因为对于诗人来说,描述死亡就和描述自己的村庄一样自然,一样坦然。在张二棍的成长过程中,死亡曾经非常朴素地围绕和介入诗人的生活,因此,诗人对于死亡有着超脱于常人的理解和认知。对于诗人来说,死亡是平常的,日常的,庸常的,死亡不是一样可怕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生死就像是日出日落,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因此,在沉重生活的压迫之下,诗人甚至认真地说:“ 我根本就不愿意出生”:
就不想在这油锅般的世界里
分一杯残羹。也不想通过
眼神,辨别同情或厌恶。是的
托谁的福,我活着。并且
愈活愈有缺陷,愈活
愈有敌意
······
我可能就是那个有缺陷的人
我可能就是他们想要干掉的人
我越活,越心里有鬼。如果现在
哪个阎王说该死······我眼睛都不眨
——来吧,我根本就不愿意出生
————《我根本就不愿意出生》
这首诗,像是诗人的告白,又像是诗人的宣言,诗人用“我根本就不愿意出生”来抵抗“生的逼仄”,从而获得“死的辽阔”。在生的面前,诗人是“软弱”的;在死的面前,诗人是“强大”的。但“我根本就不愿意出生”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束手无策”,是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逃避,是一种自我否定。而他的更多的父老乡亲们,正是在“束手无策”中平静地走向死亡:
这次,挺不过去的人,是得了胃癌的
栓寿叔。他躺在土炕上,打滚
把嘴唇都咬破了
死了,总算不咬了。嘴张得老大
连一枚薄薄得口含钱,都咬不住
————《咬牙》
栓寿叔终于还是没有把寿栓住,在”把后年的收成造光了”之后,只有“咬牙”,忍着生命最后的感知——疼痛,走向死亡。
此时,疾病和贫困让死亡变得渺小和容易。诗人直接描述死亡的诗歌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讯号,一种潜在的意识,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更是随机的。有写他人的,也有写自己的。他的《徒留衣冠冢》、《守陵人》、《一个老人死了》、《总得有什么,让我们跪下来》、《我应该怎样死》、《大人之殇》等诗歌,都有着直面死亡的豁达或“辽阔”。
如果要进一步解读诗人的生活背景的话,或许对于其对死亡题旨的“青睐”并不奇怪。在一个相对闭塞的村庄,一个人的死亡往往是全村的事情,每一户家庭或多或少的都会参与其间,死亡有时成为村庄一次隆重的集会。而且,亡者往往就葬在自家的地里,或者就在离家不远处的家族墓地。生和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死亡在年少的张二棍的心中并无畏惧。往日的日常经验,成为了今天诗人对许多事物的终极描述。
“野外,我来了”
很显然,这是张二棍入职钻工不久发自内心的呼喊,从这呼喊声中,我读到了诗人拥抱大自然的快乐,以及对新生活的憧憬:
我不是猎者。可是野外,我来了
腾然升起的鹰,把天空拉得无限接近阳光
而我眼睛里长出的羽翼,那般温暖的,拍打着春天
我不是看客。可是野外,我来了
······
我带着帐篷,火种,以及爱
有一天,我只带走石头
石头里盛开的远古花朵
以及,记录我和你在一起的那些日记
————《野外,我来了》
这首诗直抒胸臆,几乎不用解读,也能够读出诗人内心的悸动。对自己的生活,他有了全新的想象,他有了足够的热情。他身处旷野,沉浸在与天地和山野的热切拥抱之中,他说:而一瓣落英再柔软的下坠/也足够/砸疼一个勘探者关于美丽的回忆。
从这一主题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地质生活虽然辛苦,但并不无聊,相反,它第一次以粗砺之风雕刻着诗人细腻而宽广的内心世界。工作中的见闻,走过的山野,小小的昆虫,都激起诗人的无限诗绪:
在群山之颠
我们是一块石头的儿子
抚摸着古朴的裂纹
是一朵野花的父亲
亲近瘦弱的笑容
要时而坚硬,时而柔软
要做一只蜜蜂的情人
有着一触即伤的甜蜜
————《在山颠》
在山颠,诗人已经是石头的一部分,是“野花的父亲”。诗人对于大自然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他把自然风物视同己出,即使被一只蜜蜂蛰伤,那也是“甜蜜”的。可见,诗人对于自然万物有着无限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另外,诗人的职业和大地有着高度的融合性,而诗人的内心又高度自觉地和大地交汇在一起。对于诗人,这是幸运的,对于大地,这何尝不是一种慰藉——大地遇知音。
关于地质生活,诗人还写下了《露水是秋蛉共同的爱人》、《写给钻探的兄弟们》、《向外高处》、《在灵丘》、《尧峪》、《看鸟》等诗歌,他写道:我散落在山野间的兄弟啊/拥有野花的姓氏/并以来自地心的石头/命名一场经年的约会/我的兄弟/在机台上探求真相的兄弟/你们爬在钻塔上的时候/或者更高。诗人显然对于自己从事的钻探工作有着职业的崇高感自豪感,对于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着兄弟般的感情。他认为,当钻探工冒着危险爬上钻塔的时候,他的形象是高大的,“高于高耸”。
正如诗人所说,钻探是寻求大地内部的真相,那么,诗人又在用诗歌告诉世界属于钻探工内心和生活的真相。
低处的飞
张二棍的诗歌,让我再一次看到了生活的力量。没有诗人的钻探生活,没有诗人苦难的少年生活经历,没有跋山涉水,和大地紧密的拥抱,就没有作为诗人的张二棍。而往往,生活在低处。
张二棍的诗歌正是一次低处的盘旋,是一次贴近地面的飞翔。他不需要飞的多高,只有这样,他才能看清楚满山的野花;只有这样,他才能闻到泥土的芬芬;只有这样,他才能触摸到生命的疼痛。尽管诗人向往高处:
我永远低于一只鹰和另一座山峰
所以,我必须把所有的话都藏在足音里
来和你们,我走远的前辈,来一次长谈
不带水,不带爱人,不带马匹和盐
一把锤,足够了
有花香,引领着路
就有蝴蝶追逐着地质人
·······
向往高处,是因为无人来过
向往高处,就要用一把锤的铁质
沾染另一些元素的色泽
并目睹一场金属般恒久的爱
————《向往高处》
从一座村庄出发,从自己困苦的乡亲出发,从自己清贫的家出发,从一个钻探工的内心出发,诗歌才是有源之水,诗魂才是有根之木。诗人的低处,是向往高处的低处;诗人的高处,是企望用双脚丈量山峰的高处。张二棍的诗是有着无限“旷野”作依偎的灵魂皈依。
诗集《旷野》是诗人入选31届青春诗会,由《诗刊》编辑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我不能说收入诗集的每一首诗都堪称优秀,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本每一首诗都十分优秀的诗集。诗歌更大程度上是遣情和记录,是一种忠实于内心的不诗不快的表达。对于诗人而言,抒写出这些真性情的诗,已经足够了。
2016-4-7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