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洱
【开篇语】2019年8月16日,作家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成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作品之一。《应物兄》首发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展现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精神轨迹,持续引发着文学评论家的讨论。
文 | 李彦姝
《应物兄》的庞大体量以及氤氲气质,从一些批评文章的题目中可略知一二。阎晶明用“塔楼小说”比喻《应物兄》结构之错综及故事情节之“不通透”。邵部以“沙”之喻道出了小说的弥散性和细碎性特征。王鸿生、项静、丛治辰等均以并列式关键词为题折射小说的多维度性。上述种种皆可作为《应物兄》文本繁复性与混沌感的佐证。“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枝蔓杂生、前因后果难以梳理、故事主线便漫漶不清”等几乎成为批评家们的共识。
线头众多、玄机频现的《应物兄》如何使得一种论题专一的批评成为可能?我以为关键是要拨开云雾,找到小说的“题眼”,即找到纷纭世事、人事、物事背后李洱所持的一种总体性观念及其核心且迫切的问题意识。当被记者问到“应物兄身上寄托了您怎样的理想和期待?”李洱回答:“知、言、行,三者的统一,是我的一个期许。”我以为这一回答正扣住了《应物兄》的题眼。应物兄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寄托在他身上的理想和期待,也是作者赋予这部小说的总体性理想和期待。如果再凝练一点,那么小说题眼只有一“言”字——人物的知、思、行皆与言紧紧缠绕,以相合或相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将《应物兄》看作一部以人物声音为主线的“说话体”小说也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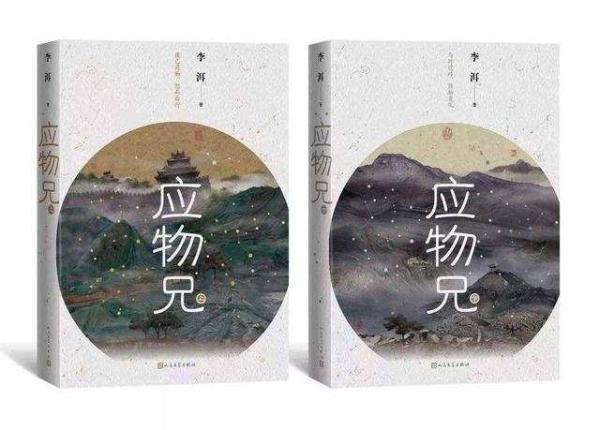
“口力劳动者”的嘈嘈切切
“言”的问题缠绕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鲁迅一向关注国民的发声问题。1926年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提出“在沉默中爆发还是灭亡”的命题;次年他在香港青年会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呼吁国民告别麻木不仁的失语症。数十年后,王小波撰文《沉默的大多数》,他所谓的“沉默”与鲁迅所痛心疾首的“无声”内涵迥异——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格趣味,表达了基于对话语世界真实性的怀疑的不合作姿态,成为对抗权力、诳语、虚伪、浮夸的隐蔽手段。鲁迅与王小波对于“言”的看法其实并不相悖,两者代表了言说之正义性的最高标准与最低标准——大胆讲真话与不说违心话。
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言说域、话语场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应物兄》固然是虚构文本,但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揭示不可谓不深入、不真诚、不辛辣。小说不是以环环相扣的情节敷衍或主人公跌宕的命运起伏演变来抵达终点的,人物叨叨扰扰的言说才是推动小说前行的主要动力。小说是围绕儒学相关话题展开的,孔子最反对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而小说中信奉孔子的各色人物大多能言善辩、辞令丰赡。人物的言说水系杂错,汇溪流以成江海,其所覆盖知识容量之庞大是一大看点。
《应物兄》呈现了太平世中的嘈嘈切切,很多人已经成为管不住嘴、憋不住话的“口力劳动者”,张嘴即来,天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管对信得过的人,还是对信不过的人。当然,公开说还是私下说,说什么怎么说,处处透露着玄机和技巧。
小说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违心话听上去言之凿凿、义正词严;而肺腑之言则低切逡巡,欲言又止,即便大声道出也常因逆耳而为人反感或不屑。拿应物兄来说,他的明言与暗思严重冲突。私域范围内第一人称的自言与腹语往往合其所想,而只要在公共领域发声,真实性就大打折扣,真话往往到了嘴边又咽到肚子里,或说出来只有自己能听到而不肯被别人听到半句,于是“他听见自己说”“他都不敢相信是自己说出来的”这种暗示身心分裂的表述多次出现。比如开篇应物兄谈到济州雾霾严重的问题时,他感到嗓子发疼,鼻腔发痒,但他却听见自己说:“《诗经》里有一句话,叫’终风且霾’,说的就是又刮风又有雾霾,所以雾霾古以有之,不可大惊小怪。”这便是博学之人的狡黠之处——躲进书本,以知识为挡箭牌绕开问题、粉饰现实。
在对雾霾进行了貌似深刻的知识考古之后,他暗自心虚:“听众不会骂我吧?”可见,心之所属的他是一个被现实经验所笼罩的、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生命体,然而从他口中冒出的语辞却属于另一套貌似完整自洽但又不免虚妄乏力的体系。谎言试图缝补自身,这是就目的而言;结果却是背叛、阉割自身。应物兄言不由衷所折射出的立场游移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症候,如同辩论比赛中的辩手“通过抽签来确定自己的文化立场”,他们对于某件事情、某个观点的认知常无“定论”,言说全由一时所处之位置决定。
小说中能言之人大多善跑“马拉松”,寥寥几语便可阐明的事偏要捻细拉长,于是就衍生一系列闲话、空话、废话、没话找话、绕圈说的话……“口语扩容”经有多种途径,比如“掉书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比如“打官腔”,冠冕堂皇,模棱两可;比如“讲段子”,灰黑冷荤,俏皮轻佻;比如“扯线头”,越扯越远,结果离题千里。
小说是在一系列无厘头的的闲话废话中开篇的——由两条狗斗殴所引发的来自狗主人代理人的争执是掉书袋和打官腔的结合,充满闹剧意味。双方以外交谈判的辞令将狗咬狗赔偿事宜的处理复杂化,直至事端难以收场。双方搬出孔子的修身、克己、德怨、忠恕之说,将一场宠物纠纷的裁量权交给了居于庙堂之上的儒学,这个“狗咬狗”的开端,为整部小说奠定了狗血的基调,也为儒学的出场蒙上狗血的色彩。
在《应物兄》所提供的数对人物关系中,很多人滔滔不绝的讲述只图逞口舌之快,罔顾听者感受,话语行为的主客体之间无有效交流,交往理性并没有在频繁的言语接招中诞生。在华丽辞章中空转的对话是一种隔心隔情的虚假交流,人与人相互理解的河道始终是干涸的。
问题不仅出在言说者那里,也出在倾听者身上。对于僵化、被动的听者而言,言说者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而他是谁、在哪说才是要紧的。
言说、知识、反讽在雾中裸露其自身
沉默不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性,言说本身也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物之言不及心、不及义、不及思、不及行。以冗长臃肿、浮夸饶舌的言说串联成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闹剧色彩。闹剧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无关反思,也无关破坏,它取消意义。它是铅笔描在像披上的卡通画,橡皮还没有用完,它就已经消失。”那些饶舌之人的言辞貌似酣畅淋漓,可是其人本身却索然无味。嘈杂喧哗、逻辑混乱、没头没尾的人物声音制造了表面密实、内里疲软的话语废墟。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李洱在《花腔》中用过这句话,悖论中带来简洁而深刻的启示,有心人可以读出一种严肃的含义。这种含义在《应物兄》中亦有鲜明的呈现,那些性情高洁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时刻少言寡语,人格的挺立是以大音希声或有一说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其中的朴实无华、高贵真诚是抵制噪音及弥漫其中的虚无的武器,而更可贵的是这种“声音的稀缺”并非出于自私、怯懦、逃避、“甩锅”,也并非出自假意的清高;而恰恰相反,是出于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道德坚守以及拒绝随波逐流的自觉姿态。
在双林与张子房下一代人中,也有默默无闻又性情高洁的知识分子,比如早逝的文德能。文德能生前留有大量笔记,但是对于还没有考虑成熟的问题从不公开发表文章,因为“他总觉得那些知识还没有被内化为自己的经验,所以无法举笔成文”。这句话尤为重要,体现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理想,这理想纯粹而又沉重,直至生命终结都没能实现。文德能身上闪耀着自我守持之美。
学术圈所谓的“成功学”秘籍是个人才华需要进行外在包装与公开宣扬,高音量、高密度的言说才是成功捷径。若一味汲取知识而不知卖弄,若治学只求向内悦己而不求向外渡人,那么学问就失去了其工具性,而知识的持有者也极可能泯然于众人。芸娘是小说中少数被褒扬的女性,她的魅力全在“静气”与“求真”中显现:“芸娘可不是一个喜欢说闲话的人,她的每句话都会给人以启迪。也就是说,’说闲话’三个字,跟芸娘压根儿都挨不上边。”程家大院是小说的承重墙——这也是一个诚念聚集之地,在它被意外发现的那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小说情感骨架立住了,五味杂陈,悲从中来,从而使这个以人物声音为主要动力的文本最终没有凝滞于口舌之快。
《应物兄》中虽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但没有核心人物或曰焦点人物。应物兄也只是叙事视角的提供者,是诸事件起承转合及串联众人言说的一根绳索。批评界对于《应物兄》的主要质疑是文本的臃肿和情节的涣散。我常常也揣测,小说如果删繁就简、化言说为情节——摒弃人物口中长篇累牍的闲言碎语尤其是晦涩的知识话语,是不是有可能积淀更为密实的情感压舱,呈现出更节制的叙述控制力和更强烈的艺术感召力?
但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剪除“言说”的枝蔓与各类知识话语,那么这部小说所蕴含的关于“言、知、思、行”关系的核心问题意识以及尖锐的反思批判可能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噪声与静谧、泛滥与匮乏、反讽与深情、卑琐与高尚为了显露自身与反衬对方,不得不纠缠在同一文本中——症候大面积爆发,才更凸显疾患之痛切,疗救之必要,也才更衬那些健康高洁灵魂之可贵。言说、知识、反讽在雾中裸露其自身,这部小说要想成为它自己,必得先树立迷障,继而穿透迷障,于是它也便只能保持现在所是的这副样子了。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 封面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