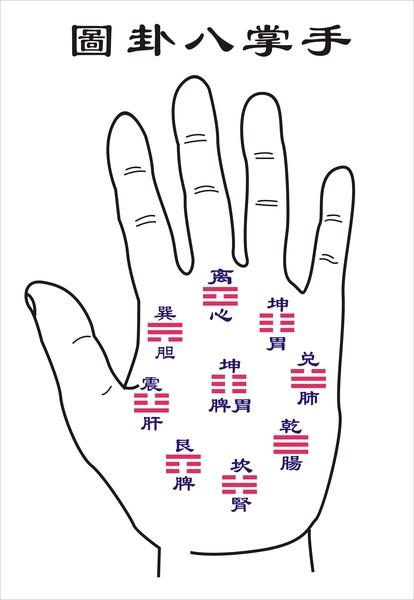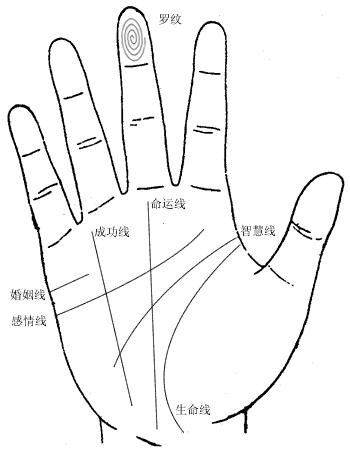文/王淼
在人类文化史上,排泄物——粪便,一直是一个颇遭忌讳的话题。尽管排泄物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更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管你是否情愿,粪便中的部分细菌都会通过某种渠道重新进入你的身体,化为益生菌拱卫你的肠道,而粪便本身也是被人类和诸多动物广为利用的养分资源。但是,粪便是为人类的“眼中之脏,鼻嗅之臭,口中之秽,所排之污”,并因其臭不可闻的属性而被人类视为忌讳之物,令他们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英国昆虫学家兼博物学家理查德·琼斯的新著《自然的召唤:粪便的秘密》是一部关于粪便的专著,书中的主角自然是粪便,而主角中的主角,则是“粪客”。其中包括粪甲、粪蝇等等诸如此类的以粪便为生的粪食者、腐食者、捕食者、寄生者……

《自然的召唤:粪便的秘密》
作者不仅在书中解答了粪便产生之后发生了什么,粪便去了哪里,它们最终如何消失;同时也探讨了粪便之于环境的意义,粪便的实用价值,粪便的循环再利用,以及围绕粪便所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网络:一抔粪便新鲜落地,众多粪客争分夺秒,为了获取“粪量有限”的资源而展开竞争。正是借助它们的竞争,粪便化为沃土,然后作物丰收,牧草生长,从而开启了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
诚如琼斯所说的那样,生态环境就像一个互联所有鲜活之物的复杂网络。每当粪便初现,无数粪甲、蝇虫接踵而至,呈现出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拉开了生态系统运作的大幕。而粪便即承载着一系列的生态启示,观察其中的个体如何依存、如何共生,既代表着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象征着一种面对排斥话题时所持的开放心态,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对这个星球上生物之多样、物事之庞杂的景象产生敬畏之心。
正所谓“一粒沙中看出一个世界”:“一摊粪便虽量少体微,孤形单影,但通过观察那些粪甲、粪蝇及其他来来回回对粪便加以循环再利用的动物,我们便至少迈出了认识全局的第一步。”
“粪本无主,先到先得”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古埃及人崇拜的对象是蜣螂,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屎壳郎”。古埃及人崇拜蜣螂,是因为蜣螂总是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制作粪球,然后不遗余力地推滚着粪球,在大地上负重前行。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蜣螂是智慧和执着的化身,而在蜣螂弱小却又执着的身影背后,有着灼热的阳光和辽阔的土地。正是太阳和土地,构建了农耕社会的广阔背景。显而易见,古埃及人并不在乎蜣螂嗜腥逐臭的生活习性,他们更为看重的是蜣螂对环境友好的循环再利用的行为。
的确,大自然是从来不会暴殄天物的,即便是万物生灵排泄的代谢废物也从不会轻易被浪费。首先,土地自身就不是被动的中性介质,而是一个动态的生物系统,其中生活着大量的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它们不停地降解枯叶、干枝、动物尸体和排泄物,化解有机物质并加以重复利用。
蜣螂及其他粪甲、粪蝇之类的昆虫,其实都是其中的无脊椎动物的一员。它们在这个动态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它们将粪便降解,使之重新被吸收到土地之中,既疏松了土质,又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为作物的生长提供了一片沃土。对于粪食者而言,粪便是一种赖以为生的资源,但在数量上却决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需要它们奋力争夺,抢占先机。
所谓“粪本无主,先到先得”,在争抢方面,它们的确极尽所能、各显神通,它们或者推粪而行,或者在粪便中安家,或者在粪便下掘洞生活,或者略施小计、鸠占鹊巢……为取得优势的生态位,它们甚至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配备”了强大的武器:结实的体形,强壮的铲足,折扇般的触角锤节,乃至脊、隆、瘤、棘、刺、单角、叉齿……应有尽有,一应俱全,称得上披坚执锐,武装到了牙齿,外表就像装备齐全的士兵一样神气。
毫无疑问,敢于冒险,积极主动,是所有粪食者获得粪便的不二法门。力大者,固然以力量取胜,力小者,也不妨另辟蹊径,比如,尾蜣螂属和姬足蜣螂属,它们的策略是悬附在树懒肛门附近的毛发上,静等寄主排便,既无须费力寻找,更不用参与抢夺,只要守株待兔,便可坐享其成。
总而言之,不管采取怎样的策略和方式,每一个粪食者都要与其他角逐者竞争有限的资源,不惜自相残杀,不惜付出生命,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脱颖而出,在生命的进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天竞物择的胜出者。
换位思考,理解粪客如同世间所有的事物一样,粪便因物种而异,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而且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生命周期,这就是琼斯所说的“时过粪衰”。既然促使粪便再循环的主体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生物群落,那么,粪便就会随着这一群落的节奏发生变化,而这一切又必然会受到季节不同和天气差异的影响。
琼斯将粪便的生命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新鲜期:新鲜出炉,静待粪客;成熟期:第一拨粪客嗅臭而来,蓄势待发;饱和期:你争我抢,各显其能;霉变期:粪客减少,粪便变干;腐朽期:逐渐风化,边缘萎缩……另外,一抔粪便还会经过解体期、残余期、碎渣期、存迹期和偶闪期,直至融入土地,完全消失。
针对于粪客而言,它们之于粪便的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任务,从新鲜期和成熟期的迅速出手,到饱和期的相互排斥、争抢地盘,直至霉变期和腐朽期的逐渐离开,繁殖的目的已经达成。而粪便的主要成分细菌,或已被取食,或进入休眠的芽孢模式,等待开启新的轮回,可以说其中的每一个粪客,都是维持自然运转的一分子。
粪客担负起与恶臭打交道的重任,其间无论是粪蝇的“做作”,还是蜣螂的“逞强”,其实都是它们自然的天性使然。然而,尽管人类从粪客的劳作中获得了不少好处,但他们总是对粪客的生活习性充满了偏见,他们不仅将蜣螂和粪蝇看作不洁之物并加以摈弃,对于粪便的话题,自诩文明与庄重的人类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人类习惯于凭感觉去判断世间万物的是与非,他们既无视粪便是被世间广为利用的养分资源,更不会探讨粪便之于环境的重要贡献。“粪便”一词,也只是被他们当作相互攻讦或咒骂的武器,只有在脏话或秽语中才会被偶尔用到。
事实上,粪便,以及利用粪便生存的生物及其手段,既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也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据说最早的蜣螂发现于距今1.4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化石中,可见粪便与粪客的故事其来有自,历史源远流长。
远古时期,人类靠大自然的自我净化,就能远离污染源。农耕时代,人类通过掩埋,或者是倒入河流的方式来处理粪便。工业时代,人类发明了公共卫生处理系统:排水沟、公共厕所、下水管道……但不管身处哪个时代,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蜣螂和粪蝇这些保护环境的无名英雄,人类就会被自身或者牲畜的粪便湮没。
所以,对于人类而言,面对粪便和粪客,与其内心排斥,不如抱以开放的心态去重新认识它们,将学童间流传的重口味幽默转化为严肃的环境问题。在这方面,作者为我们提供的方式之一是换位思考,他认为要理解粪客,就要从它们的哲学出发,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庶几能够得出不失公允的结论。
它们都是“奇妙生物链”的一环作为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兼博物学家,琼斯自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植物学家,琼斯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即明显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从孩提时代起,琼斯就迷上了动物粪便及其中的居客,他的第一次昆虫调查报告是在十七岁时完成的,而他的探粪之旅则开始得更早——2015年初,当他撰写《自然的召唤》书稿时,已在英国各地采集收藏蜉金龟属蜣螂达四十五年之久。
在琼斯的探粪之旅中,他不仅日益意识到粪便和粪客在自然生态的循环与平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从中体验到无尽的乐趣。琼斯一直为懂得欣赏或知道采集粪甲、粪蝇及其他粪虫的人不多感到遗憾,他也一直为有机会亲眼目睹数以千计的蜣螂如潮水般涌向粪便的情形感到兴奋不已。作者以生动、幽默的笔法讲述了他偏爱的粪虫,他如何找到它们,如何观察它们,如何感受到“一些显得离奇,一些令人震惊,还有一些让人觉得非常美好”……从而将一个遭人轻视、受人鄙夷的话题,推上了科学专论的大雅之堂。
琼斯的寻虫经验是,不一定非要俯身扒粪,可以凑到近前,或者保持一定距离,即足以观察来来去去、无休无止的粪甲和粪蝇。如果在体量较大的牛粪或马粪中寻虫,要从粪缘开始,再沿着粪表的自然裂缝扒开,最后观察粪底的草根状况。琼斯一再提醒大家,赤手扒粪,深陷其中,寻虫事毕,一定要洗手。
有一次,琼斯亲手捕获到一只粪金龟蜣螂,当这只粪金龟蜣螂用光滑粗钝的头向前推,配合带齿的阔足努力飞走时,就如同一架迷你直升机升空,向下产生微微凉风。琼斯将这只粪金龟蜣螂飞过时发出的嗡嗡声,称作他“童年美好记忆中的夏夜之声”。琼斯的叙述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俳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当我们跳出世俗的偏见,用审美的眼光注目那些可爱的小生灵时,会发现自然界的昆虫并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分,它们都是“奇妙的生物链”的一环,同样构成了美丽精彩的生命世界。而热爱自然的作家情同此心,在他们的文字中,也无不流露出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善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