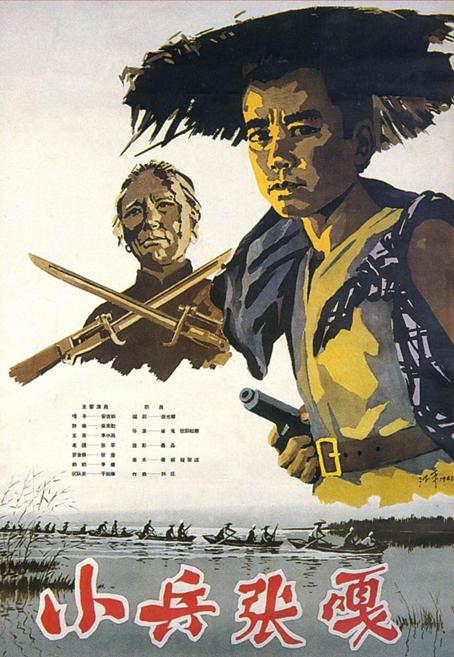网络大片《魔域血刹》上线后,一路热播,收视率超乎想象,是什么元素导致这部网络大电影引起观众共鸣?是什么手法让电影产生如此艺术效果?为让观众更深刻理解电影《魔域血刹》,2017年6月4日,怪奇公社新媒体联盟记者刘洪进专访了《魔域血刹》编剧杜鸿,看看编剧如何解说这部电影。

刘洪进:作为中国新生代作家代表,自本世纪初,您开始转型电影创作,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您精准转型新媒体电影创作,取得了不俗成绩。下面,请您作一下自我介绍。
杜 鸿:我理解的作家、编剧冠以著名,就是署名的意思。
因为作家编剧靠作品吃饭,所以,每部作品必须著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著作权版权归这个名字所有。
所以,但凡大家看到作家编剧前面有“著名”二字,不要以为他的作品也会有多么了不起,那只是表示他是这部作品的所有人而已,因为他是一个署了自己名字的作家。而他的作品是好是坏,你得看了才能做出准确评价,千万不要被他著了一个名,成为所谓的“著名作家编剧”而挟持。
作家编剧永远要靠作品说话。包括获奖,也只能代表一部分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的主持下做出的研判。里面究竟有多大程度与作品的“好”有关,你得自己看,自己辨别,而且你得拿出自己的真本事,来研判他的作品的好与坏。包括在我内。
虽然自去年以来,编剧电影入围第27届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获得了2016年第四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编剧“红枫叶奖”和第23届法国维苏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马车奖”及巴黎语言学院奖。但是,我的作品是好是坏,得您看了,由您说了算,就这么简单。包括正在爱奇艺独家热播的电影《魔域血刹》。
刘洪进:据了解,您此前从未涉及过魔幻类型电影的创作,是什么样的动因,让您通过电影《魔域血刹》开启涉足这类题材的尝试?
杜 鸿:类型电影,是中国电影产业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电影《魔域血刹》是我第一次涉足魔幻类型电影创作。
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与文学概念上的魔幻现实主义比较起来,影片更加直接地实现魔幻境界与现实境界、魔幻想故事与现实新闻、魔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有机对接,并以此来针砭时症,呼唤真善美。就成片来看,这一效果,非常完美地实现了。
最初接触这个作品,当然很新鲜。和其他原创作品比起来,类型电影有它自己既定的互文谱系和呈现节奏,甚至还有确保受众在审美和内容接受度上的既定程式。
所以,在创作这部电影作品时,我面临着重新学习,以此来吸纳这一电影类型所有最前沿的经验和成果。然后,站在这些成果和经济的肩膀上,完成新的创作。当然,这种过程,也是对自己的挑战。
与此同时,我将电影《魔域血刹》的创作,与典型的好莱坞式叙事结和典型的中国故事进行融合,使之既突然出讲好中国故事,又吸纳中外先进电影成熟经验,以此实现完美突破。这样,进入剧本创作之后,整个人就好像走进了一个从未涉足但特别具有陌生化效果的辉煌宫殿。
在电影里,好莱坞故事模型与魔域血刹的生死对决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承载着思想性、人文性和现实性的融合,最后形成了成熟的电影剧本,从而也完了本片的“英雄之旅”,同时也完成了我作为作者的“作家之旅”。
刘洪进:电影《魔域血刹》一上线,收看率直线拉升。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兴奋点,让它能够产生如此良好的收视效果?
杜 鸿:很多作家、编剧会对最终出来的影片说三道四。那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家编剧虽然身在影视行业,但是对影视行业没有本质上的认识和了解。
说实话,我在电影《魔域血刹》审片室里看完全片之后,相当长时间保持着沉默。为什么呢?因为内心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
可以说,从文字到镜头,从剧本到影片,这个过程简直太神奇了。就在那一刻,应该说,我发自内心对导演燕红兵、总导演演员胡军和青春派演员王艺瑾、孙鹤鹏、吴雅思的倾情主演,对胡凯莉、袁国扬、路占春、黄婷的联合主演,对著名怪奇特型演员外的倾力助阵,心里生出十分的感动。
从影片里,大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他们都是在用全力和生命共同创作着这样一部作品。从表演,到外影的选择;从特效到音效的创作;从一帧帧画面之间的转承衔接,到镜头呈现出来的故事伦理和节奏,都是他们付出极大努力,才收获到的心血之作、真诚之作和背水一战的绝地之作。
所以,这就奠定了这部影片收视长虹的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质量。质量绝对是决定影片的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就是电影《魔域血刹》的现实主义特质,创造出艺术性别出心裁的陌生化效果。这部影片看似全部建立在一种虚构的镜像上,演绎出人性的暖与冷的故事。
但是,在影片整个节奏的节点上,不无闪耀着现实主义作品所特有的精神光芒。像保护女孩、拯救男孩、鞭挞丑恶、颂扬真善美等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的情节与细节,直指人性深处的善恶抉择和人性温暖,呈现出人类共性的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文基调。
当然,影片收视率火爆,还表现在创作者们在摄制、后期和音效等方方面面,发扬工匠精神,力求精益求精,开创出震撼人心的镜头叙事高度,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置身电影所制造的代入感里面,让人无时无刻不感觉是在看一部院线大片。
刘洪进:电影《魔域血刹》是您完全超越现实创作的一部魔幻类型作品,而且自创了一个新魔界谱系。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谱系?
杜 鸿:在这个世界上,包括整个宇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每个事物虽然以个体性质而存在,但是在这些个体事物的内部,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或解剖,它们都存在自身特有的构成秩序和逻辑或者叫伦理与谱系。
即便是小到一个细胞,在它们的内部,依然都有着十分显著的构成规律和谱系。
所以,文艺作品,特别是需要以实现传播价值最大化的电影,就需要在故事及其故事真相上,将故事的起承转合和真相的内在伦理与逻辑,或是人物的层级谱系,交待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才能更好、更有价值地实现传播目标。所以,电影《魔域血刹》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循这条普遍的规律。
关于电影《魔域血刹》魔域的道统和谱系,其实没有刻意去突出哪个神统和宗教派别。
影片完全基于道儒释三教合一之后,以善恶对立为类别,分别建立了以白眉道人为代表和总领的正道化身,以花巅血刹为首领的邪道化身,从而构成了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体系,而这两个对立系统,全部归纳于惩恶扬善的总纲之下。
而为了顺应电影最前沿的艺术效果,在中国传统神统谱系的基础上,我引入了好莱坞最前沿的叙事谱系。比如,白眉道人这一人物,在好莱坞的故事模型里,又是智慧长老的化身;而花神佛莲沈紫嫣和罗志刚则是故事的主角英雄人物。而魔窟,则是洞穴的具体化;金晓峰、宋婷包括阴阳魔宇,则更多地充当了助手、朋友乃至叛徒、奸细,甚至打手的角色等符号,并且他们的人物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人物的角色也存在互换和多重属性,并通过剧情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与表现。
所以,电影《魔域血刹》既是在中国传统道儒释文化背景下讲述的中国故事,又是在好莱坞叙事模式统领下的“英雄之旅”在中国电影里的具体呈现。也正是这种双重谱系的融合与叠加,大大提高了电影内涵的深远性和外延上叙事能力的张力。
刘洪进:电影《魔域血刹》对未来网络大电影创作,有什么样经验和创作贡献?
杜 鸿:电影《魔域血刹》对未来的贡献和启示,主要表现在网络大电影大片化的尝试上。当然,这种大片化,主要表现在剧本内容及其节奏,融合了最现代的电影创作和市场元素,并做到了最佳基点的对接。
再就是摄制上的精益求精,实现了场景、剧情、镜头推演与叙事效能的大片化。
三是后期现代电影技术的运作,包括编辑、特效、3D和动画等当代最前沿的影视技术,在影片里得到充分和大量运用,从而确保了影片大片化和观众观影的刺激性效果。当然,影片还在策划和宣发上,进行开创性的运行模式创新,也是影片在市场准入和收视方面火爆的重要因素。
刘洪进:魔欲之子是一个什么样的隐喻?要想救赎男孩子,那么拯救女孩更是迫在眉睫?为什么电影会有英雄与恶魔的双重救赎的效果?
杜 鸿:电影《魔域血刹》讲述了一个多重救赎、向善而生的故事。
影片从故事层面到文化伦理,提供给观众的真相和内涵是多重救赎的可能性:一是男孩危机,必须救赎男孩。
影片通过沈紫嫣、罗志刚与魔欲的战斗,完成了对魔首花巅血刹的征服并救出了金晓峰,阻止了花巅血刹对男孩继续伤害的可能性,从而取得了救赎男孩战争的胜利。
二是救赎男孩子,必须拯救女孩。万事万物讲究因果。恶魔花巅血刹并非生来就是恶魔。她经历了从柔弱女孩、被伤害的女孩到跳楼的女孩,再到身怀仇恨的血刹、复仇的血刹和作恶多端的血刹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成长史。基于这个伦理得出的结论,要想救赎男孩子,那么拯救女孩更是迫在眉睫。
三是英雄与恶魔的双重救赎。影片从跨越进魔域边界的那一刻起,以沈紫嫣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和以花巅血刹为代表的恶魔势力,在一场善和恶的战争中,完成了彼此的双重救赎。因为战斗,沈紫嫣激发潜能,完成了由凡夫俗体到花神佛莲的升华,花巅血刹在孕成魔欲之子并接近魔力巅峰时,重新被收服并归于刹道,也完成了一种放下屠刀的向善救赎。
刘洪进:请谈谈您下一步的创作打算。
杜 鸿:今年的创作计划比较重。有三部电影需要创作。首先是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什么都好·结婚太早》,讲的是一个家族伦理故事。霸道总裁加玛丽苏的风格让戏份层出不穷,与其他传统玛丽苏剧的区别是,女主不再是柔弱、傻白甜的设定,而是能与困难对抗的女汉子。面对爱情的重重阻扰,她用她的机智一一排解。
其次去年就定下来,一直没能开机的反腐电影《猎瞳》。目前已经五易其稿,剧本还的继续打磨。主要讲的是杜十娘穿越到350年后,深入父亲杜撰和副市长孙富的巢穴获得了诈骗的核心证据,协助检察官柳遇春端掉了官商诈骗窝案。
再就是一部反映女性心路历程的电影《终生美丽》,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女性题材电影。
杜鸿简介:杜鸿,著名作家,编剧;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第六届委员,湖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主席,湖北省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微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石牌保卫战》《琵琶弦上说》和散文集《怀想三峡》等18部。主编有《中国非主流文学精选》(上下卷),译有《肯尼迪大家族》。编剧电影《谁杀了潘巾莲》《500米800米》等13部,编剧电影《500米800米》入围第27届斯德哥尔摩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获得2016年第四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编剧“红枫叶奖”。微电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获省广电局2016 “820”工程奖。2017年,编剧电影《500800米获》获得第23届法国维苏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马车奖”及巴黎语言学院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