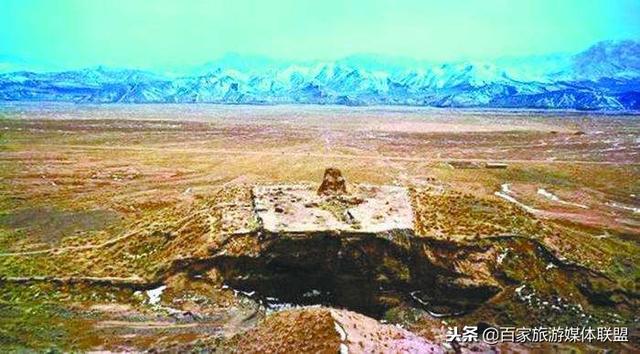薤菜:似韭非韭的菜中灵芝
汪鹤年

秦末,曾自立为齐王的齐国贵族田横自杀后,其门人曾写了两首悲歌哀悼他。后来,这两首歌成了古人常用的挽歌,这便是送王公贵人出殡的《薤露歌》和送士大夫、平民出殡的《蒿里曲》。曲以“薤露”名之,是说人生短促,犹如薤叶上的露水,瞬间即干。至于“蒿里”,则是传说中死人魂魄的聚居之所。
古人之所以用“薤露”来命名这首挽歌,可能基于两种原因:一是薤叶仅有数枚,中空,呈半圆柱状线形,生得极细,又极光滑,且有不明显的三至五棱,露纵然能在叶上凝结,水份也有限,难以持久,以“薤上露”来形容人生的短暂更为恰当;二是狭卵形的、可供食用的鳞茎其味苦辛,与送葬者的心情相吻合。于是,当“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的歌声响起,一种凄美的“伤逝”情结便弥漫在人们的心头,真不知撼动过多少脆弱的心灵。
在蔬菜中,薤是鲜食时间最短的一种,只有清明前的短短几天。这时所采的鳞茎白净透明、皮软肉糯、脆嫩无渣、香气浓郁,美其名曰“薤白”,自古被视为席上佐餐佳品。其嫩叶亦可炒食、煮食。除鲜用外,其鳞茎可用醋渍、盐渍、蜜渍等方法加工腌制成酱菜,即所谓“藠头”,分别有甜、酸两种。由于其含有蛋白质、维生素、核黄素、碳水化合物和钙、磷、铁等营养物质,食用价值高,且产量又少,一直列入高档蔬菜之列,素有“菜中灵芝”之美誉。
薤菜还是一味很好的药材,中医认为它有健脾开胃、理气宽胸、温中通阴、舒筋益气、通神安魂,散瘀止痛、杀菌消炎等功效。《神农本草经》说它有“轻身、不饥、耐老”之功。唐孟诜说“学道人长服之,可通神,安魂魄,益气,续筋力”。《食疗秘书》说其“除风,助阳道,去水气,泄大肠滞气,安胎利产妇”;《随息居饮食谱》认为可“散结定痛,宽胸止带,安胎活血,治痢”。《食疗本草》还记载了一种疗疮生肌的药方:“薤,轻身耐老。疗金疮,生肌肉,生捣薤白,以火封之。更以火就炙,令热气彻疮中,干则易之。”《本草衍义》也有方曰:“与蜜同捣,涂汤火伤,效甚速。”《食医心鉴》中还记载了用薤白粥治痢疾的偏方:“治赤白痢下:薤白一握、同米煮粥,日日食之。”

宜与热油同烹的苦味之蔬
起源于中国的薤,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极其悠久。宋代朱长文《墨池编》曾说:殷汤时“仙人务光辞汤之禅,隐于清冷之陂,植薤而食,清风时至。”这固然只是一种传说,不可全信。但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素问》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其所说的“五菜”之中,有益于肺的薤已占有一席:“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
编定于西汉的《礼记》中,更频频可见薤的身影。《礼记·内则》曰:“脂用葱,膏用薤。”郑玄注:“凝者为脂,释者为膏。”即油脂在常温下为固态者称为“脂”,呈流动状态者则称作“膏”。意思是说,如用冷油淋制凉拌菜,就以葱调味;如用热油炒菜,则以薤调味。《礼记·内则》又云:“肉腥,……切葱若薤,实之醯以柔之。”醯即醋。可见当时人们在烹饪肉食时,为消除其血腥味,常以葱、薤同肉一起放入醋中煮熬,这样不仅可除去腥味,还可使肉食更容易煮烂。
不知是何种缘故,战国时人还以为薤、葱等菜蔬具有醒瞌睡的功效,《康熙字典》引用的《仪礼·士相见礼》中就有“葱薤之属,食之止卧”的记载。
因薤略带苦味,秦汉时期的《灵枢经》还将薤作为苦味之蔬,与甜葵、酸韭、咸藿、辛葱同列为“五菜”,以附“五味”之说。
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道教,则将薤同韭、蒜、芸薹、胡荽等五种带刺激味的菜蔬视之为“五辛”,也称“五荤”。
两汉时期,薤的种植极为普遍。连宫苑中都每能见其身影,并采用了类似今温室的栽培技术。明末清初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就说:“汉世太官圃,冬种葱薤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以火,助其温澜乃生。召信臣为少府,以为不时之物,食之伤人,不可以奉供养,奏罢之。”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也有“正月,可种瓜、瓠、芥、葵、薤、大小葱”的记载。
据《汉书·龚遂传》记载,龚遂任渤海太守时,“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没有多久,便达到了“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的效果。
《后汉书·庞参传》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庞参被拜为汉阳太守,他上任之时,郡人任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庞参参悟良久,才明白其中所蕴含的企盼自己的上司能清廉自守,不畏豪强,开门恤孤之寓意:“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

主要用以调味的薤,渐渐还被人们用为普通菜蔬。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就在《塘上行》一诗中写道:“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尽管取鱼肉而弃葱薤的描述,采取的是比喻的艺术手法,但毕竟是当时现实生活的折光。
魏晋南北朝时期,薤的食用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发掘,种植经验也更加丰富。晋郭璞《尔雅》注云:“薤,鸿荟,又云劲山。茎叶亦与家在相类,而根长叶差大,仅若鹿葱。体性亦与家薤同,然今少用。薤虽辛而不荤五脏,故道家常饵之。兼补虚,最宜人。”
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载,当时人们在制作一种名叫“薤白蒸”的类似今加料糯米饭时,就将切碎的葱、薤、胡芹等作为专门的调料加入其中,以增加其香味。
《齐民要术》还系统地总结了种薤的经验:“薤宜白软良地,三转乃佳。二月、三月种。八月、九月种亦得。秋种者,春末生。率七八支为一本。谚曰:‘葱三薤四。’移葱者,三支为一本;种薤者,四支为一科。然支多者,科圆大,故以七八为率”;“叶生即锄,锄不厌数”;“叶不用剪,剪则损白”;“拟种子,至春地释,出,即曝之”。除了对种薤的择地、种植时间及每窝所种鳞茎数量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外,还就繁殖所用鳞茎的采掘要求、保存方法以及种植后的除草、剪叶等注意事项,进行了较详尽的说明。
据传,隋炀帝还仿效西胡人的酒品配置,用薤白制成“玉薤酒”,因醇厚甘洌,曾名闻遐迩。白居易《春寒》诗就赞颂过此酒:“今朝春气寒,自问何所欲。酥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李商隐《访隐》诗中也有“月从平楚转,泉自上方来。薤白罗朝馔,松黄暖夜杯”的吟咏。《本草纲目》认为,制作此酒的方法很简单:“以酥炒薤白投酒中”即可。
大约是因薤味道不错,也可能是薤的出产较少,唐人竟至将其作为馈赠礼品。杜甫就写过《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一诗:“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诗人在收到朋友的所馈薤菜后,就通过对其玉润珠圆,青翠欲滴情状的传神描绘,曲折地表达出对友人的深深谢意。

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腌渍的薤菜,大约可称得上是“藠头”的原型。宋陆游《咸薤》诗云:“冻薤此际价千金,不数狐泉槐叶面。”说的便是腌渍的薤白,可能因系新品的缘故,价格尤其昂贵。
当时,人们种植的薤菜,已普遍取代野生薤而成为常用菜蔬。《本草纲目》引北宋药物学家苏颂《本草图经》就反映出这种走向:“薤处处有之。春秋分莳,至冬叶枯。《尔雅》云:‘葝,山薤也。’生山中,茎叶与家薤相类,而根差长,叶差大,仅若鹿葱,体性亦与家薤同。今人少用。”
在元人王祯的《农书》中,亦可看到关于野生薤的记载:“一种麦原中自生者,俗呼为‘天薤’,即野薤也。叶比家薤较小,味亦辛。即《尔雅》所载‘葝,山薤’也。亦可供食,但不多有耳。”同书中对家薤更推崇备至:“[薤]生则气辛,熟则甘美。种之不蠹,食之有益。故学道者之所资,而老人之所宜食也。医家目之以为菜之珍,不亦宜乎?”
元人贾铭《饮食须知》还在总结前人种薤、食薤等有关经验的基础上,对薤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薤味辛苦,性温滑。一名藠子。其叶似细葱,中空而有棱,其根如蒜。有赤、白二种,赤者味苦,白者生食辛,熟食香。”足见,薤在元代已有赤、白两个品种。在吃法上,则有生食、熟食两种吃法。
据元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载,用薤白、粳米、葱白一起制作的薤白粥,据说可治老人肠胃虚冷、泄痢等症。
明清时期,薤仍为人所重,其吃法亦多种多样。明王世懋《学圃杂疏》曰:“葱、蒜、薤与韭虽俱五荤,而为人所常用。薤性稍平,江浙多有之。吾地少,亦可不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则云:“其根煮食、芼酒、糟藏、醋浸皆宜。”明末清初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还说:“薤有赤、白两种:赤者苦无味,白者肥且美,可供食馔,充药用,闽人目作素蔬,饭僧供佛,交天祀神,非此不称敬。”清高士奇《北墅抱瓮录》也说:“薤叶似葱而有棱,根似小蒜,一本数颗,相依而生,北人呼为藠子。……性能益气宣滞,于老人尤宜,故少陵有‘衰年味暖’之句也。”

不过,尽管薤已成菜蔬常品,但野生薤在人们生活中仍不时地充当着“客串”佳肴的角色。清人黎庶蕃《春菜诗》便形象地反映出“野藠”仍为人所爱的事实:“前胡落釜甘胜肉,野藠登盘贱于蔌。一春烟雨大巢生,十日燠晴香菌簇。”
北方人现在已极少吃薤了,但南方人对薤之钟爱之情仍丝毫未减,且大多以腌制为主。四川、湖南、贵州等地,人们常常把薤头与辣椒放入泡菜坛同泡。吃时,先拿出来与泡辣椒一起捣烂,再下些酱料调味,然后当作凉菜的拌料;或是直接用其下饭。其味酸辣咸,极其可口。当然,惯于鲜吃者仍可用其制作出薤白煎鸡蛋、薤白粥、腌薤白、糖醋薤白等肴馔来。
参考文献(略)
《先民菜篮子里的秘密》(连载)
版权作品:鄂作登字-2017-A-00016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