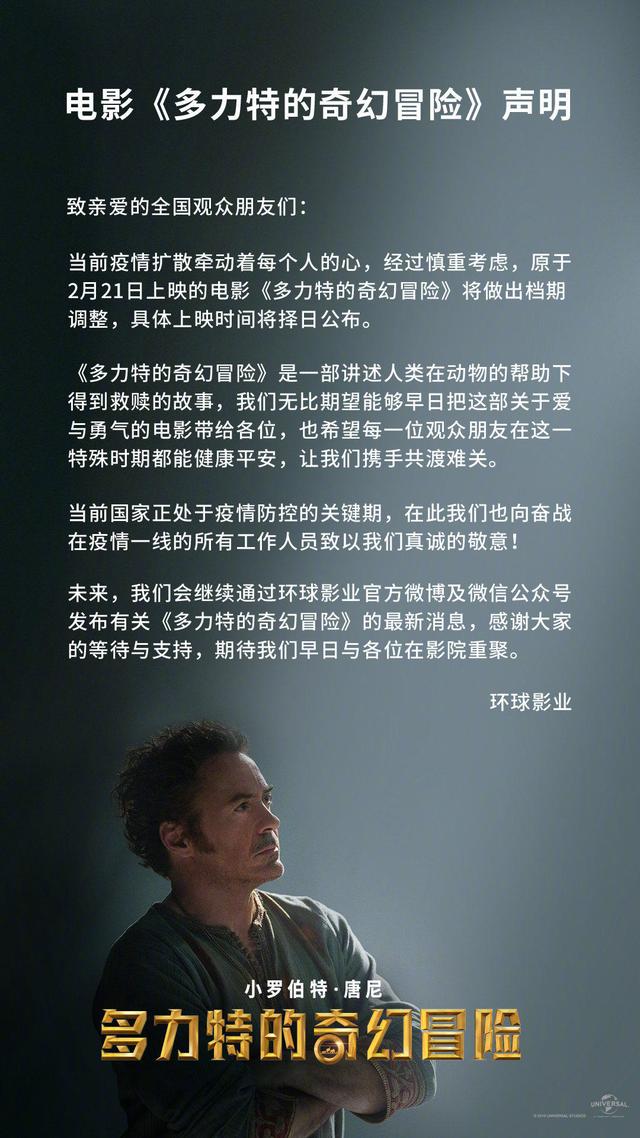《隐入尘烟》展现了四季的更迭和两个人情感的变化。 (剧组供图/图)
一个沉默干活的中年男人,一个行动踉跄的中年女人,一头低头拉磨的毛驴……
这是电影《隐入尘烟》中最重要的三个角色。
电影对白不多,大部分依靠动作推进叙事,农民的手和脚是闲不住的,一年四季都在劳作。观众跟随主角的劳作感受着四季的更迭,见证了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
四十多岁的“老光棍”马有铁的父母和两个哥哥早逝,没有人给他张罗婚事,他就寄居在唯一的亲人三哥家中,帮他养羊种地,直到年纪渐大,他开始被嫌弃。为了打发老四出门,三哥安排了一次“用心良苦”的相亲,托人带来了同样被家人嫌弃的贵英,一对大龄男女就这么结婚了。
婚后,马有铁发现贵英不但有残疾,还有小便失禁的毛病,他暗下决心带贵英进城看病。渐渐地,两个人走出了阴霾,用心经营着日子,盖房子、养动物、种植粮食,谱写自己的“田园牧歌”。但意外还是到来,贵英落水去世,一切都“隐入尘烟”。
暌违大银幕五年,导演李睿珺再度回到自己的家乡甘肃张掖高台县的村子里,拍了这部显得有些“沉默”的电影。套用网络流行语,这是一个“先婚后爱”的故事,两个原本毫不相识的人组成了家庭,还产生了感情,似乎并不符合人们对爱情的期待。
李睿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时候不能以城市的价值观去理解这种感情。通过老四和贵英的故事,他想要展现的是“唤醒和自我的发现”:“他俩就好像那颗被放在土里面的麦子,开始发现自己有爱和被爱的能力,有被别人依赖的价值,这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重回乡土
李睿珺出生于1983年,等到他们村大规模通电,已经是1990年代初。他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家的土坯房贴着一张从挂历上撕下来的照片,上面是北京的城市景色。当时的农村,很多人喜欢用这种挂历装饰自己的家,孩子们以此作为窗口去想象大城市的样貌。
高中时代,因为父亲的工作,李睿珺一家从村里搬去了县城,家里的宅基地就转让给了村人,他渐渐地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乡村。当李睿珺走出家乡,考上大学,并拍了几部电影之后,他才意识到:“城市能代表什么呢?它只能代表中国的局部,而更加真实、更普遍的情况是,中国人大多生活在乡村的世界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睿珺开始和童年记忆一一告别,家里的老房子早就被后来的主人荒废;爷爷奶奶去世后,叔叔买了新房,旧宅也被拆除,如今变成了一片空地。几年前,为了村容建设,村里有一项政策:如果愿意把留在村里废弃的房子拆除,政府可以补贴一万五千元。在外打工的同乡不少选择了接受安排。
这些变化被李睿珺悉数写进了《隐入尘烟》的剧本,当村里人都在抛弃故土的时候,老四和贵英却在坚守土地,他们自己做砖垒墙,一步步建起了自己的新家。
2020年初,李睿珺回乡筹拍这部电影,原本计划分成五次拍摄,用一年的时间拍完,很快疫情来袭,为了不耽误进度,他不敢离开村子。最初,剧组的工作人员进不来,他就动员家人和邻居一起参与拍摄,请姨父扮演男主角老四,他们还自己动手,建造了电影中老四的新家。
电影里贵英去世后,老四选择了离开,他辛苦建造的新屋被推土机拆除,给侄子换来一万五千元。李睿珺将这部电影命名为“隐入尘烟”,他想告诉观众:消失的东西并不是真的不存在了,它们只是隐藏起来。
2022年2月,《隐入尘烟》入围第72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李睿珺成为第一位入围“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80后导演。

为了扮演曹贵英,演员海清提前到李睿珺的家乡体验生活。 (剧组供图/图)
“外出打工不是唯一的选择了”
南方周末:《隐入尘烟》是一部关于土地的电影,土地是你创作的母题。在不同时期,你作品里的主人公展现出对土地不同的态度,这些内容是怎么来的?
李睿珺:我电影里的角色对待土地的态度是变化的,比如《老驴头》的主人公“老驴头”的儿女坐在商店里面说:“我们要土地干什么,我们出去打工很轻松呀,土地反而变成累赘了,有人包就给他吧,每年给我几百块钱,不好么?”那是2009年左右,当时农村的老人很多没有医保,合作医疗也尚未完善,老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赖土地,儿女出去打工,他们没有土地就无法生存,所以我展现的就是这样的矛盾——老年人想要保留自己的耕种权,而年轻一代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土地了。
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观察,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在外打工多年想要回家却回不来的人存在了,比如一些人年纪比较大了,村里的人会把他们当成城里人,认为他们早就应该在城里扎根了,这让他们不好意思再回来,处在尴尬的境地。
我后来就一直想拍一个曾经“抛弃”土地在外面打工的人若干年后是否可以留在城市的故事。正好到了2016年左右,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快40年了,第一批农民工也快60岁了,我觉得创作的机会来了。我想知道这批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的处境是什么,拍一个“老驴头”的子女和孙辈的故事,于是我就创作了《路过未来》。《路过未来》的故事主体发生在深圳,看上去像是一部城市电影,还第一次起用了明星,当时有人说我要转型了,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这些,就觉得是时候关注城市里的农村人的故事。
南方周末:你的很多电影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里面都有一个叫做张永福的人,为什么?
李睿珺:张永福在我的设定里就是一个受到土地政策影响的人,不同的时代他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比如在《路过未来》里,这个人物因为包地挣到了钱,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在《隐入尘烟》里他虽然在城里住上了别墅,结果却生病了,还需要被人救助。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土地承包,为何你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切?
李睿珺:土地流转的变化是农村的大问题,差不多从2009年开始的,始于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政策,其实就是有农民出自不同的原因把自己的耕地租出去,有能力的人就大量地把这些土地租过来,有的人甚至包了全村的地,再雇佣农民来耕种,给他们发工资。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集中耕种,节省劳动力,也方便机械化,但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也有可能发不出工资。
何况,还会出现一个人在外打工觉得累了想要回家,结果发现自己的地早就被包出去的情况。这类合同有时候一签就是三十年,等于这个人在村子里没有土地了,要靠买粮食度日,还要继续打工,可是等到他老了,没有劳动能力了,就只能被辞退,也没有土地可以养活自己。
南方周末:现在有一部分农村人没有那么向往城市了,很多人开始想要回到家乡,或者不愿意再去城市,据你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李睿珺:的确,他们会想自己为什么要去城市,每天比过去紧张,就算能多挣点钱,花的也多。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本来是学影视的,在北京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了两个月就回家乡了,他说自己想要复习考公务员,想要稳定的生活。
我九成的高中同学毕业后都回到了家乡的县城工作,还有一些甚至会选择在家养羊放羊,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选择。对于我们这些80后来说,好像开始觉得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不是唯一的选择了,在家反而更有安全感。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基本都是在家乡拍摄的,土地和家乡对你这样一个长年在外地工作的人意味着什么?
李睿珺:我认为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是说我们在土地上耕种才和土地建立关系。我电影里的老四和贵英也是如此,他们的生命在很多人眼中毫无价值,但是他们其实和庄稼是一样的,就算没有家人的接纳,土地也会接纳他们。
我经常回家,但对家乡的态度很复杂,可以说是爱恨交织,我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这个变化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我也不能粉饰它。从物质层面来说,家乡肯定是一天天在进步的,我家到1990年代初才通电,现在大家也都用上了网络;以前很多人没钱看病,现在有了合作医疗……但从情感层面来说,确实越来越冷漠了,人际交往以利益出发的情况越来越多。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隐入尘烟》里对乡村伦理关系的展现?老四和贵英的家人和邻居对待他们的态度似乎非常残忍。
李睿珺:社会不断地在变化,人的关系也会。比如我现在只要通过视频就可以和家乡的母亲对话,以前必须坐火车回家,看上去紧密了,却和家人失去了坐在一起的机会。我想农耕文明也进入了2.0时代,每个人都想搭上时代的高铁,老四和贵英就是被挤下车的人,后面再来的车他们不愿意去乘坐了,但他们可能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往前走。
而那些跑得比较快的村民也会迷失,很多东西被异化了,也许偶尔还有一些残存的记忆,这可能就展现为他们对待老四和贵英的态度吧,偶尔也会同情,但大部分时候是冷漠的。我认为老四和贵英的离开,就好像是一个1.0的农耕文明时代的结束。

马有铁和曹贵英两人在婚后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秩序,他们获得了从未获得的尊重和爱。 (剧组供图/图)
农村女性和光棍的“价值”
南方周末:和你之前的电影比起来,《隐入尘烟》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特别关注到了农村的女性群体,对她们的刻画更深刻了一些。近年来,很少有电影关注农村女性这个群体,更不要说贵英这种身有残疾还不能生育的女性,你是如何关注到这个群体的命运的?
李睿珺:农村的女性的价值很容易被漠视,但她们是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和意义。
我拍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想要展现一对孤独的男女,他们有相似的命运,如何去应对周遭的一切。我想记录下这对男女的一段生活,表现他们如何去建立感情,如何营造家园,如何跟世界相处以及如何自洽的问题。
南方周末:我记得片子里有一个细节是说,贵英的病也是可以治好的,只是她家里人不愿意带她治病。
李睿珺: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看病,怕给家人增加负担,贵英的家人更顾不上她了。而且贵英的病不是完全生理性的,其实也是一个精神性的疾病,她的哥嫂以前经常打骂她,她一害怕小便也容易失禁。
片子里有一场戏,她冬天的时候跑到村口等老四回家,老四见了呵斥她,贵英吓了一跳。其实老四担忧的是这么冷的天如果感冒了怎么办,他还给贵英买了一件大衣披上,这一举动又让她吓了一跳。贵英的病是长期受到惊吓造成的,结婚之后她慢慢获得了安全感,后来就越发地自如和放松,还能干一些农活了。
南方周末:有的观众可能不太理解老四这个角色的处境,他身体健康,也比较能干,为什么甘于在哥哥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个现象在农村普遍吗?
李睿珺:村子里的婚姻都是父母给安排的,如果父母实在无力,自己也不出挑,性格也不活泼,很多人就这么单着了。就我的观察,村子里没有结婚的男性不在少数,很多还是80后,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相对来说,女性单身的状况会少很多,她们即使离婚或者守寡,很快都会有人上门提亲的。我们家乡的村子里,现在的确有人像老四这样的,四十多岁也没有结婚,给哥哥家放羊为生,他家里连台电视都没有,我甚至没有听他讲过话,不是他不会说话,而是他不想说话。他每天很早就出门放羊,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事情做,就去村里的小卖部看年轻人打牌,也不说话,就坐在角落,哥哥嫂子做了饭他就吃,第二天又去放羊,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
我对老四的理解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找到老婆,也没有机会出去打工,到了侄子都要结婚的年纪,家里人觉得他有些多余,才给他介绍了贵英,他只要结婚就可以分家出去单过。但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才有人开始在乎自己,有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尊重,他们在彼此身上都找到了以前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他们可能不觉得自己命运悲苦”
南方周末:你会不会觉得老四和贵英的生活太被动,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反抗一样,你觉得这说明他俩是愚昧的吗?
李睿珺:不是的,他们是有反抗的,只能说用自己的方式,显得比较微弱吧。当村子里的人都在嫌弃贵英的时候,老四的做法就是当着他们的面把贵英抱上驴车,在她尿裤子的时候为她披上自己的羊皮袄子,这就是用行动告诉其他人“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贵英本来是一个十分胆小的女人,但是当她和老四在一起之后,也变得勇敢起来。比如老四去给包村里地的张永福献血,贵英会拽住他的衣角表示不满,还会去敲护士的窗户,提醒她差不多了,赶紧把针管拔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维护体面和尊严,是有自己的自主意识的。
他们有自己的生存哲学。电影里反复出现麦子,这些麦子被选为种子,长成粮食,再被磨成面粉……这些并不是麦子的选择,它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无法决定自己何时被播种,何时被收割。庄稼人相对于麦子是自由的,他们有手有脚,可以自主地行动,所以老四和贵英可能并不觉得自己的命运是悲苦的,他们也可以相对从容地面对其他人。
南方周末:你身边类似老四和贵英的人多吗?他们大多是什么样的命运?
李睿珺:一直都会有类似的人,我还带着海清(在片中饰演贵英)去我们当地的养老院去观察,里面很多都是像老四和贵英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在村子里就是五保户,但其实他们往往是没有人去照料的,现在住进养老院虽然条件不能说多好,至少不用风餐露宿了。
当然,我去养老院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村子几个熟人表现得很沉默,也许他们还是喜欢在田间地头奔波的感觉,因为农民是闲不住的,一旦闲下来,他的状态就变了,这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隐入尘烟》原本有一场戏,村里的人就问老四为啥要和贵英结婚,她不能生孩子也不能干活,只能是个拖累,还不如去养老院。老四就觉得为什么自己要去养老院,自己有手有脚,可以劳动,那样更自由,他是不愿意成为五保户的。所以电影里他哥哥让他申请政府的保障房,为侄子结婚弄套楼房,他也是不情愿的。
南方周末:《隐入尘烟》的结局给人一种急转直下的感觉,本来两个人的生活渐渐开始好转,但贵英却意外落水去世了。为什么你会安排这样一个结局?
李睿珺:有些东西它该来的就会来。本身他俩在一起就是一个意外,所以他俩的结束也是一个意外。但是不在了不代表没有来过这个世界,麦粒长成麦苗,再变成成熟的麦穗,收割后回到麦子的形态,这些也仅仅是生命的不同阶段。收割不代表死亡,第二年又会孕育新的生命,土地一年四季都在见证生活的轮回,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命观。
贵英不小心铲掉了一颗麦子,老四说没关系,反正到了夏天也是要被收割的,把它埋在土里,它变成了其他麦子的肥料,它就还有价值,不一定要抽出麦穗才有价值。
“关键是找到值得拍的东西”
南方周末:海清是《隐入尘烟》的女主角,贵英这个角色和她之前的形象有很大不同,为何你会选择与她合作,又为什么选择非职业演员作为男主角?
李睿珺:我和她认识有几年了,我写完《隐入尘烟》这部戏觉得贵英这个角色很适合她,和她的年龄也相仿,我就问她愿不愿意试试看,她看完剧本也很喜欢,就答应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再找一个职业男演员和她配戏,但是我发现不是每个职业演员都能拿出一年的时间来拍摄,我就觉得我姨父是不是也挺合适的,他之前也演过我的好几部电影了。也因为疫情的因素,加上马有铁有很多干农活的动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我们就定了姨父扮演男主角。另外,海清到了高台之后,其实有段时间就是住在姨父家里,所以他们之间已经比较熟悉了,我和她说要不男主角就找我姨父吧,她也觉得没问题。
南方周末:你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疫情,电影行业受到很大影响,你担心电影拍出来之后没办法上映或者没什么票房吗?产业的变化对你拍摄造成什么影响了吗?
李睿珺:这几年艺术片的确是不太容易,拿到投资的机会在变少,但是我想既然我之前可以花30万拍一部电影,我现在也可以。
说实话,这个电影我最初找人的时候,肯定是希望按照工业标准去呈现的,结果遇到困难,那就退回到最初的方式,我觉得也可以接受。有好的摄影、录音、灯光固然是好的,不行就用最原始的办法,大不了就多花一些时间,不能说有朋友请我吃了一顿满汉全席,我以后除了这个就不吃饭了,没钱的时候一样要吃馒头配老干妈。
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值得拍的东西。拍电影还是一个行动力的问题,真的想要拍摄,没有什么可以拦阻,就好像我要说话,有人把我的嘴捂上,我还是会发声的。
南方周末:你在拍摄《路过未来》之前,似乎一直都保持着独立电影的制片方式,你电影的资金从哪来?
李睿珺:《夏至》就是我自己筹了30万拍的,一开始也不懂,还想着用胶片拍,后来才知道以我当时的条件只能用HDV摄影机拍。这个片子我父亲给了我一部分钱,本来是他们要买房子的,我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就拍成了。
到了《老驴头》,我的状态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还钱,但确实又想拍,那就决定还是做一个低成本的电影出来,我的剧本有人说写得很好,我就投了鹿特丹电影节的剧本发展基金,得到了一万欧元的赞助,加上我和妻子两个人在电视台打工赚的钱,我们就又拍了一部。拍摄的方式就是回家动员所有的亲戚朋友,把他们训练成“演员”。其实这时我就发现既然找不到投资,我就先拍再说,技术什么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做后期的时候,我们又得到鹿特丹赞助的2万欧元,这样就拍完了。
其实我第一部获得投资的电影是《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天画画天(电影公司)说可以给我投资50万,我就拿这个钱回老家拍了出来。到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投资多了一些,是天画画天和劳雷两家公司拿了两百多万做出来的。之后就是拍《路过未来》,安乐的江志强给我投了一千万,《隐入尘烟》的成本也差不多。
南方周末:其实你的电影都算是小成本制作,《隐入尘烟》的出品方好像有好几家,你能谈谈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吗?
李睿珺: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我的剧本设定就是要拍摄四季变化,我从一开始就想在村子里待一年,投资也谈得差不多了,打算分成五个周期拍完,每次拍二十多天这样,正好可以完整地拍到村子的四季变化。
结果赶上了2020年的疫情暴发,一开始谈好的投资就断了,我只好先拿自己的钱拍,把第一周期的拍摄扛下来,后面又找了一些资金,把第二周期的拍摄也解决了,等到了第三周期,实在是没有钱了,能问的公司我都问了,最后兜里只剩下2000块钱,给孩子准备上幼儿园的钱都被我花了。万般无奈之下,我托朋友几经辗转找到了嘉映的负责人覃宏,他很愿意支持我们,说虽然经济不好,但我们总还是要生存下去。我和妻子赶紧买了一张19小时到北京的车票回来见他,他说马上给我们打钱,让我们赶紧去拍。同时他又帮我们找了其他几家公司一起投钱,就这样我们才把《隐入尘烟》拍摄完成。
我现在意识到,拍电影就是一个不断地解决困难的过程。
南方周末:从你的第一部电影《夏至》算起,你现在已经有六部长片问世了,在十来年的创作中,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
李睿珺:我很难总结说自己有什么变化,只能说拍电影确实越来越难了。这个难有几方面的因素,有环境的,也有资金的,还有创作层面的——我对自己的要求高了,对电影产生了敬畏。不像拍摄《夏至》的时候,我就想管他呢,随便划拉一个故事拍了再说。
其实每一次拍摄机会都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只能说是珍惜,尽可能在有限的资源和条件下做到最好,这也是导演唯一可控的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