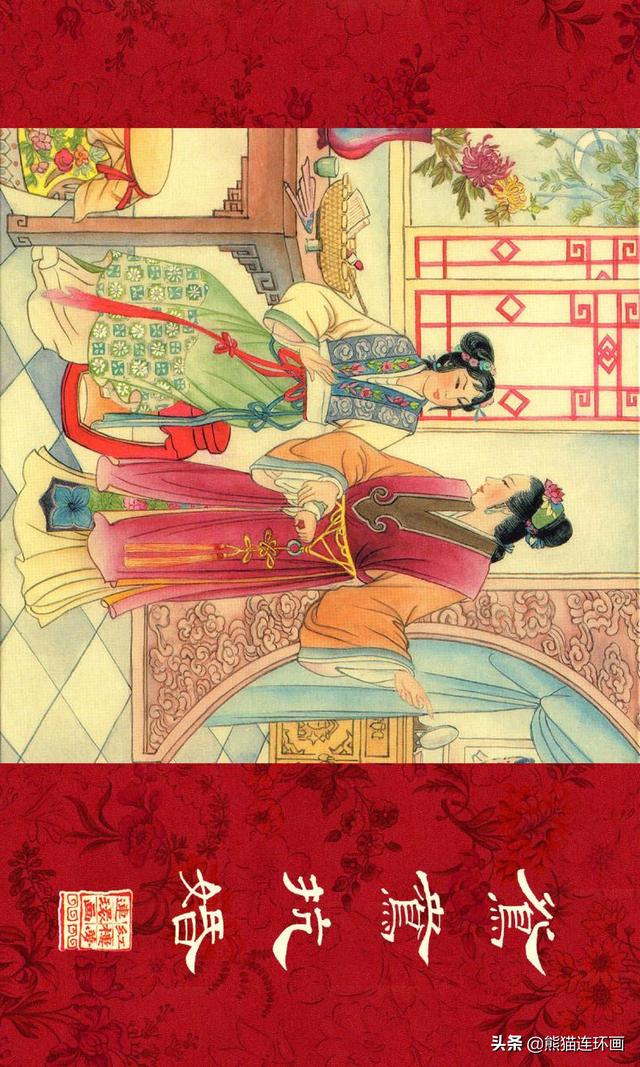2018年11月9日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9月开始,香港、杭州、北京等地陆续推出了纪念丰子恺的几个大展。
记者/薛芃
丰子恺
丰子恺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画家。在所有对他绘画的描述中,“雅俗共赏”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用笔简练又有意趣,有批判,有关怀,还有温情,画的都是生活,讲的却是人生。他的漫画从浪漫化、抒情性,到充满童真童趣,再到抗战时期和1949年之后一度成为宣传工具,这个过程也成了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漫画史。
但丰子恺终其一生都怀抱着浪漫主义的生活情怀,他是画家,更是一个文人,一个典型的从民国思潮中长出来的知识分子。
日本画家竹久梦二
“遇见”竹久梦二很难想象,如果年轻时的丰子恺没有痴迷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他日后是否还会画出这样的“子恺漫画”,甚至是否还会继续画画。
竹久梦二对丰子恺绘画的影响,几乎渗透形式、内容、情怀各个层面,更重要的是,在20岁出头迷失方向的这个年轻人心中,梦二成为一种精神动力,牵引着丰子恺,似乎在告诉他,画画并非没有出路,关键是看你画什么,怎么画。
1919年夏,21岁的丰子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急切地渴望继续深造。这时,他已经在恩师李叔同的引导下,学习了两年西洋画。李叔同曾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5年,跟着日本外光派画家黑田清辉学习油画,师法自然,偏爱明快的色调和户外光线。所以,当他自己回国教学时,自然也是一套西方美术教育的方法。从浙一师的第三年起,李叔同开始教丰子恺图画课和音乐课,这也成了日后丰子恺涉猎的主要领域。然而,丰子恺很快就在绘画这件事上产生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画不好素描,办过一次画展也掀不起任何涟漪,无济于事,经济上又让他力不从心,他一方面憧憬着走上职业画家的道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叩问自己到底要不要继续学画。
毕业后,丰子恺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回老家桐乡石门湾做一个安分的小学老师,而是与同学吴梦非和刘质平一起,去上海办学。1920年,他们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这是继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学校之后,上海市第二个专门教授西洋画的艺术学校。同年4月,又与刘海粟、姜丹书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美育学术刊物《美育》月刊。
短短一年中,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本刊物,看似丰子恺已经卷入了上海文化旋涡中心即将大干一番的时候,他“几乎立刻就后悔为了一份固定职业而放弃学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丰子恺研究者张斌说:“从1930到1937年,丰子恺回老家修建了缘缘堂,那个时候就想赋闲在家,写写画画,过田园诗人的日子。而这种理想生活其实一早就在丰子恺心中埋下了种子。”上海的花花世界显然不适合丰子恺。
但在上海的两年中,丰子恺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在上世纪20年代的留洋热潮中,丰子恺决定借钱赴日留学,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在文化上“现代”起来。
日本的留学生活只有短短10个月,他将自己的这10个月称为“游学”。“遇见”竹久梦二,是在东京神田的二手书店。竹久梦二的绘画,是典型的明治晚期(20世纪初)和大正时期的艺术风格,充满了哀伤情调的日本式唯美风格,尤其是后期的美人画。丰子恺看到的这本《春之卷》画集,1909年由乐阳堂出版,发行后广受欢迎,集子中收录了梦二早期诗配画作品,哀伤的情绪还没那么浓烈。后来丰子恺在《谈日本的漫画》一文中这样诠释梦二的作品:“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的,笔法是东洋的。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以前的漫画家,差不多全以诙谐滑稽、讽刺、游戏为主题,梦二则摒除此种趣味而专写深沉严肃的人生滋味。使人看了概念人生,抽发遐想。故他的画实在不能概称为漫画,真可称为‘无声之诗’呢。”
1921年末从日本归来时的丰子恺
但是当丰子恺看到《春之卷》时,竹久梦二已经不再画诗配画了,而是转向更为流行的美人画。张斌告诉我:“梦二《春之卷》中的这类诗配画在日本流行的时间很短,早于丰子恺到日本的时间十来年,那是日本杂志和刊物刚刚兴起的时候,梦二常在这些出版物上发表这些小画,也会做一些书籍的装帧设计。而丰子恺比梦二小14岁,中国杂志出版的兴起时间晚于日本十几年,也就是说,在与杂志出版的关系上,丰子恺与竹久梦二颇为相似。”
从绘画风格上来说,丰子恺究竟是怎样具体被梦二影响的呢?浙江美术馆的展览中,策展人将二人的类似题材作品并置对比,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同级生》一画收录在《春之卷》中,梦二以毛笔速写,画中一位坐着人力车的贵妇与一位站在路边背着婴儿、蓬头垢面的妇人相见寒暄,这是多年前的同学在各自经历巨大变化后的一次短暂相聚,梦二画的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怪相和人世悲凉。与之对比的是收录在1945年《子恺漫画全集:学生相》中的一幅《小学时代的同学》,西装革履、手拿画框、全身透着现代气息的进步青年,遇上肩挑扁担、粗布褴褛的底层商贩,他们也曾是同学。
丰子恺曾经明确地写道,《同级生》真正打动他的不仅是简单的线条,更是诗趣和画题,这种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漫画生涯。
除了绘画本身,丰子恺与梦二也有很多其他“巧合”,在杂志刊物上发表漫画而成名是其中之一。梦二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但因为很少参加大型画展而被当作“游走在艺术世界边缘的业余画家”,在这一点上,丰子恺也与之相似。
在日本的短暂游学期间,竹久梦二的作品给迷茫中的丰子恺打开了一扇大门,他试着收集所有竹久梦二的画集,但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这太难了。离开之时,他便委托在东京的酒友、同是爱书之人的黄涵秋,让他帮忙留意。丰子恺回国后,黄涵秋陆续集齐了夏、秋、冬三卷,又与梦二的《京人形》《梦二画手本》一同寄给了回到上海的丰子恺。这些画册一直陪伴着丰子恺度过创作的黄金时期直到中年,后来在颠沛流离中散落遗失了。
遗憾的是,丰子恺一直与竹久梦二是“神交”,他从未见过梦二本人。他在1936年写道:“这位老画家现在还在世间,但是沉默。我每遇从日本来的美术关系者,必探问梦二先生的消息,每次听到的总是‘不知’。”
丰子恺《儿童放学》 ,30.1×22.7厘米,设色纸本(丰子恺家族收藏)
丰子恺《好花时节》,34×27.2厘米,设色纸本(丰子恺家族收藏)
子恺漫画回国后,丰子恺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并给《美育》杂志做装帧设计,还给其他杂志画插图,包括朱自清主编的《我们的七月》。丰子恺初获影响力,是通过上海知识分子圈中的口口相传。
朱自清与丰子恺同龄,他注意到丰子恺,是因了丰在浙一师读书时另外一位恩师夏丏尊的推荐。当丰子恺游学日本时,朱自清与夏丏尊成了同事,任教于浙一师。朱自清又将丰子恺介绍给了作家、翻译家郑振铎和诗人、散文家俞平伯。郑振铎并不是一个与当时画家交往密切的人,但他看到了丰子恺在《我们的七月》上发表的第一幅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很喜欢,这也是丰子恺第一次以“TK”之名公开发表作品,“TK”意为“Tsu-Kai”,是“子恺”当时的英文缩写。
1925年开始,丰子恺受郑振铎之邀,开始为刊物《文学周报》定期供稿。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é)在著作《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中写道:“在发行《文学月刊》时,郑振铎希望用丰子恺的漫画和装帧设计抗衡自己心中的竞争对手刊物的诱人图片。丰子恺干净、整洁甚至略显简朴的漫画为这份精英文化刊物增添了时代气息,与‘鸳鸯蝴蝶派’多愁善感的情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文学周报》来说,刊物想吸引的读者,是那些讨厌低级趣味、又反感陈旧乏味的严肃文艺的人,也就是那个时代进步的人,这些人也成了丰子恺漫画的第一批簇拥者。
发表在《文学周报》上的作品多是黑白木刻式的小插图,以“古诗新画”为主要类型。他画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秦观的“指冷玉笙寒”,杜牧的“卧看牵牛织女星”,用笔简练也随性,构图精巧,不在画面中加入多余的元素,干干净净很通透。他喜欢用毛笔先随意勾出个小边框,再在其中作画,这多少是受了风俗画前辈陈师曾的影响。
这时的丰子恺选择画“古诗新画”是有些令人费解的。从在浙一师读书到日本游学,丰子恺都更倾心西方艺术,他曾经非常反感《芥子园画谱》,认为那是程式的、守旧的,艺术不该如此。但在“五四”新风的氛围中,他反向选择大量画古代诗句,发表在刊物上,也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几分古意。张斌说:“丰子恺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以《芥子园画谱》为例,年轻时很排斥,但后来由于自己研究中国艺术史,又教书,对‘芥子园’的态度便有了转变,到了后期,则很赞同其中的某些教学画法。他对传统的态度也不会太随波逐流,多是依着自己的性子和喜好。”关于“古诗新画”,白杰明认为这是“艺术家的文学视角”,而且在这些小画中,古典的气息仍是以现代的画法传达的,诗图相配,有些哀婉的抒情调调,也应了竹久梦二对丰子恺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而,左翼人士可看不惯这种调调,他们常在自己的刊物中撰文批判。尽管后期丰子恺的绘画内容转向生活,也画世态炎凉,但在他的骨子里,有着不可磨灭的抒情格调,这一点成就了他的独特性,也成为他“一生都不得不面对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
1929年之后,“古诗新画”的作品少了很多,直到1943年他创作出最后一册“古诗新画”的集子,取名《画中有诗》,写到自己偏爱此类创作的原因:“余读古人诗,常觉其中佳句,似为现代人生写照,或竟为我代言。盖诗言情,人情千古不变,故为诗千古常新。”
无论如何,郑振铎非常喜欢这些插画,他决定将其称为“子恺漫画”。虽然“漫画”一词早有出现,但在中国,从丰子恺开始,这个概念才作为一个新兴词语普及开来。后来,俞平伯在给《子恺漫画》第一集的跋中写道:“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这两句评价确实很精确地概括了丰子恺的画风,而且自20年代起至晚年,丰子恺的风格就相对统一,其间虽有变化,但不出大的框架,无论是绘画语言,还是题材格调,都一早就打上了丰氏烙印。他说自己作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把漫画比作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丰子恺《大道将成》,设色纸本册页
找回童心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在现在的浙江桐乡市石门镇。京杭大运河在这里形成一个120度的大弯折向东北,缘缘堂就在转弯的夹角处。1933年春,依靠着几本畅销书的版税收入和开明书店股份的固定分红,丰子恺有了一定积蓄,决定回到故乡石门湾,修建一处由自己设计的家宅。
如今,在丰子恺的老家桐乡,街头随处可见“子恺漫画”。这些小画依旧不过时,其中传达出的伦理道德,更像是一种温情的规训,成为人们生活的背景。
他的宅子位于石门最好的一块地方,坐北朝南,打开院门就是河水。今天的石门镇上,仍多是白墙黑瓦,现代的建筑痕迹很少,还可以依稀感受到从前的宁静与安详。丰子恺当年也是看重故乡的安宁,选择离开纷闹的上海。再加上童年恣意玩乐的生活是他最美好的一段记忆,成年之后,他总感伤于失去了年少时的天真、简单和勇气,儿女的接连出生,也让他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但他逐渐将这种失落感转化为与子女同乐的童趣,家庭生活成了丰子恺新的重心。
早在1925年,丰子恺为俞平伯诗集《忆》创作的插图,就是其童心的初次展露。这个偶然的开端,开启了丰子恺在作品中追求纯真、以儿童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俞平伯的诗句写的多是回忆,他与丰子恺一样,沉湎在童年往昔的记忆中,多少也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因此,他们的诗与图格外相配。《忆》是民国时期最为雅致的出版物之一,用宣纸精印,线装,丰子恺画了18张插图,朱自清写了跋文,这时他们三人都只有20多岁,已经开始通过《忆》这本小册子,追忆童年、告别青年了。
“五四”时期是中国“发现”童真的时期,许多刊物上都刊载了儿童行为、心理的研究,儿童文学、童话也大量出现,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冰心的儿童散文都是其中代表。所以,《忆》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只可惜,这三个“文艺青年”把《忆》做得太过精致,定价高,内容也遭到了政治立场坚定的批评者抨击,他们这一次的童心,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但对于丰子恺而言,《忆》中的插画已为日后家庭生活题材的漫画埋下了种子。
当了父亲之后,丰子恺画儿童越来越多,这既是他作为父亲的慈爱,更是因为,他越来越认识到,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具有自然之美,他向往“儿童的清白的世界”,认为“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
丰子恺的嫡孙丰羽是其幼子丰新枚的儿子,他告诉我:“爷爷很爱跟小辈孩子们一起玩,他也不会故意做出老人的姿态,对孩子们指手画脚。”丰羽说爷爷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一句话:“阿要喝酒啊?”丰子恺极爱喝酒,闲来无事就会温一壶绍兴黄酒,与友人或家人聊天。跟孙子辈聊天时,也总爱开玩笑,他喜欢孩子的天真与自在,也喜欢自己与孩子在一起时的那份无忧无虑。
从20年代到40年代初,丰子恺画了大量儿童画。20年代,独子瞻瞻是家中最小的男孩,时常入画,还有大姐阿宝(丰陈宝)和侄女软软,丰子恺在随笔中写道:“他们三人就像罗马帝国的政治三巨头,瞻瞻在这三人中势力最盛,好比罗马三巨头中的领胄,我名义上是他们的父亲,实际上是他们的臣仆,而我自己却以为是站在他们这政治舞台下面的观剧者。”
丰子恺的儿童画几乎都源自生活,他如记日记一般用寥寥几笔画下日常点滴。丰羽每次在看这些画时,都感到格外亲切:“我一看就非常有感觉,这些人物很熟,都有接触,所以这是跟其他人看画不同的地方。”
白杰明认为,丰子恺超前的儿童观念并不仅仅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美学赞美儿童的中国翻版,也不是冰心那种“五四”时期“儒家浪漫主义”道德观念的简单折射。他赞美儿女的纯真,最常画的却是孩子们心安理得的自私与自恋,他画穿着爸爸衣服洋洋自得的儿子,也画拿着两把蒲扇假装骑自行车自娱自乐的儿子,真实,自然,不呆板,不虚伪,这样的儿童画在当时非常少见。他的这种观点也与当时更流行的“儿童进化说”相左,如今看来,丰子恺显然是前卫的。
竹久梦二《海边的太阳》《江畔秋景》《木偶》(三条屏) , 108.3×34.3厘米,设色绢本立轴
“护生”与逃难“在丰子恺的绘画生涯中,有一条线索与我们现在梳理的漫画是并行的,就是《护生画集》。如果说在漫画中能看到更多生活中的丰子恺,在‘护生画’中,则是另一个更内省的、更警世的丰子恺。”丰羽在谈到爷爷的绘画时,特别强调了贯穿丰子恺一生的《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的诞生,是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一个约定。
1918年秋,刚满40岁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法师。当时浙一师的校长经亨颐很是担心,他怕李叔同的行为会给学生们带来影响,因此专门开会宣布“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可禁令归禁令,李叔同还是在学生中间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的学生中至少有两人遁入空门,丰子恺也在1927年成为了一名佛教居士。
这一年,丰子恺30岁,他觉得自己人到中年,失去了青春时的热情,只能被动地接受已然的世界,他陷入了自我认同的悲观中。他画了一幅自画像《三十老人》,画中的自己头发稀疏,疲惫不堪,丧失了热情和能量。这个时候,他跟姐姐丰满一起皈依“佛、法、僧”三宝,成为居士,弘一法师为他们主持了仪式。
1928年,皈依佛教不久的丰子恺画了50幅“护生画”,来纪念弘一法师50岁寿诞和他出家10周年。50幅画都由弘一配诗文,他选用了很多警诫大众勿杀生、勿食肉的段落,以安详平和的书法写就。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约定,从第一卷起,《护生画集》每隔10年续绘一集,每集增加10幅画与诗,直到1979年弘一法师百岁诞辰时,将在第六集中绘百幅画作。完成这6集,总共需要50年。最终丰子恺在1975年去世前画完了一共450幅“护生画”。
“护生画”的每一幅都不复杂,讲的也都是普世的价值观——爱护生命、平等、仁慈,李叔同与丰子恺所追随的佛法,并不是个人的解脱和逃避,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谓“刚健的佛法”。张斌说:“6部《护生画集》,一共画了45年,其实内在是一个整体,丰子恺将这个心愿贯穿在整个生命中,对他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也将弘一法师给他的影响贯穿了整个生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丰子恺带着全家开始逃难。离开浙江之后,历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未曾看到过的大山大水,这些陌生的风景触动了他,他开始画人物风景画。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这是丰子恺的一个重大转变。之前在上海、杭州时,他的画作多是小幅的、黑白的,以出版为主,日常生活是他绘画素材的来源。逃难开始后,他开始画稍微大一些的彩墨画,明快的色彩逐渐成了另一大特点。虽然一路颠沛流离,生活艰辛,也历经了战争的残酷,但凡此种种他的绘画中反而体现得不多,他仍然尽力在绘画中传达乐观的态度。
自始至终,丰子恺都画漫画,但他的东西有别于典型的讽刺漫画,不带刺,不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子恺漫画·战时相》里收集的黑白小画,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气氛最为紧张的——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正在奋力逃难,却不知自己紧紧背在身后的孩子早已身首分离;母亲遍体鳞伤,却仍抱着婴儿哺乳;他画在战壕里谈天的士兵和送丈夫出征的年轻妻子,还画过一幅《警报做媒人》——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警报声中躲在一个僻静幽美的山涧中,享受着难得的、私密的爱情。在战争的冰冷残酷中,丰子恺总是努力寻找着那些人性的温情。
第三种人1949年之后,丰子恺在上海安定下来,也在各方的推荐下,任了一些职务。彩墨画越来越多,用笔却不如从前圆润,更苦涩了一些。1975年,丰子恺在“文革”结束前一年去世。
在很多有关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书写中,丰子恺是缺位的,提得很少,甚至不提。研究中国艺术的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立文在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中没有提到丰子恺,但在详尽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弥补了这一空白;美国人柯珠恩的《新中国绘画》中也忽略了丰子恺;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香港学者高美庆,在其著作中把丰子恺纳入“卡通画”的部分,并认为他的作品只是“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在中国学者写的艺术通史中,丰子恺也很少占有一席之地。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错位现象,在大众视野中,丰子恺知名度颇高,他的画深入浅出,也很受人追捧,但进入专业视角之后,丰子恺成为了一个边缘画家。这不仅是丰子恺一人的尴尬处境,也是漫画之于艺术史书写的错位。
有关漫画,丰子恺在《谈日本漫画》中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漫画的发展都不如日本的热闹而且花样繁多。只有日本,大画家往往就是大漫画家,故漫画在日本美术史中非常活跃。他认为,日本漫画的发达是因为国民性,“那些身披古装,足蹬草履,而在风光明媚的小岛上的画屏纸窗之间讲究茶道、盆栽的日本人,对于生活趣味特别善于享乐,对于人生现象特别善于洞察。这种国民性反映于艺术上,在文学而为俳句,在绘画而为漫画”。丰子恺认可这种漫画与国民性的关系,但在中国,漫画始终不是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
丰子恺的绘画尺幅不大,风格变化也不够多样,这一点确实不太符合艺术史以风格流变为主要评判标准的价值体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通常一个画展中,参观者多是近看、远看,在展场中来回进退,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一件作品,但在丰子恺的展览中,无需如此费劲,墙上陈列的都是尺幅相当的作品,多是A4纸大小,只能近看,不可远观。这类漫画本就不是挂在展厅墙上看的,而是印在书中看的,即使是丰子恺晚期画过的一些相对大尺幅的彩墨作品,依然是小品式的作品。
但在张斌看来,她更愿意将丰子恺的绘画称为“诗画”,而非“漫画”。“丰子恺的作品非常讲究用笔,从一开始,他就是书法用笔入画,笔触的顿挫和变化在画中表现得很明显,这是他技法上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后来诸多‘仿丰画’中无法模仿到的精髓之一。”张斌认为另一个缺位的原因是,丰子恺的多重身份掩盖住了他作为画家的光芒。“他太丰富、太全面了,散文、翻译、音乐、设计、教育,他涉及到文学艺术的各个维度,且都做得很好。因此,他是画家,但首先是一个文人。”
然而,丰子恺的作品又不等同于传统文人画。如果说传统文人画家多避世,以山水、花木排解愤懑,抒发个人意趣,那么丰子恺的绘画则在这种情绪的基础上,更加世俗化,贴近生活。“他早期受日本绘画影响,浮世绘就是将世俗化与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种绘画形式。”张斌补充道,“而且民国本就是世俗化生活被文人津津乐道的时代,丰子恺生活在一个群星璀璨的文人圈中,成就了他诗画互相生发的独特风格。”
白杰明说,虽然丰子恺对普通大众抱着同情之心,予以来自知识分子的关切,但左翼阵营的成员很难把他视为同路人;而他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所抱有的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也使保守派不可能将他视为圈子里的一员。徘徊在左右之间,既不激进也不反动,再加上他传统与改良相结合的艺术风格,或许丰子恺只能被当作“第三种人”。无论世事如何轮转,丰子恺总相信“此境风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