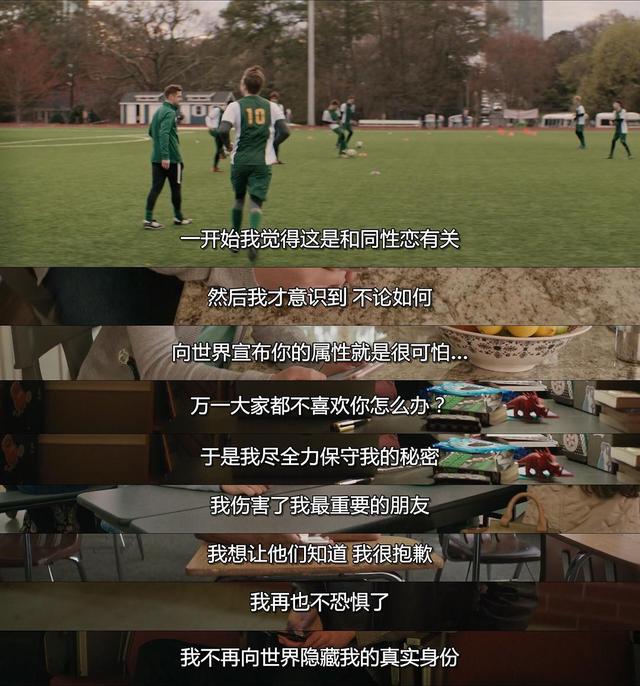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长春市,祖籍河北省盐山县,出身曲艺世家,祖父田锡贵是著名沧州木板艺人、父亲田庆瑞先说东北大鼓,后改西河大鼓田连元九岁拜王起胜(相声演员王佩元之父)为师,学唱西河大鼓兼练三弦,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长篇名家评书大全?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长篇名家评书大全
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长春市,祖籍河北省盐山县,出身曲艺世家,祖父田锡贵是著名沧州木板艺人、父亲田庆瑞先说东北大鼓,后改西河大鼓。田连元九岁拜王起胜(相声演员王佩元之父)为师,学唱西河大鼓兼练三弦。
童年时随父母浪迹江湖,1948年,定居天津咸水沽,上学读书时被“津师附小三分校”评为全校的模范儿童。读书五年,因父病,辍学从艺,没有获得一纸文凭。他靠借读同学的课本,自学完成了初、高中、大学的文科课程,并在学艺之暇,遍读名篇杂著开拓视野。
他曾经回忆他第一次登台演出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最永久的记忆。因为据他自己说,登台即告失败。
那天我坐在台上,身旁是父亲抱着三弦等候着给我伴奏。我用表面的镇静掩饰着自己的心慌意乱。我效仿着老先生开书前坐在台上的那种平静自然,成竹在胸的样子,实际我的心里在暗查着台下有几位观众——一共有9位,其实应该是10位,因为那一位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他只能算个未知数。他好像在等人,人来了可能一块儿坐下,也可能一块走。姑且不管他,我心里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我也得说的,这是我迈上专业的第一步,说好说坏听天由命,终于我开口了……
如今我已想不起来当时是如何说的,但有一处说错却记得格外清楚,那就是罗氏兄弟打抱不平,打死官军闯下大祸的时候,官府中人调集队伍,捉拿肇事者:“传令官手持令箭,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令字。”说出这一句以后,我马上意识到说错了,“斗大的令字”,那令箭应该有半拉门那么大了。但话已出口,无法挽回,更何况下面的观众有减无增,不断地“抽签”走人……
我的一场书说下来之后,台下还剩6个人。
我说完了这场书,如释重负……但我也得出一个结论,我干不了这一行。
下台往家走的时候,我把想法告诉了父亲:“爸,我干不了这一行。”父亲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干什么去?”
一句话问住我了,我真的无言可对。我能干什么去?我一无所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个最低的小学文凭都没有,我真的无路可走,但我心里却是想寻找自己能走得通的路。
父亲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接着便说:“别看今天这几位观众,他们没走,就是在欣赏你的艺术。”
我的妈呀!我的艺术!我连自己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记住说错了一句,还有什么艺术?我知道父亲这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怕我失去信心,其实信心已经失去了。
第二天,我仍然上刀山下火海一样,心里存着六十多个不愿意登台说书的理由。
至今我还记着在津南小站镇徐记书场,我的演出“盛况”。观众最多十五六位,最少的时候三四位……
天哪!我得改行!
想改行但无路可走
想到改行时,我马上就又想到一个人,这人就是父亲的师父——马立元先生。
当时马先生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编辑,曾编辑出版过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传》。一年前,我还在天津市内的时候,曾看到报纸上有一条“中国戏曲学校”的招生广告。从年龄学历上看,我有希望前去一拼,我曾提笔给马先生写过一封信,说明我是他徒弟田庆瑞的儿子,应叫他为师爷。我想考戏曲学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没多久,老先生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我的想法很好,为发展新中国的戏曲事业贡献力量。他表示支持,只是考期在明年秋季,届时你可到北京来,住在我家,我再与相关部门联系一下,到时参加考试就是了。
如今我见自己说书不行,忽然想到今年秋季就是“中国戏曲学校”招考的时候了,马师爷应该来信了,不能说书,我去唱戏。我打算写封信去催问一下,孰料,没等我写信,北京马师爷处的信寄到了这里。
还未开封看信,我已经十分激动,想着内容定是让我去北京考试。可打开信封一瞧,不是马师爷的亲笔,而是其女儿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马老于今年夏季突发脑溢血不幸身亡,全家为此悲痛万分,如今丧事刚刚办完,全家正准备带其骨灰返回原籍河北盐山下葬。
马师爷的突然去世,使我十分悲痛,也十分意外,同时我的一个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人生多少事,尽在难料中。
我并没有因此放下改行的想法。此路不通,尚有别路。不信我就非得说书。我把我的想法向我的好朋友范云倾诉。他对我表示同情,并表示愿意帮我寻找出路。
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范云对我说:“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你愿意吗?”
我一听,这是一个惊喜:“当然愿意,可我怎么能去啊?”
范云说:“我的一个同学在歌舞团里当指挥,从他那里知道民乐队里少个三弦伴奏员,我向他推荐了你,并说了你是专业艺人,基本功没问题,有识谱能力。他说,可以免试专业,到团里来试用一年,即可转正。试用期每月工资33元6角,如能行,即可来团报到。”
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每月33元6角,够你自己的生活费了,家里人呢?”
我哑口无言。此时我知道,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是和家庭的整个前途连在一起的,我的前途即家庭的前途,我的事业即全家的事业,但我说书没人听,就等于没收入,全家何以生存?尽管当时父亲与搭档合作还能维持生计,我将来能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吗?想到此,有时半夜暗流眼泪。
忽然有一天,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南京亚伟函授速记学校”有一条招生广告,言其校,函授招生,邮寄课本,半年毕业,便可掌握速记技术,有此技术可当记者,可当专业速记员,可找到工作……我犹如又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按其地址汇款寄信。半月后,果然收到函授课本一册,辅导材料一份。于是每月抽出时间认真攻读,并练习那些速记符号,怎么用几个符号代表一句话,以及字形与符号之间的变异……学得我头昏脑涨,出门转向,而且初期入门尚可,待到函授学校来函说老师定期要到天津市内某地当面授课时,我便傻了眼,我在天津南郊小站天天面对寥若晨星的观众,在煎熬说书。父亲怎么会让我去天津市内听函授速记学校老师讲课,他连什么叫“速记”都不知道。我就是说也无用,只好又一次作罢。
好像是老天爷看到我心灰意冷到了要绝望自杀的程度,怕我出事儿,于是当我们转换演出场地到了津西杨柳青的时候,我的说书情况便有了点起色。
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这段经历,并总结道:父亲说,说着说着就有人听了,这个理论很浅显,但是我后来想也很自然,是啊,非逼你说书你就得琢磨,你就得执着,你就得不能放弃,你就得研究它,英国首相丘吉尔,到牛津大学去做演讲,题目就是成功的秘诀,丘吉尔上去之后说了,说我的成功秘诀就三句话:第一,不能放弃;第二,不能放弃,不能放弃;第三句话,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不能放弃。
完了。我那个时候没辙,我也不能放弃,我就研究这个书得怎么能说好,我听老艺人那些人怎么讲的,怎么把人物能说好,把情节能说得让人爱听,把语言说得让人爱听,我就琢磨这些个事,在这个时候,辽宁的本溪市曲艺团问我愿不愿意入团,我说可以,我说前提是,入团你得让我说书,说你不是还会弹三弦?我说对啊,我说弹三弦是我的副业,说书是我的主业。入了团到团里边,安排我弹三弦,给一个女演员当伴奏员,我找那领导去了,我说“你怎么让我弹三弦呀?我是说书的。”
“哎呀,田连元同志,入了团就得服从组织安排,说书的人我们团里不缺,就缺弹弦的,你就弹吧。”我一看行啊,弹吧,弹了一年多,然后那主演跟我搞对象了,我一想这可能是天意,弹了一年多,弹出个媳妇来。但是说书的意愿没有结束,我要说书,结婚以后了团里面有一块空地,就是有个场地没人去,因为晚上演完了,那个演员得骑着自行车自个儿回来,没有公交车,我一看机会来了,我说我去。就这么去了,把我多年来积累的胸中的这些东西我都展示出来了,到那一说,火了。天天满座。
我当时就想,我在偏远地方我能说书说火了,没人知道啊,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到了1965年,辽宁省搞一个曲艺汇演,我创作了一个段子,叫《追车回电》短篇,我这一说,一个段子说完了,底下掌声骤起,把我自己吓着了,我说敢情这玩意儿能火啊?在这儿火了,全省火了,哇的一下子大伙都认识我了。中午吃饭一进食堂,我就觉得多少双目光投奔向我,“就这小伙,就这小伙。他说的挺新……”所以艺术创作,有很多东西是始料不及的。
而这位弹出来的媳妇就是刘彩琴,当时是团里的主演,关于他们婚事可是因为吵架吵出的情缘。据田老回忆:记得1960年的中秋节,我和往常一样按照晚7点演出时间提前半小时赶到第三曲艺社,做好了演出前的准备,眼看观众们陆陆续续地买票入场,场内已经客满,时钟也指向了7点,可刘彩琴却未露身影,这是我与她合作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她从来都是提前10分钟赶到书场,稍事休息,即登台开书。今天到点儿没来,我想不出会是因为什么,19:05没到,19:10仍未到,观众席里开始议论:“刘先生怎么今天还不来?”“到点儿了……”
我沉不住气了,告诉现场服务员把情况速向团里汇报,我则疾步奔向她家。
她家在北山街的一个高坡上的木板幛子后面。当我顺路转过道口看到她家的木板幛子时,见木板幛子内聚集了不少人,我快步走上高坡,直奔她家的院门。
刚走到院门前,忽见她家的邻居老徐从院内走出来挡住我的去路,说:“连元,你千万别进去,彩琴家里吵起来了,你要进去会更麻烦,你站在这里,等他们矛盾化解一下再说。”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停步,只听见院内一片吵嚷声,其中也夹杂着刘彩琴的声音,未等我想好是进是退的时候,忽见彩琴疾步走出院门。她显然已经化完了妆,但头发却是蓬松着,有一绺头发斜散在面前,左手夹着一床棉被,被角在地上耷拉着,那样子看上去很狼狈,她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带着怒气,当她看到我站在面前时,脱口说了句:“连元,咱们走!”
我来不及问为什么,只得遵从命令似的拿过被子,同她一起走出来,把她送到曲艺团的女单身宿舍。
宿舍里别人还没回来,于是我便问她因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
她稍平静一下情绪说:“今天我化完妆,准备要走的时候,想起我有一件男式蓝料子中山装上衣,那件衣服你穿了肯定合适,因为我穿着有点大,我在柜子里翻,怎么也找不到,头两天还在柜子里怎么忽然就不见了,我妈问我找什么,我说找我那件衣服,男式上衣,我妈说你找它给谁,我说我穿,我妈说,我知道你是要给那个田连元穿,我说是啊,怎么的,我妈说,你甭找了,我把它收起来啦!我还留着给我儿子穿呢!我说你儿子还没长大呢,他穿不了,我妈说,给谁穿也不给那个田连元穿,搞对象应该他给你买衣裳,你倒好你送给他衣裳,倒贴呀!
我说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接着就吵起来了,她说我和你搞对象她不同意,我说婚姻自由,最后越吵越厉害,我说要走去演出,他们竟让我把值钱的东西都放下,一把把水晶项链给扯断了,我喊我爸,他也不管,我说我走,他们说,走就永远走,别回这个家,我就扯过我盖的那床被子,夹着出来了,出门就碰上你了。”
一席话说完,我心中不知什么滋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心中暗自在想,今生我以“永对你好”报答你“被逐出门”。我没有当面表白,因为我认为说出来的誓言是给别人听的,自己的誓言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我问她:“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她回答很干脆:“我就在女宿舍住了,明天继续演出,不能耽误了团里的事,这个家我是不回了,我上食堂吃饭。”
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劝她,我只能表示,今后我会尽我之力关照她。
到了第二天,我们两个继续去书场演出,观众继续满员。演出完毕,我送她回女宿舍休息,我则回我的男宿舍休息。
我觉得这件事团里领导应该是知道的,如知道必然会有个态度和办法。但时间过去了三天,一切如旧。
第四天,团长、书记分别找我们两个人谈话,问我们相处了多长时间,互相印象如何,愿不愿意成为一家?
当我回答愿意的时候,接着他们便说:“愿意就结婚吧!由团里出面为你们操办,结了婚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搞业务啦!”
我说:“我们原定计划是五年之后再结婚。”
团长说:“早晚结婚都一样,现在彩琴和家里闹成这样了,她一个大姑娘在外边住,各方面也不方便,你们俩结婚后团里还有新房,给你们一间,算是解决了你们的终身问题。”
我一时没了主意,只好说听听彩琴的意见,团长说:“她也同意,定个日子就办吧。”
我想她同意我也就同意呗。
于是双方与团里商定10月12日举行婚礼。
我们两个都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团领导干预得太热情。我们的“五年计划”化为泡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