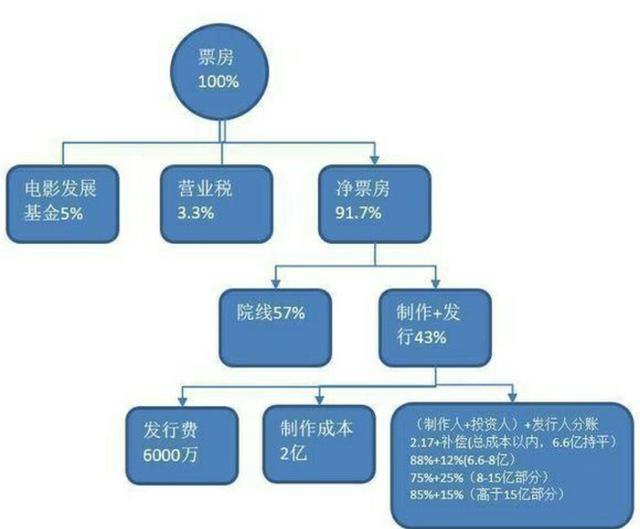“我三十几岁时不慎运动扭伤,得了较为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虽然不是癌症、艾滋病之类的不治之症,但也耗费了我不少精力。为了摆脱椎间盘带来的疼痛,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去修理这几节不争气的骨头,可谓历经人间沧桑……”
这是作家黄毅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疼痛史》后记中的一段话,介绍了这本书创作的缘由。从本书开篇的《疼痛的缘起》开始,我们进入了作者肉体疼痛的体验,先是青年时期的腰,因为一次“卖弄”般的运动示范,“好像被分成了两部分”,从此,“彻骨的疼痛犹如晨钟,在我的体内铿然訇响,余音袅袅,经久不散”。接着,是作者长达十几年的各种医治过程,“病急乱投医”的各种治疗,推拿、牵引、气功、复位、拔毒、“麦肯基”、火针……无所不用其极。
肉体的疼痛还没有治愈,这期间又有了“心痛”——从《父亲》一文开始,先是大哥,然后是母亲、父亲的相继去世,还有诗友,文学老师、中学老师、少数民族兄弟,噩耗不断传来,好像现实生活一层层地淤积着沉甸甸的岁月泥沙,让我们的呼吸也粗重起来。
我要说,黄毅的这部《疼痛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元素的散文集,是他近十几年来思想观念、审美形式上的进步与蜕变。是他在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怀疑中,不断地进入了解自我、正视自我,试图摆脱人生困境的努力,当然也是他自我意识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黄毅诗歌散文的主题演变。
很长一段时期,新疆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诗歌和散文,主题大多描摹西部时空的奇崛物象,或抒写多民族生活风情,或深入西域历史文化等,我们可以视为区域性群体写作的共性。黄毅曾经是新疆优秀的诗人,代表性散文作家,以往诗文中大多是对新疆大地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的抒情性书写,其中充满奇思妙想的、富有智性和想像力的诗意。这也是他能够在这种带有公共性的符号化写作中出类拔萃的原因吧。我当年在读完他的散文《新疆四季》后写下的随感中说:“阅读这样的美文令人愉悦:智性、诗意,连绵不断的的生动具象,微妙的生活细节、丰富的想象。但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对于事物“变化”的专注与敏感。散文中常常对某些细微的、局部的事物特别留意,这些不被常人注意的、容易被忽略的“微生物”,经过他的定格与凸显,会发生使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虽然,这些艺术作品体现出的是大真,大美,但它只是我们现实社会的一个向度。它代表的只是新疆前现代阶段的文学状况,是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传统意义上的“古典世界”。正如一位作家描述的:“古典世界是一个静止、凝固、重复、节奏简洁的永恒世界,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尚未破碎的“乌托邦”世界,一个业已消失的典型的农耕文明世界。在那里,人的整体性与自然或世界的整体性合而为一,彼此认同、相看两不厌,拥抱在一起;在动植物身上可以感受到人性,在人身上可以看到植物性和动物性”(张柠:《节奏与精神秘密》 见《十月》2009年06期)。
现实社会还有一个向度,就是是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的巨大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古老”的新疆大地节奏的整体性逐渐散裂,或者说,现代生活摧毁了古典诗意发生的基础,人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空前的改变:时空被速度压缩;熟悉的事物逐渐消失,陌生的事物纷至沓来;游牧生活和绿洲文明社会靠血缘关系为纽带,把熟人维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也在剧变……
这就是人类文明在告别前现代而进入现代过程中所创造和洐生出的新的状态和特性。现代精神,简言之就是现代同传统的断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有关社会、人的现代性略过,单说文学,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脱离了宏大叙事、集体自我意识的束缚,实现了个人经验的自觉,创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第二、从审美意义上说,是指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上的革命,是从二元对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功利性,进入揭示人性的复杂性的艺术审美方向。
一位作家现代意识的确立,好像随着骨头越来越严重的变形,以及亲友的逝去,实际上是急速变化的世界,让这个对于事物“变化”专注与敏感的人捕捉到了。有强烈的疼痛感了,说明什么,岁月无情,人不再年轻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想想作者的过去,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骨头的妙响》,是青春年华的体验,那时候骨头发出的声音,是妙响,是鹰笛在高原悠扬动听地吟唱。虽然,这是朋友开的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但却是一个时代的抒情气质和艺术象征。
如今完全不同了,新书中的这一批散文,从“病痛”这个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的实际上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人生困境。作品摆脱了区域性群体写作的共性,直接进入“病痛”这个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些病痛有肉体的,精神的,肉体与精神交融的,更有失去亲友、老师的,人生艰难岁月的,面对复杂社会的人性的。《我是一块儿仙人掌》中有这样一段精彩之极的描述:“那一天,我的身体从背脊一直延伸到大腿小腿,一共扎进了一百四十七针。趴卧在理疗床上,我就像是一块儿仙人掌,或者一只刺猬,背负着满身的尖刺,而我的刺不是用来防备外来的攻击,我的刺全部反转深入我的肌体,那一刻我开始理解,植物的根须穿刺泥土,是为了让枝头的树冠更加葱茏。”
幽默调侃的笔调,蕴含的是茫然、无助、迷乱,甚至还有荒诞、焦虑。文中的“诗意”仍然富于想像力,具象微妙而生动,但如今“立场”变了,心态变了,文学的关注点变了,变成关注平凡生命的个体,关注自身和内心的冲突,而不是那些“神奇的”“神性的”审美内容了。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是一个“从神到人”的过程;基本原理: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
在《疼痛史》中,《酒殇》是一篇长达数万字的长散文。曾记否,“美酒”对于游牧民族,从来都是欢乐、豪爽的象征。“酒殇”的“殇”,是挽歌,是一个生长在新疆多民族地区的“壮族人”,对“酒”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的疑虑和反诘。可以说,这又是关于一个民族的“疼痛史”。其中关于草原帝国的历史考证,探寻那个曾经激情四射、豪气盖世的民族
兴衰的原由,以及酒对某些民族,个人命运的影响。
文章中还叙写了好几个才华横溢的民族兄弟因为饮酒的不幸,巴登、阿木尔的早逝,老那的失落,令人痛惜。文中一个个关于“酒到底是什么”“酒能改变什么?”的天问,流溢出的内在悲剧性和孤独感,正是的典型的现代精神气质。
《疼痛史》全书中,交织着疑问、挣扎、企望、追求的多重心态,表现事物和人性复杂多面的精神世界,都显示出这部新作可贵的艺术创新能力。可以预见,如果一位作家在直面自己的内心方面体验越深,生命的境界就会越扩展,人生与世界的理解就会越有深度,也就越能创作出更加优秀的艺术精品。
我十分期待黄毅再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胡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