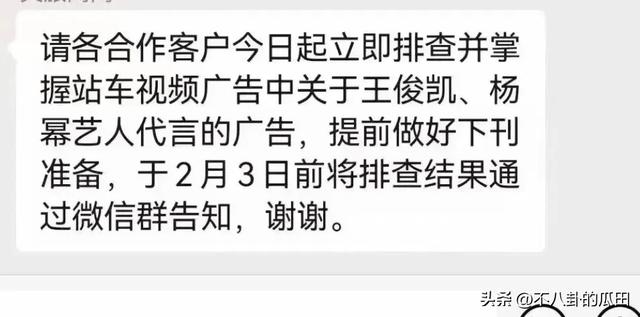始建于1927年的建设大路是沈阳市铁西区南北分界的中轴线,也是南五马路越过铁路向西的延伸线。1931年以前,铁西是一片耕地分散的自然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侵占了沈阳,成立了伪奉天市政公署,1934年6月《西工业区平面图》制成。当时的规划是东起安福街(原第二纺织厂西侧马路),西至嘉应街(现兴华大街),南起南五马路(现建设大路),北至中央路(现北三马路),在这个范围内有46家工厂确定了位置筹备兴建,这是铁西早期的建设规模。在此之后,铁路以西的这段南五马路就被日本人用日本宫崎县北端的名山“高千穗”命名为“高千穗通”。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它才取建设工业区之意命名为“建设大路”。20世纪,建设大路见证了铁西区“南宅北厂”的格局。当时铁西区以建设大路为界,南面为居住区,北面多为厂矿,3条铁路线贯穿于各个厂矿间,并错综复杂地汇入沈阳站。每天的上下班时间都有巨大的自行车流往返于建设大路南北两面,勤劳的工人们不停地推动着工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铁西区的改造,铁西区北部大批企业迁出,“南宅北厂”的格局消失了,建设大路也不断地扩建,延长到东起南五马路公铁桥、西至重工街4公里的长度。它依然在忠实记录着铁西区的变迁与发展。
建设大路在铁西区横贯东西,如果把铁路看作铁西区呱呱坠地的地平线,那么建设大路就是支撑起铁西区的脊柱,有了它的存在,才有了躯干、四肢以及毛细血管。不过,这一具曾经生机勃勃的肉身,从孕育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离不开脚下的那条地平线。

1910年的铁西
铁西,顾名思义,就是铁路以西。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建设受铁路的影响之深。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沈阳的杰出代表,曾经被称之为“共和国工业长子”“东方鲁尔区”的铁西区,在20世纪下半叶度过了最为辉煌的时代,在“一五”(1953-1957年)和“二五”(1958-1962年)时期,新中国将全国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在这里,大量资金政策人才汇集在这里,这里也为新中国贡献了100多个工业“第一”,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实力,不是钢筋水泥堆砌的房地产,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实力,是国家发展的脊梁和肌肉。同时,领先全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的工人村,往来于厂区与住宅区之间潮水一般的自行车流,都是铁西区曾经光彩夺目的名片,在几十年间都是全国人民艳羡的对象。
1910年是清宣统二年,那时奉天古城外围的区域还不叫“沈阳县”,而叫“承德县”。那时候的铁西基本保持着几百年来的格局,各个屯子都还在,虽说铁路已经建好,火车已经开了进来,但当时任谁也不会预想到这片土地上后来发生的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片开阔地,怎么就变成举世闻名的工业区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两个字:铁路。没有铁路,就没有铁西。不论现在的铁西给人们的观感是什么,它都摆脱不了自己身上最初的烙印,透过这些烙印,后人清楚地看到铁西的前世今生。
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以南、南十东路以北、兴工南街以西、云峰南街以东的地区,在明清两代叫作“揽军屯”,是盛京西经辽中进北京的必经之路。明代沈阳中卫在这里驻扎军队,招募兵勇,揽军屯由此而来。清代,揽军屯和附近的艳粉屯、路官屯一样,都归镶蓝旗主、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管辖。当时老百姓还给揽军屯起了个别名叫“大墓”。因为这里有一座占地面积巨大、建造规格很高的坟墓,里头安葬着努尔哈赤的爱将、清开国元勋安费扬古。20世纪初,揽军屯的工商业逐渐兴起,到1935年已有工商户332家。当时揽军屯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百业兴旺,一片繁华景象。九一八事变之后,包括揽军屯在内的铁西地区被规划为奉天西工业区。随后,满铁株式会社与伪奉天市公署共同出资伪币350万元,强制收购规划地内的村屯和土地,然后出售。揽军屯此时被日本人规划为他们的生活居住区,原住民、工商业户以及学校被迫迁往景星、兴顺街一带,原来的揽军屯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日式建筑。从此,揽军屯就从铁西版图上消失了。直到1989年,沈阳市进行路名整顿,将南滑翔路南侧、铁路北侧的马路定名为“揽军路”,算是给当年的揽军屯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要说铁西的历史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非常悠久,年头也长,但是对现代城市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曾经的活动痕迹得以保留下来的也寥寥无几;第二部分相较前者,从时间范畴来说几乎不值一提,最多也就一百多年,却基本奠定了现在的铁西格局。如果把第一部分归结为农业文明,第二部分归结为工业文明,那么使两部分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就是铁路。
1958年,当时隶属于铁西行政管辖的郑家洼子挖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族部落古墓群。到1988年,铁西已经挖出了41座,直接把铁西地区的人类活动史推到了2700年前。不过,铁西肥沃的黑土地还是那片黑土地,黑土地上的人类活动史自春秋战国以后却出现了断层,铁西在文献或者考古方面再次登上舞台就直接到明清了。大部分人把这个时间点人为地设置在了明末清初,认为明代沈阳中卫城的周边人口并不绸密。明末的时候,随着努尔哈赤的迁都,沈阳城及其周边地区才一下子热闹起来。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即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后,把沈阳城外的土地分封给了八旗旗主,城西一直到老边大道以南区域封给了镶蓝旗,旗主是努尔哈赤的侄子、郑亲王济尔哈朗。现在的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的丁香、红旗台、宁官等村镇都属于镶蓝旗管辖,而距离城区相对较近的揽军屯、路官屯、艳粉屯等都是郑亲王府庄地。前些年在云峰街还出土过一块“郑亲王府园寝”的石桩。
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克沈阳之后,沈阳古城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城西部的屯、堡有增无减,但已归入镶蓝旗下,接受了新一套管理系统。紧接着的200多年里,这里按照自然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前进,直到工业社会破门而入——铁路建成了,火车进站了,铁西开始全面发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