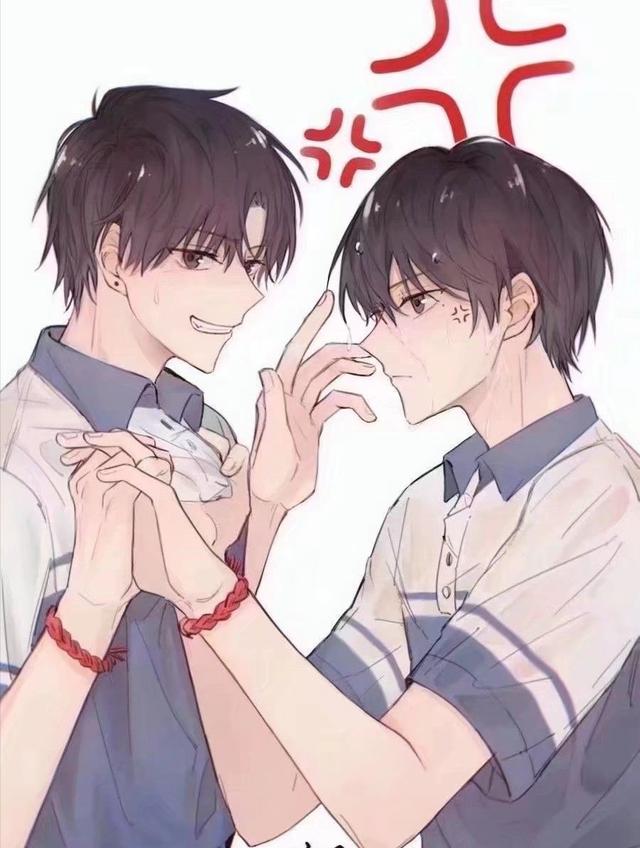作者|朱良启
我对过中秋节不怎么感兴趣,有时甚至觉得过节是一种负担。不是我不热爱生活,相反,我很热爱生活,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对待,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业余时间看书学习,与朋友交流探讨各种问题,不曾虚度岁月。
之所以有这种心理,应该与我青少年的生活经历有关。那些逝去的中秋节在红色的喜庆里总夹杂着一抹或浓或淡的灰色。

我经历过的五十一个中秋节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变的是过节的时间,变化的是过节的方式。从幼时到初中毕业是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处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农村很穷。
我是住在家里,每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相近,都是赶在一年中秋收秋种极繁忙的时间段。在过节前,父母会抓紧走完该走的老亲戚,或自己走一趟,或分派我们去。也没有什么珍贵礼物,一般四斤月饼是标配,或者加点水果。
淮北地区风俗,亲戚要往来才有亲情,长时间不走动便不亲了。所以中秋节和春节一定要看望长辈,对方留饭把礼物再回一半即可,不需要回访。这件重要的事情办好,便可以集中精力忙秋收秋种了。

在我的印象中,一年中秋季是最忙最累的。春天可以只种不收,夏季收过麦子即可种玉米大豆,无需翻地。但秋天需要收的庄稼太多,豆子芝麻要割,绿豆杂粮要摘,玉米要掰棒子、砍秸秆,红薯要刨出切片晒干。
所有的土地收完庄稼后都要施一遍农家肥,然后犁地,才能再播种小麦。这些农活要连天加夜干完,怕损失,怕变天,豆子玉米只要被雨淋两三天就要生芽子。那是农村种地全靠人力,畜力。全家上阵,死命地干。
白居易在《观刈麦》中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其实秋收之忙甚于五月。那时也没有中秋节假,学生请假也得回家帮忙,没有收成就没有钱。家家指望卖掉秋粮得到一笔收入呢。每天要从天麻麻亮干到月出东山之上。人极度疲劳时便不再奢想浪漫,没人陪你矫情。累极了,只想干完活能歇歇,早睡一会。

中秋节这天白天和往常一样忙,村里并没有过节的氛围,中午也和往常一样,但晚上一般要多炒几个菜,菜是自家菜园随意摘的,还要杀一只自家养的公鸡。
月饼或是买的,几块钱一斤,一斤有四个,或是自家做的,主要是糖和面,再加些芝麻香油的混合物,小时候我们每人可以分两块月饼,一两个苹果和梨子,在零食很少的情况下,孩子已经很满足了,当晚并不舍得吃完,要吃一星期左右。

至于现在流行的什么水果月饼、豆沙月饼,什么苏式、广式、秦式等等月饼,只在报纸上见过。还有传说中几十元几百元一斤的月饼,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不知道,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父亲给我们讲过嫦娥奔月的故事,我感觉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女人,家里的活不干自己跑天上潇洒去了,也许是她干累了逃离的吧?至于中秋节的来历,淮北地区的传说是“八月十五杀鞑子”。
元朝时期,汉人苦于被外族统治,剥削压迫太甚,平时汉人家中不准有铁器刀具,连菜刀也被收走,只有做饭时才发菜刀。于是汉人秘密串联,相约于八月十五这天一起举事,消息写在纸条上塞进圆面饼里一家一家传递下去。
终于这天饭后汉人不再上交菜刀,而是举刀相向看管他们的异族。推翻元统治者以后,为了纪念此事,汉人要在这天吃圆面饼表示不忘根本,因为圆,遂称为“月饼”。

我上高中和大学一共七年,在这一阶段,没有在家过一次中秋节。这期间仍然没有专门的中秋节假,连双休日也没有,而学校是正常上课的,全部在学校过的。
最多是在距离中秋节前最近的那个周日回家,帮忙干干农活(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依然累,但劳动强度没以前那样大,父母不愿意耽误我们的前程,尽力自己多干),吃顿好点的饭菜,走时带几块月饼就算过节的意思了。
到校以后,在中秋节当日晚上,学校领导如果仁慈的话,在公共礼堂会用电视播放中秋晚会。不过看看电视台里的歌台暖响,豪华奢侈,阵容庞大的中秋节,再看看眼前我们自己寒酸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中秋节,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处在同一个人间。

第三阶段始于1994年,那年7月我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离家十几里远的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一来能拿工资了,二来我和两个姐姐的承包地被生产队调整土地收回。
家里还有土地,但减少了许多,加上家里有了拖拉机,人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劳累,日子开始过得轻松了不少,此时的中秋节有了过节的样子,干活可以早早收工,人能团聚,吃喝丰盛了许多,作为成年人,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喝酒,父母不再禁止。
只可惜我母亲于1995年元月去世,此后几年,没有了母亲的中秋节总是显得冷清,物质再丰富也使我们总感觉索然无味,几乎都是草草应付。后来家里姐妹先后出嫁,家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更是冷清,父亲还是要为过节做些准备的,我是一点过节的心情都没有,敷衍着吃点东西了事。
我心里清楚,曾经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在一起过节的日子连同我的青少年时光一齐永远消失了。以前穷,可全家对未来充满希望,齐心协力过日子的场景还是令人留恋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人却散失了。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最后一个阶段,1997年10月,我结婚后离开家,住到妻子学校,后来在淮北市里买房住进市里。国家重视传统文化,中秋节也有了专门的假期,我们也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物质,妻子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对过年过节很是注重仪式感,连周六周日都要好好过一番,对中秋节这样的假日更是不能放过,鸡鱼肉蛋自不用说,大闸蟹之类的东西也一定要有;各种月饼都要买来尝尝;水果不再只是苹果梨子,还要有哈密瓜、火龙果、猕猴桃等等。
两三人她也要整满一桌子饭菜,她的口号是:“过节就要有过节的样子!”有时看着满地的吃喝东西,我都为专门消灭它们犯愁。饭后我们一起去空阔之地赏月。比起我的青少年时代,彼节于此节已不可同日而语,物质,丰富充裕,精神,轻松悠闲。
但吃着眼前的美食,我眼前却老是浮现出一幅场景:在余威依然存在的秋天骄阳之下,一览无遗的庄稼地里,一位少年抬起略带忧郁的脸庞,直起酸痛的腰杆,抽出已经肮脏的毛巾擦抹掉满脸的汗水,望一眼满地的庄稼,稍微停顿之后弯腰又奋力大干起来。临近正午,村边传来母亲悠长的喊声:“回来吃饭了,今天过节,早收工一会——”
作者简介:朱良启,毕业于安师大中文本科,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淮北七中。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淮北市作协会员,烈山区作协常务理事。先后有三十多篇作品在省市区获奖。在《青年文摘》《新安晚报》《安徽青年报》《市场星报》《淮北文史》《淮北日报》《淮北矿工报》《淮北广播电视报》《相城》《立根》《濉溪文艺》《烈山文化》等省市报刊、网络媒体发表文章350余篇,百万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