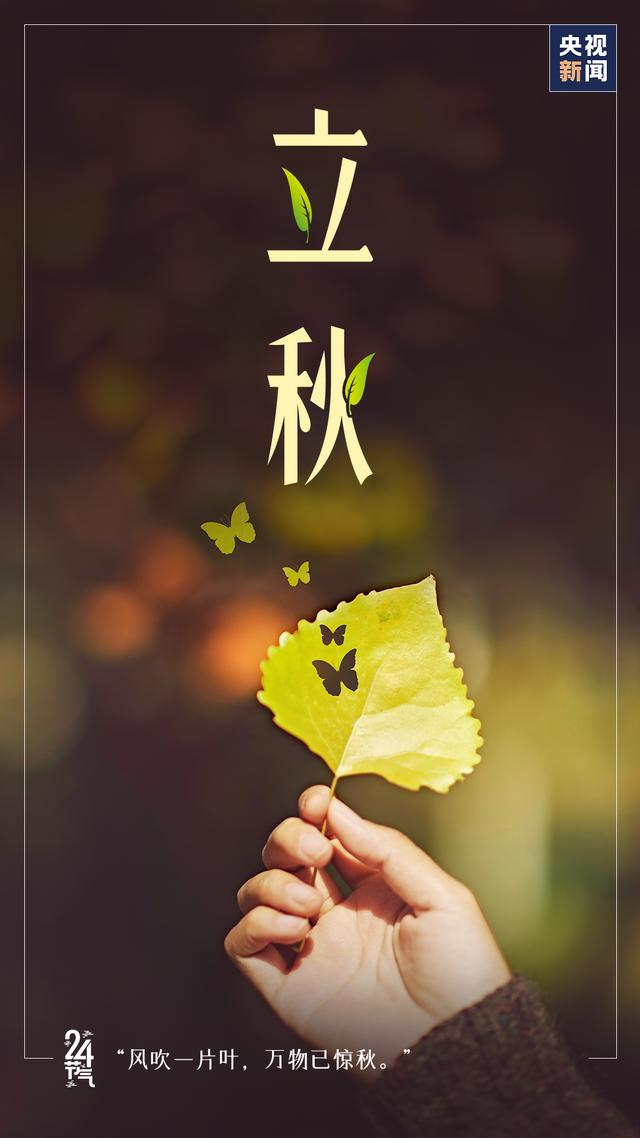原标题:姜各庄渡口的变迁
作者:张淑艳 孙绍棠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 乐亭故乡人网站(www.guxiangren.com)
题图来自网络,同本文无关

在没有火车、汽车等先进运输工具的年代,水运是主要的运输通道。在滦河下游,每隔三五里地就有一个渡口,由于河道来回摆动,所以摆渡也不固定。
姜各庄渡口大概形成于元末明初,据《昌黎县志》记载:“姜各庄渡口就曾在少佛林、拗榆树、大滩、莲花池等多处变换。是滦河下游的古老摆渡口,也是连接昌黎和乐亭两县的交通要道。”渡口不只是为两岸村民相互交往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姜各庄镇及其周边各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渡口上最早的渡船是由“会上”建造的。(“会上”是建村后村民的自治组织)。渡口的船只和设施村民一直认定是共有共用的公共财产。姜各庄渡口最大的特点是不收费。解放后,两岸的姜各庄、拗榆树等村村民过河也不用交费。摆船的工钱是每年完秋后一次性发放,故称为“秋俸”。所需钱粮是每年粮食进仓后由各有地富裕户自愿捐送粮食,在外有买卖的富裕户则捐送银钱,多捐不嫌多,少捐不嫌少。此外还有一些经常过河的巨商富贾和其它大户,专门指定为渡口捐赠钱粮。合作化时期,由生产队给一些粮食作为报酬;到了年底,邻近的大队也给些谷子、玉米等。按照乡俗,正月里过渡的也给些小钱,几分几角随意,没有就拉倒。平素有办红、白喜事的从渡口过,也会主动表示下意思,迎亲的大队人马上船,新郎官也递上点儿喜钱,喜烟喜糖。摆船的代代相传,收入稳定有保障。
建国初期,滦河里水很多。最美的是春水和秋水。夏季的夜晚流水的哗哗声,像奇妙的轻音乐。可一到发大水的时候,巨大的滦河涛声仿佛穿越了天空和大地,覆盖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的摆渡小船,春夏秋都行走在滦河里。每到黄昏时分,又圆又大的落日,映红半天云霞。很多河鱼不停地跳出水面。人们快乐的欢呼和笑脸,像和鱼们在河面上一起飞翔。
近年,滦河河道里的水少了,沿河村民便在河道两边的沙滩上垦植农作物。地方政府还组织人们在河滩两侧栽上了杨树,形成了万亩杨树林。
历代渡口的渡船和摆渡方式是随着河水的流量流速的不同而改变,根据不同的季节和需要配备有大板船、二溜子船、小溜子船和水笸箩。大板船是将两侧船帮用木板封死,密封严实不渗水,船头和船尾向上翘起,整个船体是空心实体,即使是河水漫过船面也不会沉入水中,除能摆渡二、三十人以外,主要是用于摆渡车辆。满载货物的骡马大车,可以不卸车就能直接赶牲口上船,若摆渡载货大汽车往往是将两艘大板船用煞绳捆绑在一起。若摆渡一两个人或三五个人,则用小溜子船或二溜子船。“溜子”即是梭子,是方言俗语,其外形如同织布用的溜子而得名。水笸箩是用柳条编制而成,里外涂有一层桐油,比盛粮食的普通笸箩大一些,四周的帮高出很多,能坐一个人。它的用途是滦河涨水有洪峰大浪渡口封船后,可供水性好的村民有急事到对岸去,抗战时期民兵们多用它渡河传送鸡毛信。船上的动力设备:船尾有舵或橹,船身两侧设有成对的棹(桨),每艘船上都备有杉木竿子(篙),大船上还有桅杆,可用绳索升降大蓬(帆)。春秋两季水浅时用竿子撑船,夏季水深船竿子够不着河底时则搬棹使船前进。每逢干旱年河道较窄时,便在渡口两岸各立一个木桩,用虎口粗的大煞绳将两个木桩连起来,过河时人在船上用两手倒绳子使船前进,名为“倒綆”。常言道“十竿子不如一棹,十棹不如一橹,十橹不如大蓬一鼓”。蓬帆省力速度快但很少使用,主要是用于出远门。用小溜子船倒绳子渡河时,摆船的可以不上船。
过渡有过渡的规矩,比如,最后上船的那个人要划前桨,那人是老人、孕妇或太小的儿童,也会有人替一把;第一个离船上岸的人,不能毛手毛脚自顾自,要将固定在船头的铁链顺手带上,将铁链上的铁钎插牢在硬土里,方便后面的人上岸。如果猫弹狗跳,在船靠岸的一瞬间纵身一跃,船倒退好远不讲,船上的人还会猛然间失去平衡而东倒西歪。“同船过渡,五百年前所修”,这是缘,乡亲们都懂。
渡船也渡牲口,过渡最多的是牛,有时一头有时一群。但牛不能上船,只能泅水,由牛主人在船上牵了领头的缰绳。善泅的牛往往会泅在船前头,帮一把力,牵着船前行;不善泅的就拖了船的后腿,牛主人拿鞭子吓唬它或真的抽它一下,它就会攒劲泅。牛天生会泅水,未下过水的小牛见母亲下水,也会硬着头皮颤颤惊惊跟着,一旦四脚离地,它就自然而然地浮在水上了。
在渡口,大伙儿都是过客,匆匆地来匆匆地去,短暂相逢,然后各奔前程。滦河两岸的人民自古就有联姻的习俗。儿时在河边上玩耍,常常叠个小纸船,放在河面上,让它顺水漂流,我们则在小船后面叫喊着:“小溜子船儿啊,摆河南儿哪!”谁的小船漂得最远,就预示谁将来要嫁到河的对岸去,此时伙伴们就大声喊“嫁过去了!”“嫁到河南儿去了!”
俗话说:“隔山不远,隔河不近”。山路再难走,总有走到头的时候,而隔着一条滦河,虽然对面看见自家的烟囱,没有船,也只能“望家兴叹”,尤其是河滩的沙路更难走。1994年7月2日,由于中考工作紧张,笔者(张淑艳)母亲病重,自己却未守在身边,中午突然家中来人说母亲病危,急忙坐上来人的摩托车往回赶。到了河边,新建的大桥尚未合拢,只好坐船过河,可是沙滩路难行摩托车老熄火,只好推着摩托车前行,半小时的路却走了近两个小时,到家时也未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成为终生的憾事。1979年夏,滦河发大水,摆渡一天只走一个来回。有一次笔者在渡口等了近一整天,终于坐在船上。面前河水急流汹涌,波涛滚滚,真让人胆颤心惊。渡船从北岸一出发,就被激流冲到东边5公里处大滩的马良子村南,船工们有的急忙升起风帆,有的在船的两边使劲的搬棹,(杆子已够不着河底不能支了)紧张地奋战了近一个小时,人人大汗淋漓,才把船掉头沿河西上。一船人坐在船舱里大气都不敢出。
坐船的不能说“翻、沉、害怕”等不吉利的字眼,不能乱走动,以防重力不稳。
坐船险,等船更烦。有时候有急事,眼看到码头了,可是船却开走了,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看到船在对岸,就得站在河岸扯着喉咙喊,岸那边的人听得见才会来接;有时候坐在船上,你催得再急,船匠们依然不紧不慢撑篙。有时碰上急事,码头上船已离岸,只好大声喊:“等等我!”那就让船匠为难了。不掉头吧,听那声音蛮急切,像是耽误不得;掉头吧,不光一船的人心生怨气,对岸的眼巴巴望着船掉头,也免不了骂骂咧咧。俗话说:走路怕撒尿,行船怕打掉。“打掉”是掉转船头的意思,船掉一下头,会要耽误好多的行程。
碰上风平浪静,急着过河赶路的人多,船头船尾会挤满了人,没上船的拼命往上挤,上了船的死活不肯下来,哪怕船沿压得离水只剩两指头宽的边。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冬季大雪节气前后,河流开始结冰。即便是气温偏高的年份,到了大雪土地也要封冻了(但也有“小雪封地地不封,大雪封河河无冰”之时)。这时节滦河河面夜间冻一层薄薄的冰,白天太阳一晒就化开,上游大块大块的冰化了就冲到下游,本地的说法叫“发冰排”。发冰排时巨大的冰块好像一块块水晶,在水中上下浮动着,时而露出水面,时而沉入水底,时而一泻千里,时而又出现冰塞、冰坝。有时河中的冰块、冰花占河水的40%还多,排山倒海涌来,相当壮观。
这时节渡河非常危险,渡船有被冰排卷走或冲翻的可能,所以渡船就停摆了。可是河面又没有冻结实,跑冰过河更危险。两岸交通几乎断绝。1987年初冬,笔者家中建了新房,母亲想到我家来“暖房”,一连三日到码头上,因为冰排严重,渡船不敢摆渡,等来等去也过不了河,直等到11月底才跑冰过河完成了给我家暖房的心愿。
封河时节,河道上结出厚厚的冰层,滔滔流动的河水一片宁静、凝固的世界,河面变成了镜面,泛着熠熠光芒。数九寒天河水封冻以后,行人车辆可以从冰上直接过河,俗称“跑冰”。然而船工们仍很辛苦,他们把船只拖上河岸检修。冰面封实以后,选择坚固的冰面作为冰道,撒上一层沙子,以防行人、车辆打滑摔倒。除最寒冷的暴风雪恶劣天气外,渡口总不断人,一边检修船只,一边引导人们从冰道上“跑冰”。因为滦河有的地方水深流急,冬天也不封冻。所以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跑冰过河的。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八九”后,气温回升。大雁结队飞回觅食,这时河里的冰已经开化,上面厚厚的一层冰,底下流水哗哗作响,冰面裂开条条大缝,冰看上去很厚,但却是酥的,禁不住重量。有时白天冰开化了,晚上又冻上了。在滦河的岸边冰化后就形成一条小溪流,叫“沿凌水”。而河中间的冰还没有化,不能摆渡。怎么办?船工们在水狭窄时就搭个跳板,有时跳板够不着,人们只好淌过这条沿凌水再跑冰过河。
有一句俗语:近道怕鬼,远道怕水。说得有意味,有哲理。因为本地人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黑夜行路怕这怕那,而外地人对地理环境生疏,不知什么地方常见鬼,无知无畏,自然啥事没有。至于说到远道怕水,那也深有道理。因为河道深浅,有无漩涡暗洞,外地人皆不知,贸然下水,必定凶多吉少。
滦河封河后有的地方水深流急,不结冰的湍急水流称为清沟,结冰不厚不结实的点叫冰窟窿,尤其是摆船的更加辛苦,每天扛着冰镩子检查冰道,在冰道两侧凿开冰层察看有无空盖子。河水封冻数十天后,河水流量减少,导致流动的水面下降,与冰层下缘形成一定空隙后的冰层叫空盖子。空盖子失去了河水浮力的依托,极易碎裂坍塌增加了跑冰的危险性。每到刚封河是或开河时,都有外地人由于不熟悉道路,掉到清沟里淹死,当地人叫“顶铺盖子”。也有的夜间过河,掉到冰窟窿里,河水虽不深但却爬不上来,一是衣服湿了笨重,二是冰滑抓不住,被活活冻死在河道上。
党创立初期,昌乐党组织在姜各庄渡口设立了秘密联络站,接送和掩护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乐亭和昌黎南部开展工作的人员,为昌黎路南地区播撒革命火种,负责人是木瓜口村的岳泽普,人称“岳老爷子”。岳老于1933年发展了昌黎县的张其羽为共产党员,成为昌黎县第一个中共党员。后张其羽在姜各庄程庄小学教书,秘密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并于1936年初组建了姜各庄地下党支部,这是昌黎县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们秘密培训抗日积极分子,刻印传单,到滦河两岸各村散发,宣传“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等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为参加1938年的冀东农民大暴动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暴动失败后,张其羽回到滦河岸边,在岳泽普领导下开展工作,在两岸各村组建抗日政权。姜各庄成了昌黎南部第一个抗日堡垒村。当昌黎县城和泥井等据点的日伪军到沿河一带清乡扫荡时,村民们便从渡口过河到各村躲避,并将大小船只划到对岸的河湾里隐蔽起来,当敌人赶到时,只能望河兴叹干瞪眼,当乐亭县城和汀流河据点的敌人来扫荡时,也是这个办法。在峥嵘的岁月里,滦河是抗日军民的天然屏障,姜各庄渡口为两岸各村群众“跑敌情”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抚昌联合县工委、办事处改建为昌黎县委。由于姜各庄交通便利,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群众基础好,所以昌黎县民主政府就驻在姜各庄,公安局设在草程庄,法院设在向阳坨村。同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其中有筹备召开国民大会的条款。为落实协定,冀热辽行署派干部来姜各庄主持推选解放区的国大代表,全县选出县委书记郝炳南,信庄周春育为出席全国的代表。
1946年冬季,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沿北宁路向路南解放区大举进犯。听到国民党军队出城的消息,全体村民连夜向南转移。当时笔者姥姥也跟着人群往滦河沿儿跑,过滦河时,有个壮年妇女见姥姥跑不动就搀扶着、拽着她一起跑。刚过滦河,追到岸边不敢过河的国民党伙会们就开枪了。姥姥拧着个三寸金莲,颤颤巍巍,落在后面,一颗子弹无情的扫过来,正好打在她的臀部上,鲜血直流,瘫倒在地。好心的群众将姥姥拉起来,找了辆牛车,拉着她继续往南跑,才避免了被打死的危险。
1983年,滦河上游修建了水库后,水量减少,政府在下游姜各庄渡口修建了一座临时木桥,汛期到来前就拆除。但由于桥面过窄,只能一辆大车通过,不能开对头车,所以曾有行人被大货车卷到河里,叫人又喜又忧。1984年发大水,桥来不及拆,木桩子都被冲到渤海里去了。
1992年河北省政府提出,为了适应和促进河北省经济的发展,开发沿海资源,加速建设环渤海经济区,决定修一条从秦皇岛经唐山沿海直达沧州的公路。乐亭县委、县政府修筑东起姜各庄渡口,西至大庄河56公里沿海公路,并在姜各庄渡口建一座大桥。1994年9月底环渤海公路上第一座大桥——姜各庄特大桥建成,新旧两桥形成双向行驶格局。为唐、秦二市乃至全省的经济腾飞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当年摆渡过河的情景更已成为人们渐渐模糊的记忆了。
(作者张淑艳、孙绍棠,姜各庄镇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