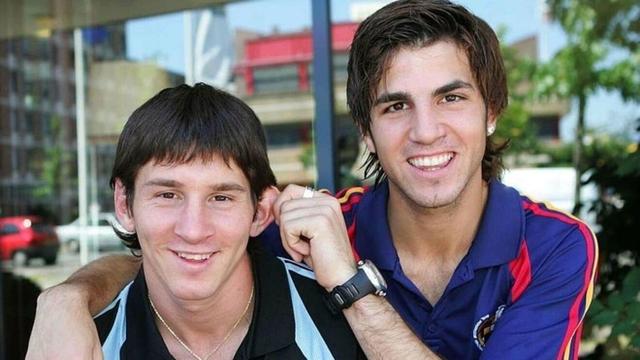大武的记忆孙良鑫,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大武的素材?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大武的素材
大武的记忆
孙良鑫
“大武”这个曾是乡镇政府驻地的古老村落,已经开始拆迁了。它将要和三四十年前,围绕在村庄四周的几千棵、两人合抱的柿子树那样,被连根拔掉。就连四十年前,象征大武大队,经济实力和繁荣的大礼堂、教学楼和办公楼,也将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不久,新的楼群将在异地把它取代。回头是眷恋,向前是追求!面对将要复垦的旧村址,回想它给历史留下的那亮晶晶的一页,我这位土生土长的大武人,自感有种沉甸甸又说不清的使命感。我和许多人一样,怀着骄傲而又悲伤,自豪而又凄凉,无奈里又充满希望的心情,促使我这位盲人在电脑上打下这几行拙句,以留后念,方能寝食俱安。
誉满齐鲁的大风匣
大武村的辉煌很多,现在我就先来说说,四十年前的大武人,是怎样制作百姓生火做饭必不可少的大风匣的吧!
从小就爱动脑筋的我,在做风匣的环境中长大。我耳闻目睹,见证了大武风匣的鼎盛与衰败之全过程。
我的大哥孙良福、街坊于清旺是村里最后一批出色的做风匣高手。瘦小耳聋的邻居韩启贤爷爷,是我记忆中的木匠名师。村里的好几位做风匣好把式都是他的高徒。我同学孙曰友的爷爷孙玺荣、老支书于国州的父亲于大粱姥爷,就曾被选拔到章丘做风匣十年之久。据说,抗美援朝那会儿,于殿杰、于殿利弟兄还为我军兵工厂做过制造手榴弹的三尺二寸的大风匣。建国初期,本村有不少心灵手巧的热血青年,带着木工家什,奔赴祖国的需要之处。孙曰亭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我家住在村里唯一有名字的“路家胡同”里。记得十来岁的时候,我每天晚饭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左手举一盏煤油灯,为做风匣的父亲照明,两眼还吃力地看着右手拿着的故事书。我的大姐孙艳芳,16岁就帮父亲拉大锯、解木板。
1965年,在四清工作队和支书于国洲等人的支持下,我父亲孙荣书组织村里的能工巧匠,成立了专门做风匣的副业股。而后又从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艰难地挺了过来。使各户家庭作坊式的分散经营,改为了集体性质的集约化生产。他们把木料的采购、解板、配板、烘干和风匣制作,直至严格验收,最后到销售,都搞成了由该项特长的人员来负责。就这样,大武的风匣,从产量到质量,以及它的使用范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各地的供销社,纷纷上门,联系经销。给大武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十年后,随着电力供应的充足,为鼓风机的使用创造了条件。风匣的销售日趋困难,终于在五年后、被迫停产关门。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在副业股创建之初,我父亲从本村小学请了一位老师。在我家搞了一张“商标”,其实是张印贴的初样。他走后,我拿着仔细看:上部画的是位拉风匣的主妇。也许是这位老师的疏忽,画中的人物,不是用人们习惯用的左手,而是用右手拉着一个空风匣。上面没有锅台和火焰。风匣朝里一面、也不见风匣的气嘴。画中风匣的两个邦也不是近高远低,而是相反,看上去十分别扭。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永固”牌。这也不太确切,风匣的主要功能是吹风,而不该强调它的坚固性。我把自己的看法说给父亲听。他点点头说:“你说的还真是有道理,我叫别人看看再说!”也许我是小孩子,大人们对我的不同看法并没有理睬,我也未曾再问。
很快,那张样子做成了粉红色的印刷品。每个验收合格的风匣上都会贴有一张,直到十五年后,风匣被鼓风机逐步淘汰为止。也怪,这张有问题的印贴,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大武风匣的信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销作用。我父亲曾在吃饭时说过:“咱的大队的风匣,北过黄河卖到河北。南由公社的任文明社长,引到了江苏农村他的家乡。西至德州、聊城一带,最远的是经烟台卖到了东北去。”
每年的大年初二这天,是大武人“开市”的日子。就是现在开业的意思。它是这个村特有的节日。这天一大早,各户的主妇忙着煮饺子,年轻的或者是男孩子们,则敞开大门,拿出一根摘柿子用的长杆子,挂上一支长长的鞭炮,在大门外鸣放。这时的全村“噼里啪啦”,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只见,大街小巷纸屑满地,烟雾缭绕,好不热闹。据老人们说:“从这天起,大武家庄的老少,就要开始操扯风匣的营生了”。另外,社会上早有“金窝托,银上庄,不如大武家庄一后晌”的俗话。这就是说大武人白天可在地里忙庄稼,晚上家家户户在家里做风匣,以换取不菲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来说说外出采购木料,也就是“看树”的吧!过去是看树的人,肩上搭一个帆布钱衩,再带一个幌子。让人一见就知道是买树的来了。他们走村串巷。见到合适的楸树或者桐树,经主人同意后,可进一步查看此树是否有像油饼那样一层层的窝圈病,或者是黄烂病。一旦走了眼,买了这种树木回家,不仅不能做风匣,就是当柴烧也没有火焰。其次才是丈量测算它的木材价值。然后,和对方协商好价钱,支付定金。至于交易方式,要钱的好说。有的树主愿意要高粱或小米等粮食的。那就按当地的市场价折算,等伐树时运来结清。
再就是找好几个沉稳的青壮年做帮手,捎着干粮和要换木料的粮食,带上大小锯子和粗壮的棕绳等必须的工具,推拉着车辆,返回卖树的人家将大树伐走。要买的树木往往长在房前或屋后,这就要求出去干活的人,不仅要保证树上树下人员的绝对安全,还要保证不会砸坏人家的房屋及其任何值钱的东西。
出去卖风匣的也很辛苦,装满风匣的大小车辆,重量轻、体积大,既怕风又怕雨,还怕路上出问题。过去的路窄而不平,又是木轮车,十分难走。他们经常三五成群的披星戴月,奔走在赶大集的道路上。
在家的粗笨简单的活是拉大锯、配板和烤板。好木匠多半是集中精力做风匣。多数的木匠啥活路都干。
大武风匣的设计非常巧妙。它是个外表成长方形的箱体。全木结构,内外不用一个钉子和螺丝等金属部件。通常主要有二尺四寸、一尺八寸两种规格,也可按用户的特殊需要而订做加工。我说:风匣就像一个木制的空气压缩机,里面的猫头就是活塞,它的边沿用公鸡颈部的上等鸡毛来勒成,连杆与手柄相连。推拉都有空气从风门进入,再经猫头挤压,压力足够大的气流就会经风道在风舌的自动控制下,而由气嘴喷出。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千百年来,不管是百姓做饭锅灶里的秸秆、野草和树枝,还是豆腐房、旅店和铁匠炉里的煤炭,都是在风匣的协助下,使火焰熊熊燃烧。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不尽的丰富与多样。它的功效和节省的生产力,无人能够准确估算。现在随着电器化的普及和清洁燃料的使用,风匣早已无用武之地。可我们的先人曾为此展示过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将永留史册。
壮观迷人的柿子行
四十年前,大武村周围那数千棵纵看成排、横看成列、壮观迷人的柿子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烧柿子和柿饼的甘甜也时常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多少年来,大武的柿子行和风匣一样,是除土地外,又一项养活大武人的收入来源。它同风匣一道给大武家庄引来了多少东西南北的客商,又产生过多少久传不消的佳话,你就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有些山西人,从洪洞县的槐树下和枣强县一带启程,迁移到山东各地。在大武一带定居的移民,把老家的风俗和生活习惯也带到了这里。是他们栽下了第一批作砧木的君迁子,也就是软枣树,嫁接了第一批柿子树苗。由于它抗风、抗病虫、抗干旱。树干高大,树冠像四周伸展,一棵中等的树形能遮挡半亩左右的阴凉。鲜果耐运输,加工、晾晒后的柿子块、柿子饼,糖分高,耐储存。它既是招待亲朋好友的辅食佳品,又可在冬春青黄不接时添加糠菜充饥度日,也可在农闲时拿到集市上去换些称盐打油的零花钱。因此,它特受当地人的喜欢。有句俗语:“明朝不几棵,清朝成了行”。看来,大武的柿子行,是经过多年的栽培才形成的。由此推断,那几棵三人合抱的空心老柿子树,少说也有五百多年的树龄了。
大武村还有个老规矩,儿女成家立业,不但分地、分房,也分柿子树。每年的四五月份,柿子开花的时候,常见有外地的蜂农把一个个蜂箱,整齐的摆放在柿子行里,让勤劳的蜜蜂采集柿子花粉,酿出甘甜的蜜汁。等到天气渐渐炎热,这里又成了举行大型活动的好场地。你看:在北门外!不管是装腔作势的唱大戏,还是彩旗飘扬的开大会,甚至那些争夺胜负的篮球赛,都是在这里举行。偶尔,也见消防队在这里搞训练。最热闹的大概就是春秋两季的学生运动会了。看!竞赛跑道上的小选手争先恐后,看谁跑的快,瞧!沙坑前的小劲敌,暗下决心,要比比谁跳得高……外围是呐喊助威的小观众和围观的老百姓。
1956年,我刚四岁,朦胧记得,奶奶和姑姑孙桂英领我去南门外的柿子行里赶农贸物资交流会。我姑姑怕我被人群挤丢,便抱着我挤来挤去,在一个苇席搭建的摊位前,买了个里面是白色,外面是绿底红花的小喇叭。不远处还有唱戏的锣鼓声。俗话说: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来赶集。由于,柿子的生长期较长,早晚几天采摘都没关系。所以,谁家摘柿子要抽农活之闲空。这也是本地的秋种大忙季节,大人们在地里忙农活。孩子们把汤饭送到地头,再回到柿子行,看守自家成熟未摘的柿子。这是孩子们展示天性的时候,他们像花果山上孙大圣的小弟子“刺溜溜”爬上柿子树,摘下几个柿子扔下。等在树下的小伙伴一个个准确的接住,轻轻对放在挖好的柿子炉上用火烧。这也是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吃法。你看!他们两眼被浓烟熏得直流泪,可还是用柿子树叶“扑打”“扑打”的给炉火扇着风。并不时翻动着烧的不均匀的柿子。当它由黑变焦,里面“咕噜噜”冒出乳汁时,柿子就烧熟了。这些顽皮的孩子们,用眼角扫视着周围,生怕有人打闹着哄抢他们的美食。他们用小嘴吹吹黑蛋蛋上的热气,再伸长小舌头,舔舔淌在小手上滚烫的乳汁,好歹剥去烧焦的黑皮,“嘘溜溜”吃着烫手的烧柿子。
当有外地客商来买柿子时,他们就连蹦带跳的跑去告诉大人们拿主意。这里摘柿子像过节。孩子们拿着高高的抽子,这是为摘树冠末梢的柿子而做的专用工具,它是在高杆子的细头固定一个铁丝环,缝上个布口袋,再往铁环上交叉上两根铁丝。用时,用它套住柿子,把杆子一拽,柿子便掉进布兜。这样,既可以连续采摘,又不至于把柿子摔坏。大人则摘下挂在屋檐下的高梯,带上麻绳和篮子,全家推拉着大小车辆,来到自家的柿子树下,将一筐筐摘下的柿子运回家或者当场卖掉。这里的柿子买卖不按重量而是按“份”,也就是:一只手拿三个,两手拿六个叫一拳,二十拳一百二十个叫一“份”。留下的也有几种吃法:一种是掰成两半晒柿块,或者去皮晾晒成柿饼。也可用桃核的尖儿,在柿子周围点刺几下,放在温水里泡一周,等除涩后再吃。还有,就是把鲜柿子放久了,就会变红变软,这时吃起来的感觉甚至比蜜还甜。
那么,如此之好的柿子树、柿子行现在还有吗?有!还有七棵,有的已被林业局挂上了“古树珍木”的牌子保护了起来。其余的都因复杂的历史原因而被无情的消灭了!因为,在当时,大武不但是方圆十几里的中心村,也是公社驻地。因此,大片的柿子行,已被增设和扩建的社直单位而挤站。再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的人口集聚膨胀,多数是几家住一个小院,拥挤使各家矛盾不断。盖新房又不能占用可耕地,人们只得痛苦的选择了将柿子树连根拔掉,腾出空间建新房。
现在,随着乡镇政府和所辖的企事业单位,一起撤走。又加居民社区的拆迁,这里已是空旷之地。因为水源地的保护,大武的旧址只能种植树木。这也许是人与自然的博弈而最终的平衡吧!
百姓喜欢的大礼堂
“大武大队俱乐部”,俺都叫它大礼堂。它是一座建筑面积602个平方米的建筑物。里面各种幕布、灯光、音响、投影机和放映设备,一应俱全,观众坐席有1008个。
在1976年,国家还十分贫穷,大多数农民还处在缺吃少穿、艰难度日的背景下,一个生产大队是怎样建造起这座全国罕见的村级大礼堂的?它又曾发挥过怎样的作用?我作为这个大队普通的一员,作为“乡村记忆”的热心撰稿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条件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记载。
建造这座大礼堂,当然要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强烈的文化需求两个基本条件。先说其一:从1965年四清运动时,村里相继组织人力挖机井,修水渠。重视科学种田,耕种、收获、脱粒,率先采用了初步的机械作业。大队有汽车,拖拉机多辆。各生产小队都有几辆马车。做风匣的副业股,南山坡的石料开采,已是规模化生产。社员家庭广泛使用三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闹钟。青年们的手表、大衣也是平常休闲的穿戴。综合实力在全区已稳居榜首。前来求援借钱、借农业机械等的关系单位越来越多。1976年以前就多次受到省、市区政府表彰。
其二:这个村早有重教育、爱唱戏的好传统。五、六十年代,村里就走出了“山东农业大学”本科生孙曰星,“淄博师范”生于洪吉等一批国家急需的知识分子。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大爷孙汉书、表大爷于国厚、街坊赵士德大爷等身穿奇怪的衣服,在台上舞枪弄棒耍大刀。还有于国才大叔男扮女装,扭扭捏捏演苏三。孙曰学、孙曰春两家也都是全家能上台的好角色。“文革”头一年,本村青年于传科、于桂兰等四人自编自演的三句半,荣获了张店区文艺汇演一等奖,领回了奖品民族乐器一套。文革之初,于青州、李兴业通过一村人的大协作,终于成功地移植了现代吕剧“红灯记”。以后又有他人排演了称颂本大队省级劳模张玉兰的节目。还编排了其他戏曲、歌舞、快板儿等。涌现出了孙美华、孙来发、于传安和李桂华等演英雄、当模范、唱先进的一班子名角。他们的身影和歌声不但是在邻村和本大队的舞台,也经常出现在农忙的地头、场边和整大寨田的工地上。对当时的运动和农业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在胜利炼油厂的建设工地,大武的业余剧团为上万名石油工人的慰问演出,更是让当时的石油人在五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文革时,开会多是那时的特征。多是重要的大会,白天开,一般的学习和工作安排,晚上开,经常是冬天开会顶寒风,夏天开会淋着雨。有魄力敢担当的大队支书于国洲、沉稳老练的大队长于传顺、耿直能拼的民兵连长于传华。找村里的土专家韩保德大叔、能工巧匠李象意、孙良福等人,开会研究、论证,并实地考察了多处礼堂。最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盖“俱乐部”!让老百姓也和城里人一样,开会、看戏、看电影,都到礼堂去!就这样,在全大队上下的一致赞成和支持下。建完大队办公楼之后,施工人员一鼓作气,投入到了使人振奋的新工地。那时,要钱,副业有!要石料,自己开采,自己运输。要木料,村里村外有的是大树!要工匠,许多家庭都有行家里手。要技术,有土专家、土工程师。要干劲,上下都想早完成!主体工程完工后,座位,先是各家扛去做风匣的大板凳,又用座四人的木联椅取代,最后才换成了标准的折叠式座椅。从外边看,几层台阶往上是玻璃大门,再往上,是“大武大队俱乐部”七个鲜红的浮雕大字。里面的舞台前边是弧形,两侧各有一个上下舞台的便门。从正面瞧,这个舞台是上脚为圆型的长方形画面。再配备上各种幕布,它经过请来的艺术家一番修饰,很是大方、气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同学徐圣松家巧遇他的岳父,当得知这位朱大叔是区文化局的副局长时,对这类信息特别敏感的我立即想到,礼堂的以后正需要文化局的扶持,便绘声绘色的作了一番介绍。并像自己的事一样,邀请对方来考察、做客。朱副局长高兴地答应了。还说:“要是条件完全具备了,就可介绍外地的剧团到大武去演出。”从此,山东吕剧院、淄博的几个大剧团,和几乎全省县级以上,如:广饶、沾化等专业剧团都在这里卖票唱过戏。不长时间这里还有宽银幕电影和大家见面。
每到农闲或者节假日,村里的戏迷,就在这里或排练或登台。有一次,大武的业余戏班子,于宗宝他们,要在大礼堂唱吕剧《李二嫂改嫁。》村里人陪伴邀请来的亲朋好友,在家吃罢晚饭,捏着门票,进礼堂对号入座,等待开场。门外几百名远道而来又没票的戏迷们,被拦在门外。来自40里外的敬仲镇的戏迷们,情绪激动,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和民兵争吵了起来。经过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派出所的孙所长耐心的协调,看戏的大门敞开了。这些刚才还差点闹起事来的激进分子,不抽烟、不说话、猫着腰、找个空档,席地而坐,满意地享受着看戏的乐趣。还有大武镇政府曾多次在这里开会。甚至有一次区人民法院曾在这里为一起赡养案件开过庭。
40年过去了。由于年久失修,房顶的木结构,已经腐朽。虽然几经简单的修补,也是无济于事,想大修又要举村搬迁。因此,这座风光一时的大礼堂,已于2015年被宣告为危建而停用。等待它的也许会像这里的新旧民房那样,被建设者的后人不情愿而又无奈的拆掉。
大武的记忆三部曲,到此收笔。让我们记住过去的曾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华民族日益强大的巨轮去谱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骄傲与自豪吧!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又有视力障碍,行动十分不便。虽然,自己为此打了几百个电话,拜访了几十名知情人士,力求查阅和核实的资料准确无误。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难免出错的。在此,恳求各位理解和原谅!谢谢!
2018年5月于华能辛店电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