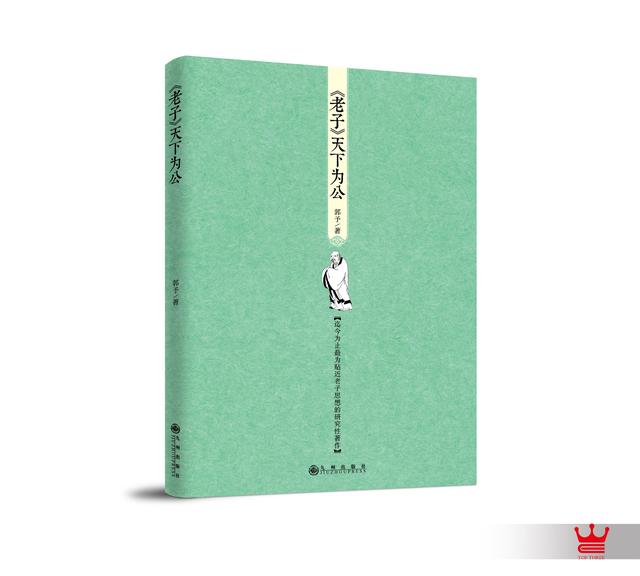【原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释文】
1.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混成”,是老子惯用的逆推的说法。实质是说“道”生成了万物。反过来讲,就成了“道”由万物“混成”的了。
“先天地生”,是说在天地诞生、生成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这其实也是一个逆推的说法。他并没有说是“道”生成了天地,而是由天地的生成上溯至“道”。貌似未肯定(其实也没法肯定,谁又能拿出证据说“道”生成了天地呢?),然而从推理论证上又加以了肯定:天地是“道”的直系后代,虽然未见得是其亲生也。王弼论曰:“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不知其谁之子”,见于《第4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意谓:我不知道它是由谁生成的,但我却可以肯定,它是万类万物始祖的祖先。这实际上还是在说,“道”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和始祖。因为就世传谱系而言,上溯到此便为止了。
2.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寂兮寥兮”,河上公注:“寂者,无音声;寥者,空无形。”“寥”,篆文本从广(敞屋)从膠,本义是空虚。后来“膠”省作“翏”。又后来,“廖”用作姓,空虚之义又改写成“寥”。从宀从翏(膠省)。而“膠”,即胶也。《说文》:“膠,昵也,作之以皮。从肉,翏声。”由此可以想见,在一个广大充裕的空间内,相关物体却都胶结在一起,由此衬托出了环境的广大与空旷。“寥”的空虚之意大概源于此吧!“寂”,篆文从宀从尗。“尗”,从金文“叔”的偏旁来看,是用木橛等尖器掘取芋头一类植物的地下球茎之形的省略,表示收取。《说文》:“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用作名词,指球茎。由此可见,“尗”实际上是指成团成堆,牵扯联络在一起的地下球茎、果实,比如花生。这样,“寂”与“寥”便有了相通之处,都是说在一个足够广大的空间内,相关实体却挤在一起抱团取暖,从而更显出了空间的寂寥与空虚。
所以,“寂兮寥兮”并非是在强调此“物”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形体的状态,而是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混成”之物单独存在于广漠黑暗的空间的这么一个场景:它那么小,那么弱,那么孤独,那么冷清,形体并不是那么大,也不是那么耀眼,也不是那么强壮;它看上去很普通,甚至显得卑微而无助。然而果真是这样吗?这个留待下文细说。先说“寂”与“寥”,它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扎堆聚集的形态,不正如《第14章》所描述的那样吗?——“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王弼注曰:“无物匹之,故曰‘独立’也。返化终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周行无所不至而不危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为天下母也。”“独”,从犬,蜀声。“蜀”,甲骨文象突出了头部的蚕蠢蠢蠕动形,南楚谓之“独”,大概是因为蚕总爱作茧自缚,一个蛹里只能有一个蚕吧!所以“蜀”有“独、单一”之意。“犬”,其甲骨文、金文字形像一立身张嘴扑咬之大狗形也。所以,“独”强调的是一种强烈的领地意识。当然在本文,则是折射了“道”虽然单枪匹马、孤苦凄清,却不乏战斗意识,绝没有萎靡不振、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意思。“立”,是挺直腰板儿,顶天立地,绝非畏畏缩缩、摇尾乞怜之态。“不改”,即不更也,是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也。“改”,甲骨文从巳(蛇)从人手持攴(棍棒),表示受制于人,不得不低头也(蛇一旦被制住七寸,便丧失了攻击性,只能受人摆布了)。所以,“独立不改”强调了“道”虽然孤军奋战,却绝不会被环境所吓倒的英雄气概。“周行”,谓无所不至也。即由一原点出发,向四方辐射之态。故“周”除有细密、周密之意外,还有圆周、环绕之意。所以,“周行”体现的是于黑暗时代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开疆拓土的冒险精神。“殆”,危也,疲敝也。“不殆”,指永不休止,不知疲倦,生机勃勃,活力四射也。
“可以为天下母”,即可以作天下的母体、天地万物的本源。为什么呢?原因如下:其一,它是万物之“混成”;其二,它极为古老,先天地生;其三,它就仿佛是空廓无边的宇宙中一个孤独无匹的“奇点”,却满含战斗精神并深具活力。它不自怨自艾,不屈服于现状;它四处探险,永不休止。那么,它虽然看似卑微弱小,但谁又能怀疑它未来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呢?谁又能怀疑它的足迹不会遍布宇宙的角角落落呢?故下文“字之曰道”,盖后生之辈皆赖其披荆斩棘、开拓道路之德,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故下文曰“强为之名曰大”,盖整个宇宙都属于它,都等着它去征服,故不可谓不“大”也。因此,鉴于以上理由,老子称它“可以为天下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故《第52章》亦有言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3.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本句的难点在于“名”与“字”的区别上。“字”,乃“标记、记号”之意。“名”,详见《第1章》释,是指事物的活动范围、社会地位、利益范畴。《颜氏家训•风操》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故“名”与“字”乃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
“吾不知其名”,是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准确地描绘、刻画它。原因在于:一,它是混成之物,难免会“惚兮恍兮”;二,它既然可以“为天下母”,因此一定处在难以把握的不断运动、变化及发展过程中。
但这样也不是事儿,总得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吧?因而,“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为什么要“字之曰道”?“道”,其金文字形像四面八方汇合、聚首之所(见《道与德》析)。因此,就其内在性质而言,以“道”字作为对此混成之物的形象表述,是再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说“强为之名曰大”呢?“强”,是勉强,表示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字眼好了。“名”是格局、范围,必然要占用的空间。因为此“混成之物”的发展是持续不断、无穷无尽的(周行而不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实在不好说呀!因此即便给它命“名”,也只能勉为其难,故曰“强”。又因为“大”有舒展、壮大之意,故以“大”名之,也算是较为贴切了,表示其发展无限,前途不可限量。
4.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本句顺承上文。老子虽然“强为之名曰大”,但仍感觉意犹未尽,故以本句加以补充说明。而从本句的句式结构来看,则是通过语意的递进来表现此混成之物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最终着重引出了“反”这个概念。
“曰”,此字另见于《第16章》析。乃逐渐大其义之意。
“大”,甲骨文像四肢伸展的大人形。表示自本体起始向外扩展。它与上一句的“强为之名曰大”略有区分,在此是专指扩展的初级阶段,看上去犹如本体的自身膨胀,因此与本体尚藕断丝连。
“逝”简单地说就是“离开、前往”之意。王弼注曰:“逝,行也。不守一大体而已,周行无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守一大体”,是说脱离本体呈射线状向外辐射发散;“周行无所不至”,是说方向并不确定,漫无目的。
“远”,其金文中间为圆圈,上下为“止”(脚),左右为重复的“行”,说明“远”就好像人在围着圆圈打转,无休无止,没有尽头。所以,“远”有“辽远”之意。王弼释此曰:“远,极也。周行无所不穷极,不偏于一逝,故曰‘远’也。”这是对“逝”之释的深化。释“逝”时曰“周行无所不至”,释此曰“周行无所不穷极”。则“逝”与“远”的区别就在于程度上。就各个方向上的射线(逝)而言,有速度快慢、用时长短之分。但若从比较广阔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去衡量,因为同是辽远无极,则表现在各个方向上的“逝”便无所区分,可同称之为“远”了。故曰“不偏于一逝”,即各方向之“逝”没有什么区别,而是一个均等的以本体为圆心向外无限扩展的圆环,圆周上各点到圆心的距离无疑都是相等的。
“反”,乃翻转山石之形。对于此字向来有歧义。有认为“反”即“返回”之意,有认为“反”即“相反”之意,有认为两者兼而有之。王弼释此曰:“不随于所适,其体独立,故曰‘反’也。”楼宇烈校释曰:“‘适’,往,止。‘不随于所适’,意为‘道’有独立之本体,即‘混然’、‘无形体’,而不随所化生之万物而止于‘有分’、‘有形体’。”释读太过了。其实王弼之意简单地说就是不随波逐流,不随遇而安,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而不随大流儿,此即为“反”。对吗?不对。
“反”,就是“相反”之意。如同“我”与“非我”的关系。混成之物由大而逝,由逝而远,这些都可以想象、理解,为什么发展到最后却变成了“反”呢?原来,除本体以外的“我”都是“非我”。当不断地发展变化,以至于辽远无极之时,作为圆心的本体的“我”在巨大的“非我”的圆内,恰似沧海一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原来的“我”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大到极致,便成为了完全的“无我”之境。即:“我”也成为了“非我”,此即曰“反”。
那么,“非我”就不是“我”了吗?当然不是。“非我”仍然是“我”,只不过是“大我”,而非最初形态的“小我”。“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就是“反”。《第65章》曰:“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此“反”字的理解。
关于“反”与“大”的关系的思想亦散见于各章。例:“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反”并不意味着对立,而是对自身以外事物的认同归一。实际就是上面所说的舍弃“小我”,以实现“大我”的“无我”之境。在此过程中,“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7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所以,“反”并不是自贱自戕,而是不纠缠于蝇头小利,不停留在一己之私,能以天下为己身,不愿因小失大也。
5.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1) 道大:道为什么大?如前所述,“道”是万事万物的混成之物,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带有独立主体意识的私自私己,或者即便有,也早已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消弭于无形。因此,“道”具有“反”(无我)的特性,故曰“道大”。
(2) 天大、地大:天地为什么大?《第7章》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亦具有“反”(无我)的特性。因此天地亦为“大”。
(3) 王亦大:王为什么大?《第65章》曰:“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作为一国之君,他理应无私,理应不争,乃理应深具“玄德”的圣人也,故曰“王亦大”。那么显然,在“四大”之中,“王亦大”才是老子真正想要推导出的结论。
6.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 法:效也。
(2) 人法地:为什么不说是“王法地”呢?其一,“王”也是“人”,用“人”代“王”并无不可。其二,由“王”过渡到具有普遍性的“人”,是要通过推导出的“自然”二字来弘扬人性,解放人性。
(3) 道法自然:就字面含义而言,此四字是讲“道”按自己的样子行事,以自身为法则呢?还是讲“道”按万物的样子行事,为万物服务呢?
河上公注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意思是说“道”最大了,要“法”也是“法”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唯一束缚,实质就是随性自然,想干嘛就干嘛。王弼注曰:“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可见这两种分歧。
其实这两种分歧根本算不得分歧,在本句这两种含义是兼而有之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语言构造上分析,可谓层层递进。四大之中“道”最大,其它三大皆有所法,“道”法什么?当然是“法”自己。因为道体最大,到“道”这个程度就只能以自己为参照物了,是谓“道法自然”。这样就使“人”、“地”、“天”、“道”拥有了“自然”这一共同准则。而所谓“自然”,就是自己本来的样子,就是自然而然。故“道法自然”亦是指“道”以不违万物之本来面目为最高准则,就是使万物皆能各得其所并各得其所欲。故就人事而言,实际是说应以人为本、以人为大,也就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方得自然,即使是“道”也是为“人”服务的。
(4) 小结:本句承上句而来。既言“宇中有四大”,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需要加以说明。本句就是说明它们的谱系关系的,并最终导出了“道法自然”这个中心思想,暗含着以人为本、以人为大的哲学思想。
【总结】
老子在本章用逆推的手法架构了一个“道”的模型,然后由其名为“大”推出“反”的概念,再由“反”的概念推导出宇中第四大——王。“王”也是“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随性自然才是人类社会中应该贯彻的最高准则。
本篇构思精巧,推理严密,大致包含了以下三方面内容:一,进一步论述了“道”的地位和构成;二,提出了为“王”的必要条件,即“与物反矣”,即无私、不争;三,由“王”过渡到普通人,发出了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的呐喊。由此我们再反观前面对“道”的拟人化描写: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不正是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写照吗?
而若将脑洞放大些,则关于宇宙的形成,本章无疑也给了我们以重大启示。
一般认为,现在的宇宙还处于大爆炸后的膨胀期,之后会彤缩,彤缩到极点之后,一切归于虚无,然后又重新爆炸。然而,如果我们依照老子的理论,则可以推想,所谓的“膨胀”和“彤缩”其实是在同时进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膨胀”就是“彤缩”,“彤缩”就是“膨胀”。宇宙并没有创始的那一刻。每一天每一妙,都是它崭新的起点(《第4章》曰:“湛兮,似或存。”)。此即所谓“膨胀”。宇宙也没有毁灭期。每一天每一妙,它都在奔向它的起点(《第4章》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此即所谓“彤缩”。也就是说,宇宙其实形如一枚钻戒。“道”是那颗钻石,宇宙起始于它又终结于它,从而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圆环——是的,这一个闭合的圆环,就恰似磁铁周遭那些密密麻麻的磁力线所描摹的情状。
若把“彤缩”视作“妙”,把“膨胀”视作“徼”,那么“道”兼具的这两种特性便称之为“玄”。
【译文】
在天地存在之前,就有一个东西浑然天成。它是那么孤单寂寞,又是那么高远凄清。特立独行且从不屈服于环境,无所不至而永不疲倦于开拓!它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万物的母体。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只能依据它的精神内核管它叫“道”,勉强地给它起名字叫“大”。
“大”,意味着膨胀;膨胀意味着爆炸;爆炸意味着辐射;辐射达于无极便意味着舍身忘我。
所以,“道”是大的,“天”是大的,“地”是大的,“王”也是大的。宇宙间有四种大,“王”便是其中之一。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
“人”围绕着“地”运动,“地”围绕着“天”运动,“天”围绕着“道”运动,“道”的运动则是以自然而然、随心所欲为最高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