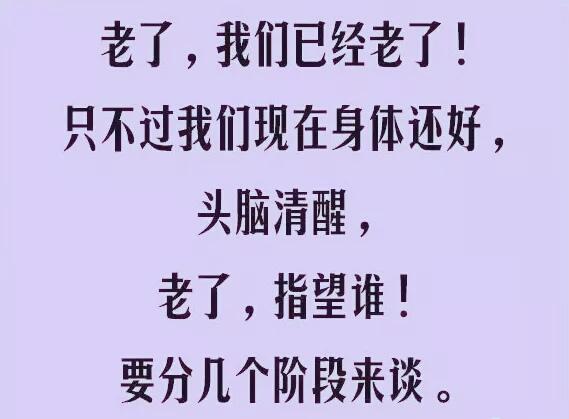近日,国内外媒体相继披露了中梵关系出现了突破性进展的消息。观察者网着重报道了台湾有关方面对梵蒂冈与大陆的关系升温的焦虑。梵蒂冈作为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或许是世界上国家体量和文化影响力反差最大的国家。作为台湾唯一的欧洲“友邦”,其对大陆的一举一动都绝非“宗教”两个字能涵盖的。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线条无限延展到近代甚至是古代,耶教之一的聂斯脱里派,即景教早在公元六世纪就曾落户华夏大地,而古代中国与罗马教廷或其使者产生实质接触也有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哪怕是“西方中心论”的顽固反对者也必须承认,晚明直至晚清的这三百年,中国是以一种仓促的被动感被裹挟进了世界体系的框架内。
19世纪中叶以降,衰朽之躯的“旧邦”一众臣民惶恐地寻找着“新命”的药方。在这个背景下,晚清士人对梵蒂冈这个母体孕育下的诸多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心态是复杂的。斥其“紊我纲常伦纪,乃夷狄之法”者甚众,受洗拜在耶门之下,设义塾论著说,援耶入儒者亦众。

万历十年进入中国的利玛窦,绝对算得上传教士的超级大V了
如果我们抛开晚清天主教传教士在启蒙和救亡这一主题下的角色,把时间点拉到17世纪中叶,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复杂的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形象。在晚明帝国的斜阳之下,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曾亲历过那段“以夷篡夏”的特殊年代,和南明的肱骨之臣们共享过一段“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的血泪史。
明清易代的史学早就超脱了古代中国改朝换代之惯常光谱,必须将其置于整个东亚范围内才更能厘清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是史学界早有的共识,而梵蒂冈传教士这群“大门口的陌生人”,又赋予了这段历史以更为宏大的世界性格局。
本文以南明永历一朝天主教传教士反清复明之活动作为切片式的考察,以求能稍微勾勒出梵蒂冈与中国五百年纠结史中的片鳞半爪。
桂林之战
1646年十月初十,桂王朱由榔登大宝“监国”,成为明史真正法理意义上的末代皇帝。相貌堂堂据说长得很像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生性懦弱,但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符合一般人对“末代皇帝”的想象。那么他登基时,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这一天距离明思宗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之上的“甲申之春”仅两年有余,但已经历了弘光、隆武两代君主,他是明室南渡之后的第三任,前两任践祚之短,下场之惨恐怕都超出所有明朝遗老的想象。

崇祯君王死社稷
朱由检君王死社稷之后,到清军攻克弘光帝朱由崧的南京仅仅历时十四个月,实际上从这一刻起,明朝的气运真的就如同燃见跋之烛,外臣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在外敌压境势如燃眉之时,内臣居然还聚讼不休,党争不断。
1645年六月十一这天,唐王朱聿键在众臣的拥戴下,力压一干主要竞争对手筹备监国,一个月之后他在福建成了“隆武帝”。和其他王爷不同,朱聿键从小并没有很优渥的家庭条件,过得比较苦逼,但生性要强且品格坚韧,虽生在王府却从小就饱经患难的朱聿键,有个和前两任明帝王不同的特点:对待那群来华的传教士特别好。在短短的不到一年半的在位期间,他还做过这样一件事:曾在福州斥巨资帮助一群天主教的传教士扩建教堂,而且御笔书写了“敕建天主堂”五个鎏金大字,并且御赐了“上帝临汝”的匾额。此外,朱聿键还做出了一个重要举动,为后文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
1646年八月初,眼看福建即将失陷的隆武帝带随从官员西奔江西赣州,八月底不料遭清军伏击,被害于长汀。不到两个月后,就有了前文所述桂王朱由榔登基的场面。当时明室在清兵及“附逆”的汉军的追击下已如同惊弓之鸟,硬着头皮上任的朱由榔的“桂王”头衔是隆武帝在位时亲自册封的,作为明神宗的嫡孙,他上位的名分很足,但他加冕之时想必心中已无复国之野望,却突然发现几乎仅剩岭南之地可逃亡,他“监国”称帝之所,便在广东肇庆。
当时,广东清军提督李成栋在镇压了张家玉、陈邦彦等民间和官方的抗清活动之后,基本稳定了广东的局势,既然粤内大定,李成栋会师西进,直逼刚刚在肇庆监国不久的朱由榔。

“随驾车马匆匆……”,永历帝急奔桂林,由于走得太着急,已经灰心丧气不愿再跟着老朱家的某些军官步卒,比如郝永忠居然出现了抢劫皇家财物的现象,登基大典用的帐子和祭祀用品在一片混乱中被抢劫一空。从肇庆到桂林,永历可谓灰头土脸,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有一股规模不大但很奇异的援军正在向肇庆进发,和当时负责断后的副总兵卢卡斯·焦在肇庆汇合。
这一股援军来自已经算是葡萄牙地盘的澳门,总人数约300人左右,由援军前线总司令尼古拉斯·费雷拉(Nicolas Ferreyra)率领。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配有近十门大炮。原来隆武帝被杀前,曾派身边的司礼监太监郑天寿协同传教士毕方济求援澳门。接到消息的澳门天主教福音会派经过短暂争论之后,决定驰援,而且给了援军总指挥25岁的费雷拉最先进的火枪和大炮。由于援军负有重配,所以行军缓慢,到达肇庆时,发现帝已奔桂林,于是这300人火速赶往桂林,力求把桂林成为稳住局势的据点。
也许有读者会奇怪,副总兵卢卡斯(Lucas)·焦居然有一个中不中洋不洋的名字,其实他就是焦琏,三年前就已经受洗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教名卢卡斯,由他来接应费雷拉是非常合适的。
惊魂未定的永历帝面对不断紧逼的李成栋已经毫无斗志,准备再次放弃桂林再奔南宁。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右侍郎摄尚书事,大明忠烈之一的瞿式耜以死苦劝,才让朱由榔稳住了心神。
“汉奸”李成栋平南时虽有小股反抗,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桂林之战明显轻敌了,而且忽视了这300名澳门援明壮士带来的新式武器的威力。
笔者在检寻《瞿式耜集》的时候,发现桂林之战有这么一段话:
“臣急从都司礼庞天寿所铸西洋大火鉖,即从城头施攻,毙敌乘马之虏官三四名,贼势稍却……督镖副将马之骥又从隔天实施炮筒,助我兵威。”
这些大炮在这场规模不是很大的遭遇战中立下了奇功。
这一仗让朱由榔从惶惶不可终日的心境中稍微解脱了出来,帮助他重拾信心的,此处不得不提一个人——传教士安德雷亚斯·科夫勒(Andreas Koffler)。他的中文名,估计会让有不少的南明史爱好者相当眼熟——瞿纱微。跟随明军不断逃窜的瞿纱微面对灰心丧气的永历帝,拿出了全本《圣经》,诵读了《申命记》和《罗马人书》,前者有摩西告诫以色列人让耶和华神为其选立国王;后者有耶稣对信徒宣称,世上任何权柄皆系神命,要对俗权恭敬服从,他向朱由榔做了告白:“我们天主教徒不畏生死,其中一项美德便是效忠皇帝,这是一种大爱,我若死在陛下您的身旁,便尽显对您的忠诚。”
感慨万千的朱由榔重新振作,并且立即召开了御前会议重整旗鼓。永历二年八月,朱由榔重新杀回到了肇庆,也算有了一个小型的“还都”。
跟随永历皇帝转黔、桂、粤等地的传教士不止瞿纱微一人,而是一个小型教团,骨干成员有迈克尔·皮埃尔·博伊姆(Michael-Pierre Boym,中文名卜弥格),弗朗西斯科·萨比亚希(Francesco Sambiasi,中文名毕方济),阿尔瓦罗·塞买多(Alvaro Semedo,中文名曾德昭)等。
为了答谢澳门方面援军,也是为了和葡萄牙天主堂方面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朱由榔在永历二年春天,派出了心腹太监郑天寿赴澳。郑天寿为了在沿途躲避清军及其奸细的盘查,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澳门,受到了澳门圣保禄学院的热情款待,并且在三巴寺举行了隆重的弥撒。
郑天寿向三巴寺赠送了朱由榔的谕诏和各种礼物,澳门方面回赠给郑天寿100只火枪,并且派遣了澳门一些本地的士兵前往广西助战。
当郑天寿带着火枪和援军回到广西的时候,永历大喜过望,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提拔郑天寿为提督勇卫,并且将自己的内廷军队,即禁卫军的军旗改为十字军军旗,有红白两种颜色,上标有拉丁语符识。
不过在和外界的天主教方面接触的过程中,也让朱由榔认识到,澳门毕竟器小易盈,对自己的反清复明大业帮助有限,郑天寿带回了澳门方面的口信,说泰西之地有梵蒂冈,乃天主教大本营,罗马教廷所在地,兵多将广,如能施以援手,则复国可成。
永历后宫集体受洗
永历二年,即公元1648年,此年也是顺治五年,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年份。这是清军入关的第四年,虽然部分心向明室的士人余气难平,仍念叨“胡无百年国运”,但大清看似已经坐稳了江山,岭南之地的反抗势力已经被打成“前明余孽”,不过是一种“匪患”。清军和明军猫捉老鼠的残酷游戏下,偶尔也会有彩蛋蹦出。在朝代更迭纪事本末的史家笔下,这一年看似在南明史的注脚上也无甚有重笔,但如果以中外文化交往史的角度看,却大有可谈之处:朱由榔后宫一家老小,集体受洗成为了天主教徒。
在年初桂林行宫遭到叛军洗劫之后,王太后气急攻心差点一命呜呼,整个后宫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消极情绪。这个时候,瞿纱微带领众天主教传教士这个小班级开了个会,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时不我待,要把永历宫廷集体受洗仪式提上日程了。
两位太后、皇后以及一干侍女本来就对天主教心存感念,而且其中一些人暗地里已经皈依只不过缺一个正式的仪式,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永历皇帝犹豫半晌之后也答应了。

卜弥格所著《植物志》的插图
这个时候,宗教的力量就显现了出来。马克思曾说“宗教乃人类精神之鸦片”。鸦片的确可以作为毒品而存在,但鸦片本身也是药材,可以纾缓肉体的伤痛。同样,如果完全从宗教的消极作用去解读马克思这句话也未免有失偏颇。“精神之鸦片”当然就有心灵疗伤的功效。无时无刻不在逃亡的永历皇室内时常充斥着一股靡废、彷徨甚至绝望的气氛,他们需要一股强心剂,哪怕是片刻的麻痹也好。
1648年农历2月,受洗的时刻到来了,主持人当然就是瞿纱微。后宫的女眷在受洗之后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名,王太后的母亲叫Julia;王太后叫Helena;马太后为Maria,王皇后为Ana。
那么问题来了,永历皇帝朱由榔本人有没有受洗呢?明末清初有一拼遁世的遗老士人都纷纷否认永历帝本人受洗,斥责这类传闻乃是对大明皇帝的抹黑。
不过传教士毕方济的日记明确记载,三月初十这一天,逃奔到南宁的朱由榔奉太后之名跪拜在了天主像前,至于有没有真正受洗就无从得知了。
过了一个月,也就是1648年四月,朱由榔有了儿子。王皇后为永历产下一名男婴,名唤朱慈炫。既然后宫都已经受洗了,按道理孩子生下来也该举行受洗仪式。但这时候朱由榔表现出了顽固的“道统”情结。大明朝三百年以儒学立国,纲常法纪效孔孟先王之法,老朱家受洗要成为异教徒了,这成何体统?当时表示了明确反对。
不料朱慈炫仅仅出生了三个月之后就害有重病,发烧不止,眼看有夭折的危险。刚刚经历过弄璋之喜的朱由榔急得团团转。这时候瞿纱微又站了出来:能救这个孩子命的只有上帝耶和华了!
在太后和皇后的催促之下,朱由榔不得不应允给太子再举行一个受洗仪式,于是襁褓之中的朱慈炫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康斯坦丁·朱(Constantine Zhu)。
虽然南明史未能像南宋史那样,被后世的史学家们列为“正史”而被造册(其原因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但从广义上讲,永历一朝成为中国史上正统王朝各君主中,天主教氛围最为浓厚的一代。
史学家们可以用比较时髦的“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永历皇室成员的内心对“天主”是否真的虔诚,还是只当做一个“神道设教”的权宜之计,但我们终究无法穿越回到那个年代,一窥朱由榔那简陋的后宫的生存状态。
求救梵蒂冈
当时清军加紧了对广西残明势力的围攻,永历四年底至永历六年,明将孙可望收拢聚敛了抗清的残存武装,基本上形成了以原来大西军为主的复明实体,和另一位身在云南的反清大将李定国遥相呼应。但孙可望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愿,与李定国心生嫌隙,双方龃龉不断。
内部手下将领不和,把自己当行权的工具,外部清兵依然步步紧逼,这时候永历帝觉悟,没有足够的外援,只能做徒劳的困兽犹斗。
永历四年秋,朱由榔秘密写了一封衣带诏,把一项重大任务交给了“西游”三人团。这三个团由团长波兰人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带领,另外两人是约瑟夫·郭(Josef Guo)和安德雷亚斯·陈(Andreas Chen),均为朱由榔身边心腹,他们随身携带的包裹中,有致葡萄牙国王书,致威尼斯共和国诸公,上罗马教皇英森诺书,致欧洲耶稣总会长帕科罗米尼(Paccolomini)书信等等。

永历帝嫡母王太后致罗马教宗信件,由卜弥格翻译成拉丁文
卜弥格在西游之前,也曾通过自己的人脉联系过在华的耶稣会的同僚,这批猴精的同僚们其实早就望风投靠了清廷,对卜氏远赴梵蒂冈表现出了极为消极的态度。但卜弥格自认为天命所负,三人在举行了一番隆重的祷告仪式之后,于永历四年隆冬时节匆匆上路了。
根据目前的史料,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三人团在路上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但仅凭基本的常识推断便可知,从广西一路步行去梵蒂冈,难度比起同样徒步到达古代印度的玄奘法师和徒步从河北一路走到中亚的丘处机要大的多。佛教徒、道教徒、天主教徒这三段西行的经历,如果没有极为坚强的宗教情感的支撑是很难完成的。
卜弥格的难度不但比上两位要大,而且结果更是悲剧得多。
卜弥格到达梵蒂冈之后累得只剩下了半条命,也只是仅仅得到教皇礼节性的答复,近东的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大小邦国的宗教改革已经足以让教皇头疼不已,至于发兵援明抗清,这事对他来说不亚于天方夜谭。驻留在罗马教廷的卜弥格久久得不到正面答复,毅然决定起身东归,他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一位看似懦弱却知人善任的朱姓皇帝在等待着他,此时,上距他从广西出发的时间已经整整八年了。
爬山涉水后的卜弥格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回到了澳门。时过境迁,此时的澳门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宽容,慑于权势日隆的清廷的压力,他遭到了驱逐,不得不借道东南亚入境中国。永历十三年八月,身心俱疲的卜弥格倒在了广西边境未能再站起来。距离中土仅有一步之遥,最终未能再见到永历帝一面。
我们无法揣测临死前的卜弥格口中念念有词的到底是“反清复明”还是“哈利路亚”,不过他用全部的生命践行了那句耶稣箴言“世上任何权柄皆系神命”。
卜弥格的同侪瞿纱微,永历皇室受洗的见证者,在公元1651年底追寻朱由榔去贵州的途中被清军杀害,从此,永历帝身边再无传教士陪伴。
结语
本来天主教传教士在晚明政府高层中也曾立志走高端路线。不过他们逐渐发现太监这个群体是个很好的突破口,因为他们没有妻妾之碍,身体上的缺陷让他们在精神上更容易“沦陷”,比起士大夫,他们更容易奉教。
本文中屡屡出现的太监郑天寿是晚明整个阉宦集团中最早受洗的一批,他历经晚明四朝,常伴君侧,任御马太监、司礼太监等职,教名为Achilles(出自荷马史诗《伊利亚德》),是皇帝和那群传教士交流的重要的中间人,即便不少清代“伤痕派”史学家们把朱由榔身边的“吴楚”党争的锅甩给郑天寿,但这个皈依天主教的“阉竖”之晚节,比起“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本来拿着老朱家工资的那群士大夫要好太多。
“以夷变夏”,“窃我中国神器,变我华夏衣冠”,“中原腥膻遍地”……大明遗民的悲愤和屈辱感已无需多言。然而,历史中有趣的地方是经常以喜剧的方式表达悲剧,在晚明同样被有着强烈保教精神的儒家士大夫斥为“夷术”的天主教,却在光复大明的政治、军事活动中扮演过不可忽视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