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古典学研究2023-03-29
原标题:伦敦蝴蝶与帝国鹰:从达西到罗切斯特
作者:程巍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本次推送转自“冯至论坛”官方微信公众号。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和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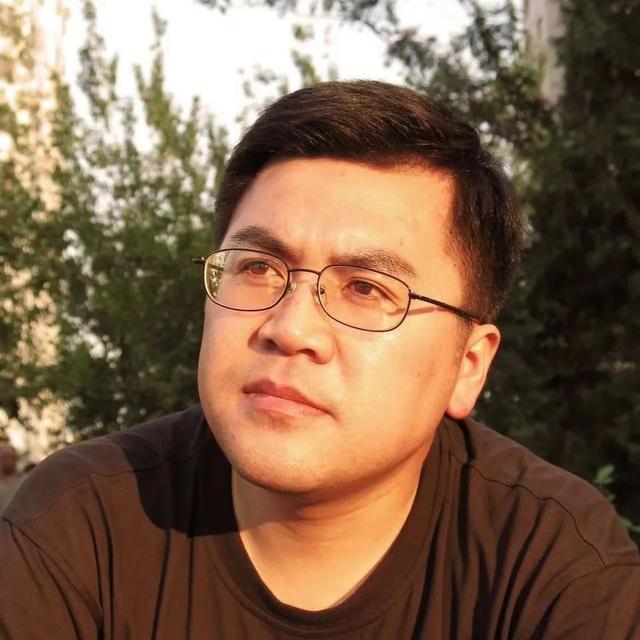
程巍,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长期从事英美文学、文化史及当代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研究,兼及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
在追寻达西和罗切斯特两个文学形象分别在1813年和1847年的对应历史原型前,我先谈谈流行于18至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的写作癖。《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作者从属于这个庞大的阅读和写作群体,而这个群体对男人的想像为她们提供了灵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在1813年倾心于达西这类高雅而冷淡的男子,到1847年,这类男子被冷落,取而代之的是罗切斯特这类粗野而热情的男子。在欲望的变迁下,是英国社会对男子要求的变迁,奥斯丁和夏洛蒂·勃朗特不过把这种要求带入了文学想像。揭示这种对应关系,并不贬损她们文学上的创造性,她们都是自觉的文学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再现时代的典型心理特征。
“18世纪末发生了一种变化,”伍尔夫回顾英国妇女写作史时说,“若让我重写历史,我将把它描述得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详尽,更有意义。这个变化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但她把她们的写作动机阐释为谋生,并说:“用你的智力一年可挣500英镑。”她的看法基于当时文学妇女的状况: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其经济来源,而若婚姻又不幸被延迟或耽搁,无法通过它获得生活保障,写作就成了惟一的谋生之道。上述说法更适合奥斯丁时代,那时妇女的职业主要是女仆和女工这些被中产阶级妇女认为“不体面”的下层妇女职业。她们被迫或自愿局限于家庭,而写作是惟一既可足不出户、又能获得收入的体面职业。到勃朗特的时代,出现了另一种妇女职业,即家庭或初级学校女教师,吸引了少数中产阶级妇女进入“社会”。更重要的是,复兴的清教主义赋予“工作”一种宗教伦理意义,扭转了摄政时代更世俗化的看待工作的态度。
这一时期,英国发生了一连串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把英国男人大部分想像力和创造力引向了非文学方面,而中产阶级妇女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发现自己惟一可施展才华的地方只剩下家庭。但即使在家庭里,她们也处于瓦特所说的“被强加的闲暇”中,因为家仆已使她们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被强加的闲暇”还有悲剧性的一面:中产阶级未婚女子总是成为婚姻市场昂贵的滞销品。考虑金钱和门第,她们不会嫁给下层男子,而同阶层未婚男子面临着经济压力,除长子外,得自谋生路,经过漫长个人奋斗获得稳定经济来源后,才娶妻生子,而这时往往年过而立。此外,他们还常在有姿色的女仆或女工中寻找妻子。这导致两个后果:首先,一些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被耽搁,出现数量惊人的老处女,到80年代这一状况仍触目惊心。“老处女”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大量妇女从未结过婚,”汤普生说,“例如,在1881年,英格兰45到54岁的妇女,有12%从未结婚,在苏格兰,是19%。”该数字没说明在中产阶级妇女中这种现象更突出,因为下层妇女有更多机会接触男性,如在工厂里,在婚姻态度上也更灵活。其次,更多中产阶级妇女虽结了婚,但一般晚婚。“1825年后,不识字的人比识字的人结婚更早,尤其是不识字的妇女。”格拉夫说,“然而,史料证明,识字的夫妇比不识字的夫妇生育了更多的孩子。也许,”他解释道,“识字妇女以高生育率来弥补自己的晚婚。”不过,下层妇女的低生育率,还与家庭和工厂的卫生条件有关。60年代后,随着经济、卫生条件、避孕方法的改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育率也呈下降趋势,到世纪末,每个家庭的孩子降至平均2.65个,比下层家庭平均3.76个还要少。
不管怎样,50年代前,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子女成堆(如奥斯丁家7个孩子,勃朗特家6个)。在这些家庭里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猎获富有的单身青年。这成了每个待字闺中的女子最热烈的幻想和最伟大的事业。可这并不容易。例如,奥斯丁就终身未嫁,夏洛蒂·勃朗特也迟至38岁才结婚。可以说,在妇女的这个“史诗时代”,大部分文学妇女的婚姻要么被耽搁,要么被延后,面临漫长无趣的闺房岁月,如果不想沉溺于庸俗消遣,阅读和写作就成了惟一高雅的消遣。这还有一个好处:在幻想中获得在现实中错过的理想婚姻。
还得弄清她们文学修养的来源。那时,英国虽有牛津、剑桥,但只招收贵族及中产阶级男子,妇女只能在初级学校受教育,无非是音乐、绘画、识字和缝补(到勃朗特时代,增加了地理课,下文将分析其意义),目的是培养高雅的太太,而不是有一技之长的自食其力者。甚至,保守的托利党在反对工业时,也反对妇女和下层阶级受教育,担心这会使他们产生对自身处境的意识,对统治不利。不过,中产阶级家庭中的父亲一般具有辉格党自由主义倾向,虽不主张女儿外出工作,也不希望女儿愚昧。家庭教育成了初级公共教育之外的弥补。例如奥斯丁和勃朗特的早年教育就主要得自父兄。这也主要是人文教育而非技能教育。这与下层妇女不一样。这样,从幼年起,中产阶级女儿们就沉浸在家庭文学游戏中,这是形成作家的最好条件。那个时代把中产阶级妇女局限在家庭四堵墙之间,却又为她们开了一扇幻想的窗子,无意间培养了她们阅读写作的热情和才能。“也许主要通过资产阶级家庭女性成员的白日梦,浪漫主义才得以进入中产阶级文化。”霍布斯鲍姆说。一般地说,这个时代中产阶级妇女的文学修养要高于同阶层男子。这对她们的婚姻未必是好事。
妇女文学修养的提高还体现为识字人数的逐年增加。1813年,识字的英国妇女占妇女总数的40%,1847年升至54%,她们成为女作家巨大的读者群,小说成为她们幻想世界的窗口,一种自我教育方式。这导致她们处境上的分裂:虽有很高文学修养,却被社会冷落。巴黎女权主义者瞿斯但30年代访问伦敦时,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存在着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一方面是妇女受奴役,一方面是女作家的高超智力。”
瞿斯但是幸运的,可以独自一人跑遍欧洲,而同时代的英国妇女却受到严格监护,很少离开家庭和本乡本土,只能以阅读和写作幻想性地满足自己。地理和阅历的局限,使其写作题材主要局限于家庭。如果说利维斯能从这些小题材的高超处理中发现她们的伟大,那么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就只评价了英国男性作家,而“未能解释18世纪以来大部分小说是由妇女创作的”,仅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有更好的感受力来发现私人关系之微妙处,因而在小说领域有真正的优势。”
可她们从何处了解到私人关系中之微妙处呢?无疑,私人关系中相当多的是男女关系。可除了父亲和兄弟,她们接触的男人非常有限。例如奥斯丁一生中只在1803年有过一段短暂恋情;而夏洛蒂·勃朗特虽结了婚,她所有作品却是在单身岁月里完成的。而且,很难设想奥斯丁和婚前的勃朗特在性方面会有什么体验或经验。她们的贞操观比下层妇女更保守,下层妇女在工厂里与男工频繁接触,有不少早就懂得了风月。据盖伊的研究,当时在男工与女工间秘密传阅着色情小说,而这类读物难得进入中产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避免谈到性,甚至母亲都忌讳向女儿直接谈到女儿不知所措的初潮,直到女儿出嫁前夕,才隐晦地暗示她在新婚之夜该怎么做。然而,这些似乎对性一无所知的女子,在婚后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对性的激情。上文提到,中产阶级妇女往往生育孩子更多,除格拉夫的解释外,还有一些原因:由于迟迟未嫁,她们不得不长久压抑性欲,而爱情小说又不停地刺激她们对性的好奇心,这样,一旦结婚,受压抑的性欲势必变成了狂热。盖伊说,焦虑、等待和幻想,使中产阶级未婚女子普遍患上了神经官能症。
显然,她们对男人和性并非一无所知,只是这方面的知识大多是从偷阅爱情小说及女友间秘谈中获得的。奥斯丁和勃朗特的小说显示出一种老练的眼光,能对走进视野的每一个男人作出迅速的观察和评价。这种速度,既是一种必备,因为必须在婚姻市场迅速把握行情,好把自己迅速而合适地嫁出去,同时又是一种才能,因为阅读小说已使她们熟谙此道。如果按伍尔夫的说法,妇女写作小说是为了挣钱,那么她们阅读小说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命运攸关的知识,因而为此不惜花钱。萨瑟兰提供的价格表说明了当时出版市场的情况。例如在《傲慢与偏见》形成初稿的1796年,一本平装小说的零售价大约是3先令,此后,拿破仑战争和对书籍开始征税导致书价上涨,到《简·爱》发表的1847年,才稳定在10先令上下,不管怎样,这都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星期的收入。此外,中产阶级妇女往往订购豪华大开本,而不像普通妇女去流动图书馆租阅普通小开本。
中产阶级妇女闺房中的幻想并非与闺房外的社会没有关系,她们以小说再现了时代对男子的审美要求,而暗中分享了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以文学形象强化了它。她们小说中的理想男子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达西是摄政时代的理想男人,罗切斯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男人。从1813到1847年,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对男人的欲望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最初欣赏伦敦蝴蝶,后来开始欣赏帝国鹰。
《傲慢与偏见》第一行是:“大凡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成了公理。”这确定了它的主题范围及诙谐的世俗风格。由于浪搏恩突然来了两个有钱的纨绔子,这地方所有有女儿的家庭陷入了一场猎取东床快婿的明争暗斗。班纳特家有五个姿色、修养各异的女儿。我们把聚光灯打在二女儿伊丽莎白身上,并通过她的眼睛,看看她爱上的达西是何等人物。她不像姐姐那么漂亮和温柔;读书多,却没有妹妹玛丽的女学究气;更没有两个小妹妹的俗气。这最后一点是她最大的特点。就摄政时代而言,“不俗”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也是评价一个人的主要指标。从1800到1830年,在摄政王保护下,伦敦形成了一种风气,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男人,其代表是布鲁梅尔。1815年后,多塞取而代之,他被称为“蝴蝶”,这个词从此成了纨绔子的同义词。他们着装高雅,举止脱俗,表情略带忧郁,寡言少语,冷淡刻薄,既显示出气质上的不俗,又显示出智力上的优越。他们瞧不起中产阶级,认为他们没文化,俗气,在钱眼里转圈子;也瞧不起工作,发现无所事事正是自我优越性的体现。他们追求一种植物性生活,依恋泥土,反感中产阶级动物性的生活,那种精力充沛、激情洋溢、吵吵嚷嚷、满世界跑的生活。“纨绔子的目的是成为他自己。”摩尔斯说,“这意味着严谨,节制,在生活各个方面尽善尽美,谨防对粗人来说合适而对纨绔子来说不合适的言行。对他而言,自我不是一个动物,而是一位绅士。本能反应、激情和热情,全是动物特征,必须抛弃。”纨绔子无比关注自己的身体、服装、举止和言谈,但这种关注渗透着精神性,是想使自己成为艺术品,与中产阶级的粗俗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伊丽莎白不幸出生在浪搏恩,在一个俗气的家庭里长大。其不幸感一定非常强烈,以致每当看到母亲或妹妹在外人面前显出俗气,总感到非常痛苦。“伊丽莎白觉得她家里人好像约定了非在今晚来这儿尽量出丑。”在浪搏恩,没人能理解她的渴望,因为没人像她那样熟读高雅生活小说。当柯林斯自以为胜券在握、向她求婚时,他无意间使自己成了滑稽角色,尤其当他以牧师口吻提到小说败坏道德感时,就无可救药地把自己推向了她最反感的人物之列。如果达西不从伦敦来,那不愿按当地习俗嫁给随便哪个有钱人的伊丽莎白,一定会以老处女身份终老在浪搏恩,就像她的作者。
达西的高雅脱俗、忧郁、刻薄和优越感,令人想到当时活跃于伦敦纨绔子圈里的拜伦。奥斯丁是拜伦的热心读者,我不敢肯定达西的原型就是拜伦,但肯定是摄政时代伦敦的纨绔子。纨绔子创作时髦小说是在1825年后,不过,探讨“高雅生活”的纨绔子杂志,如La Belle Assemblée、Bell's Court and Fashionable Magazine及The New Bon Ton Magazine,在奥斯丁写作《傲慢与偏见》的年代就已流行,成为评判男子的美学标准。制订这些标准的纨绔子是那些日渐没落的贵族。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动摇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根基,他们痛感自己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不过,仍有一份不可剥夺的、似乎与生俱来的财富即“贵族气质”可以弥补其它方面的亏损。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虽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在精神气质和文化修养上却自惭形秽。贵族正好利用了这种自卑感,把自己的文化标准推向极端,成为对中产阶级的心理压迫。这种心理反弹,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余波未平之际贵族文化逆流在欧洲的突然泛滥,并渗透进了摄政时代的生活方式中。
奥斯丁暗示达西来自“英格兰北部”,即开始工业化的北部地区,它也是奥斯丁的家乡,那里云集着钢铁厂、纺织厂及通商港口,形成了以城市工商阶层为主体的反《谷物法》联盟。达西和彬克莱通过长子继承权获得了大片地产,而且,随着铁路和工厂出现在地产上,还可坐收高额地租。然而,摄政时代的风气使这两个从工业化中获利的世家子弟反倒瞧不起工商阶级了。他们出入伦敦纨绔子俱乐部,在古老贵族的傲慢之外,又学会了高雅。他们离开城市,在乡下置地购房,因为城市正日益成为工商业者的天下。这些具有辉格党自由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希望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并以自由贸易取代关税壁垒。这危及到贵族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方式。然而,自由主义改革此时还只是来自北部的呼声。摄政王本人是一个纨绔子,内阁也由保守的托利党组成,从1800到1830年,几任首相全是托利党人。1815年《谷物法》颁布,建立了关税壁垒,以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来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托利党保守主义理论来自前辉格党理论家柏克,他痛感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带来的灾难,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秩序和特权,体现了英国保守主义者对田园诗般的传统英国生活方式的留恋以及对城市、变革、工业、自由和平等的恐惧。达西不把继承来的财产用于在北部城市兴建工厂,或在海外进行殖民贸易,而是在南部乡村购房置地,仅此就能说明他是一个有托利党色彩的贵族保守主义者。
“他身材修长,眉清目秀,举止高贵。”奥斯丁这样描写达西,但很快发现他“傲慢,瞧不起人、不易相处。”高贵和傲慢其实不矛盾,同是纨绔子的特征。此外,达西尽管傲慢,却没有侵犯性,因为这只伦敦蝴蝶太关注自己的风度,在自恋者的内在化中失去了向外的热情和冲动。如果他一生有什么事业,那就是在乡下购置一块地产,娶一位高雅的太太,靠利息或地租无忧无虑地生活。他当然反对蚕食他的土地和幻想的圈地运动,当然赞成《谷物法》。在这一点上,高雅的达西和不高雅的自耕农站在了一起。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即在对抗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一向瞧不起农民的贵族却在农民的守旧倾向中发现了同盟者。托利党的社会基础是经济落后、思想保守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当圈地者和工业家带着尺子和机器走进这些地区时,贵族和农民同时感到了某种危及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变革的到来,他们有理由站到一起。
土地所有者是工业化和自由贸易的最初受益者,却竭力保持传统生活方式。“英国贵族和绅士几乎没受工业化的影响,除非是在好的方面。”霍布斯鲍姆说,“随着农产品需求增大,城市(他们在这里有房产)、矿业、冶炼和铁路(这些出现在他们的地产上)扩大,他们的地租反倒有增无减。”可是,他们不把地租用于投资,而是用于纯消费方面。霍布斯鲍姆继续写道:“他宁可成为一个‘绅士’,拥有一座乡下房产,也许最终还能获得骑士或贵族头衔,在议会谋个席位,让儿子在剑桥受教育,这样就有了一个明确而显赫的社会地位。而他的妻子则成为一位‘贵妇’。”新兴城市工商业者没有地产可继承,“尤其是,他们大多不是盎格鲁人,来自缺乏贵族传统结构的地区,对旧制度没有情感依恋。这成了以新兴商业世界曼彻斯特为基地的反《谷物法》联盟的支柱。”城市日益成为工业家、商人和工人的世界,一个忙碌而吵闹的世界,建筑和街道被林立的烟囱喷吐的浮云般的烟雾熏得发黑。显然,它已不适合纨绔子居住,这些人只得迁往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南部,在日益缩小的田园诗色彩的乡村土地上寻找传统生活方式的最后堡垒。“我曾想在城里安家,因为我喜欢上流社会。”达西说,“不过,我可不敢说伦敦的空气适合卢卡斯太太。”而卢卡斯获爵士头衔后,讨厌起城市和生意来,迁到乡下,做了悠闲的绅士。撇开伊丽莎白有一群庸俗的家庭成员不谈,仅因她“有个姨父在乡下当律师、还有个舅舅在伦敦做生意”,就足以使她在达西面前抬不起头。
达西是拿破仑战争与维多利亚时代间泛滥于欧洲的那股反动思潮昙花一现的产物。说穿了,他是一个厌恶任何工作的食利者,标准的纨绔子正具有食利者的特征。然而,由于纨绔子无意于再生产,又要维持高雅排场,遗产很快告罄。《傲慢与偏见》发表十几年后,从1825年起,纨绔子开始走下坡路,从这时起,他们开始写作时髦小说,靠兜售“高雅生活”来赚取一味模仿高雅生活的中产阶级青年的钱。写作,成了纨绔子惟一可以选择的体面职业,而天真的中产阶级青年和妇女,成了他们的读者群。实际上,1825年后,纨绔子己相当熟悉中产阶级商业社会的营销术,而“高雅生活”成为一种昂贵商品。
达西不会料到他这类人日后的处境。1813年的他是一个有魅力的纨绔子,非常投合伊莉莎白对男人的幻想。比起浪搏恩众女子来,她在婚姻市场最幸运。除了高雅,她一无所有,却嫁给了最有钱、最英俊、最高雅的男子。她母亲会以商人眼光看待这桩婚姻,满意地说这是一宗不坏的买卖。而对女儿的聪明一直非常赞赏的父亲却可能没料到,他给予她的教育在婚姻市场具有极高的交换价值。我无意贬低伊莉莎白的爱情,但与当时的婚姻手册一样,《傲慢与偏见》一直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即它开篇所说的“公理”。假若说利维斯从奥斯丁小说中处处发现“使她成为伟大小说家的那种严肃的道德关怀”,那么女评论家阿姆斯特朗则以不带浪漫成分的政治眼光,发现“奥斯丁所有小说的第一行都提到了钱”,并且,“她以一个深谙两性关系的作家自居,致力于揭示性契约的真相。”阿姆斯特朗有意在“性契约”与“社会契约”之间建立一种同构,揭示其交换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对奥斯丁很不以为然:“(她)是一位贵妇,但决不是一个女人,”因为,“她对人的眼睛、嘴、手和脚的关注远大于对人心的关注。” 在她看来,对激情的忽视使奥斯丁的人物缺乏性格深度。不论此说是否公允,它至少抓住了摄政时代时髦男女的特征,即植物性生存。它有光但没有热,像人的眼睛。摄政时代的人看重视觉,但其视觉只停留在客厅,即使偶尔穿越窗口,也只落在几米远的花园里。这是一种向内而非向外的视力,不是简·爱渴望的那种“能超出极限的眼力”,“使我能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曾听说过却从未到过的城镇和地区。这眼力一次次越出英国边界,延伸到西印度群岛和东方。这当然不是英国乡间蝴蝶的视力,而是鹰的视力,殖民者或帝国主义者的视力。与《傲慢与偏见》封闭的英国乡村气息不同,《简·爱》弥漫着海外气息,它的多数人物来自海外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如罗切斯特、疯女人、梅森、简·爱的叔叔),要么将去殖民地(印度或“东方”,如圣约翰)。我注意到夏洛蒂至少四次提到“地球仪”和“地图”,海外地名更是遍布字里行间。看来她写作时被一种扩张的地理意识所吸引,这种地理学还与博物学及海外故事混杂在一起。我只提一下令简·爱最着迷的几本书就行了,如博物学家比维克的《禽鸟史》、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及东方的《一千零一夜》。这是关于海外风俗、传说、风物的知识,而知识正是权力的开始。同一时期,伦敦为赴殖民地任职的英国人提供两年职业培训的海莱伯里学校,也在传授这类知识。与剑桥、牛津偏重人文教育不同,海莱伯里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其原则是效率,不是礼仪。而且,由于它率先实行考试制度,避免了流行于牛津、剑桥的懒惰贵族风气,成为日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范例。其实,地理学和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事业的构成部分,甚至是其前锋。罗切斯特和圣约翰是剑桥毕业生,其精神却是海莱伯里的,不看重仪表风度,不留恋英国,而是充满向外拓展的激情。这也是勃朗特的激情。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爱尔兰裔身份产生的疏离感使她缺乏盎格鲁人对英国土地和旧制度的依恋。她显示出比奥斯丁丰富得多的地理学和博物学知识。中产阶级的目光已经穿越客厅窗子,落在广博的大地和海洋上,他们的脚步随后也将到达那里。
勃朗特对奥斯丁的评价,透露出风气的变化。其实,从摄政王死的1830年起,变化就开始了,它致力于扫荡伦敦华而不实的纨绔作风。也许不该夸张勃朗特的爱尔兰裔使她产生的对时髦社会的疏离感,但她的确把一种非常有个性的北部中产阶级男子带入了文学,并给予高度评价。与达西相比,罗切斯特不是长子(没有遗产继承权,只得去西印度群岛发迹),相貌不雅,举止粗鲁,有侵犯性,行踪不定,激情似火。这全是摄政时代纨绔子竭力避免的动物性。再看看简·爱,这个慈善学校培养出来的女教师,是一个孤儿,姿色平常,敢爱敢恨,更让人头痛的是,打小就反抗权威。勃朗特有意嘲讽摄政时代的高雅人士,当他们出现在罗切斯特的客厅时,她使他们成为喜剧角色。“跟他们在一起真是活受罪。”然而,这还不仅仅是审美观念的变化。
摄政王刚死,格雷组建的辉格党自由派内阁就掌握了政权,取代托利党保守派。同年,反纨绔派杂志《弗雷泽》创刊。“乔治四世已死,一个新时代诞生了。”布韦尔说。此人原是一个写时髦小说的纨绔子,像卡莱尔、狄更斯、狄斯累利和萨克雷一样,对时代风气的变化有敏感的嗅觉。这几位前纨绔子以《弗雷泽》为阵地,率先开始对纨绔子的挞伐。这意味着改革风气的来临。上台伊始,格雷内阁就致力于清除托利党设置的种种特权障碍。1832年颁布《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部分城市的有产者获得选举权),瓦解了摄政时代贵族排外主义。1846年又废除《谷物法》,代之以自由贸易政策,更为工商业松了绑。可以看出,辉格党的社会基础不同于托利党,主要是城市工商业者及满世界跑的殖民者。1833年,《弗雷泽》宣布取得了对纨绔子的胜利。然而,使新风气成为新时代精神的人,是1837年登基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日,这位18岁少女在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我将尽力完成对国家的责任。我很年轻,在许多方面没经验,但我肯定没人比我有更强的意志和更强的愿望去做合适而正确的事。”她所说的“合适而正确的事”,日后证明是帝国主义,或如她后来的首相狄斯雷利所说:“东方,是一个事业。”纨绔子或许有成为帝国主义者的才能,却没这个兴趣,因为他们迷恋英国乡村,顶多像蝴蝶一样在庄园附近优雅地飘飞一圈。他们显然不是女王希望的那种孔武有力、野心勃勃的男人,那些工业家、生意人、传教士、殖民者和军人,这才是使英国从文弱状态中振作起来的力量。女王敏锐地感到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新兴工业国对英国古老霸主地位的威胁,考虑的不是风雅,而是实力。她想恢复英国18世纪那种体现在航海家和殖民者鲁宾逊身上的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男子汉气”。看看勃朗特对罗切斯特的描绘,我们对这种理想男子就能获得一个印象:“体育家的身材”“又圆又亮的鹰眼”及“像狮子或这一类的东西”等。其中提及最多的是“鹰”,总之,是突出其高远和有力,并把“力”看得比“美”更重要(“你的严厉有一种超越美的力。”)。摄政时代的蝴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鹰面前失去了魅力。中产阶级已获得自信,为自己的形象加了冕,城市和工业也不再是需要躲避的东西,而具有了美学特征:“我渴望到有生活、有活动的地方去。米尔柯特是艾河上的一个工业大城,它准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这就更好,对我至少是一个彻底的改变。这并不是说我一味沉浸于对那林立的烟囱和浮云般的浓烟的幻想,而是,桑菲尔德也许离城太远了。”烟囱和烟雾进入了工业时代的美学。看来,我们离摄政时代的确很远了。这种美学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当罗切斯特说“瞧,算术是有用的”时,他触到了这个时代英格兰北部地区工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核心,即可测定的数量概念,它既表现为工业效率,又表现为边沁的“尽可能多的人的尽可能大的快乐”。
同样,“工作”这个被摄政时代贬低的词,在维多利亚时代又获得了它18世纪时的尊严。由于复兴的清教主义进一步把它纳入神学范畴,它甚至成了“责任”或“天职”。女王日记中出现过这个词,而它在《简·爱》中俯拾皆是。如果说《傲慢与偏见》描绘了世俗逸乐,那么《简·爱》就几乎是清教徒作家班扬《天路历程》的维多利亚时代翻版。圣公会牧师之女夏洛蒂·勃朗特不仅是《天路历程》的热情读者,并在《简·爱》中对它多处引用,而且《简·爱》的精神也是清教主义的,尽管它试图与禁欲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它的画面中到处晃动着《圣经》里的意象和面孔,如“桑菲尔德”(“荆棘地”),“冰”与“火”,圣约翰,等等。甚至简·爱从桑菲尔德出走,冒着冷雨,忍饥挨饿,在泥泞路上跋涉三天两夜,圣约翰在天职召唤下,历经海上颠簸,热切地到遥远而酷热的印度传教,死在那儿,都像征性地再现了《天路历程》里朝圣者的经历。一方面是去远方的冲动,一方面是清教徒的天职,把两者结合起来,去远方就成了天职。简·爱对待工作的态度就充满了清教徒的热忱。卡莱尔这一时期也致力于把资本主义与清教伦理结合起来,在《过去与现在》(1843)中说:一切真正的工作都是宗教。而且,在1833到1845年间,以牛津为中心,宗教复兴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牛津运动”),旨在从社会革命导致的世俗化中重建宗教权威。尽管这场运动在动机上从属于浪漫主义时代的宗教反动,有托利党人的保守主义色彩,以超自然的神秘和对权威的服从来对抗边沁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但当它被中产阶级政权压制和改造后,却为中产阶级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宗教意识形态。牛津的这些宗教意识形态家被拥护者称为英国国教主义者,被反对者讥为加尔文主义者。或许,反对者比拥护者更能揭示这场宗教复兴的实质。
不管“东方”在简·爱的想像中激起多少诗意和色欲,它主要是一个异教的东方,有时是作为市场的东方,而英国传教士和殖民者有责任去那儿完成使命,像圣约翰所说,“去扩大主的王国,为十字旗赢得胜利。”或,“上帝给我一个使命,如果我把它带到远方出色地完成它,就必须有技巧和力量,勇气和雄辩,这是军人、政客、演说家的素质,全集中在一个好传教士身上。”夏洛蒂·勃朗特幼年常与姐妹们在桌子上摆弄绘着士兵、殖民者和传教士形象的木偶玩具,幻想他们在东方异教世界创造出种种奇迹,现在,这些木偶形象全集中在了圣约翰身上。简·爱只因依恋罗切斯特的怀抱才没跟从圣约翰去印度,可她并不缺乏这种热情:“我愿意作为他的助手或同志,与他一起漂洋过海,一起在东方的烈日下、亚洲的沙漠里辛勤工作。”
简·爱没成为殖民地传教士,而成了国内宪章主义者,这两者并不矛盾。与反《谷物法》联盟一样,宪章运动兴起于英格兰北部地区,勃朗特的家乡正在这一带。《简·爱》第130页提到一天夜里,罗切斯特“要去米尔柯特参加一次公共会议”(显然是宪章主义者的秘密会议);在第272页,简·爱对罗切斯特说:“除非你签署一个宪章……”第368页提到谢菲尔德发生骚乱后,一个步兵团驻扎到该地(显然是指对宪章主义者的弹压)。难怪托利党评论家说,正是滋养了宪章运动的同一种思潮孕育了《简·爱》。其实,简·爱从罗切斯特身边出走后的经历,也是一个宪章主义者的经历。她在一所为贫苦女孩子设立的乡村学校担任教师,“我不能忘记,这些衣着粗陋的小农民,是用与名门望族后裔一样的血肉组成的;她们心中,与出身最好的人一样,埋藏着美德、优雅、聪明和仁慈感情的天然胚芽。”如果说简·爱在宗教上显示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这里则显示出一种社会平等观念。正是这一观念,使她离开罗切斯特,并在成为与他平等的人后,重新回到他身边。也正是这一观念,使英格兰北部工商业者和工人于1838年发动宪章运动,要求普选(1867年议会颁布第二个《改革法案》,部分城市的工人获得选举权)。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北部工人,其精神后来孕育了1848年革命及1893年工党建立,它最大的受益者是辉格党(1831年托利党改名为保守党,而辉格党从此被称为自由党)的北部工商业者,他们被推上政治舞台,为工业和自由贸易松了绑。难怪恩格斯在1871年指出,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英国工人阶级甘心充当“伟大”自由党的尾巴。北部宪章运动和南部牛津运动一起衰落于40年代中期,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和贵族阶级同时退下权力舞台,而作为“中间阶级”的中产阶级终于站在了自己时代的门槛上。英国海外殖民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来临,米字旗出现在珠江口。伦敦蝴蝶早已香消玉殒于英国乡间,而帝国鹰振翅而起,高飞在日不落帝国广袤的天空上。
从宗教上说,《傲慢与偏见》尽管处于宗教反动时期,却是一部世俗气很重的作品,满篇是爱情、调情、闲暇和享乐,甚至惟一的宗教人物柯林斯也被描写成小丑。而在时间上已脱离宗教反动的《简·爱》却显示出宗教狂热,甚至简·爱的爱情也带有宗教色彩。在回答为何要嫁给“比你大二十岁、得由你来伺候的残废人”时,她说:“因为我喜欢献身。”这是从基督徒的谦卑中产生的献身狂热。就像简·爱把工作看作宗教,她把爱情也看作宗教,或者说她把自己的情欲宗教化了。一个有原始基督徒倾向的宗教复兴主义者会在神秘感召下把一切宗教化,视为上帝的象征。然而,不管怎样,情欲毕竟还在那儿。到她1853年发表《维莱特》时,情欲从书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上的拘谨。有趣的是,具有虔敬主义倾向的“牛津运动”在1845年衰落后,宗教仪式反倒多起来。这导致了一种普通的伪善:人们以越来越淡漠的宗教虔诚参加越来越多的宗教仪式。外在法律和舆论比“内在律令”更多地制约着宗教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阿姆斯特朗说,“当初,夏洛蒂允许自己赋予简·爱某种程度的性自由和社会流动性,尽管作为作者她自己显然没这方面的经历,可在她后来的小说《维莱特》的女主人公露茜·斯诺这个单身女教师身上,这一切消失了。” 勃朗特确实曾有过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经历,不过,这番评论的其他部分是确切的,尽管这并非勃朗特有意所为,她不过描绘了一种变化了的社会状况。露茜·斯诺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后英国中产阶级男女的写照,他们后来获得了“the Victorians”这个带贬义的集体名称,它的同义词,“对一个人来说,是道德上的伪善,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情感上的拘谨,对第三个人来说,是社会上的势利。” 或许,都有那么一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