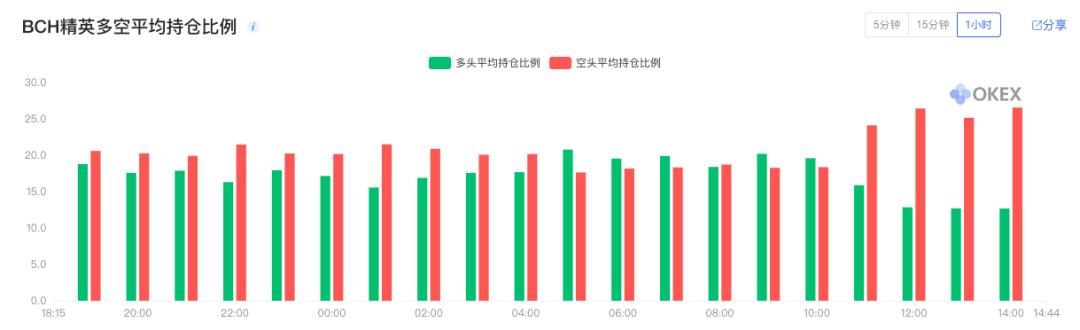老编先说
四年前,本平台推出14集连载回忆录《姚懋初自传》,比较系统介绍了周浦一批青年求艺学画、成长开拓的历程。这批浦东美术史上的拓荒者,如今都已经是耄耋老人,鲁兵老师是其中的一员,最近,这位周浦本土出生的农家子弟将这段学画经历整理成文,由本平家推出。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这批青年的崇高理想、艰辛奋斗的故事,为周浦文化自信填上一笔光辉的记录。
学 画 记(下)
鲁兵
自画像/1960年于老家
一进校门,遍地落叶,满屋灰尘,三天大扫除,才使校园有点样。看老师们,个个象霜打了一样。刚想坐下来,接上面通知,学校也要积肥!班长们跳上擂台报指标,最高达到一万担!咱班秦泽良,只报了千担。韓老师说,实事求是,千担已经不错了。
哪里去挖肥?大家想到校门口的黑水沟,纷纷拿着脸盆“抢地盘”,好不容易占到一小段,农村的同学抢着先下沟,在冰冷的浅水里徒手扒。班主任捲起褲腿也要下,被大家劝住了。老师急于要给学生补课,却又下了灭蚊灭雀的任务。正好黄昏蚊子出来“做市”同学们拿出脸盆,涂上肥皂泡,跑到飞蚊堆里去黏粘,全体大收获,每人脸盆上都有几百个幼蚊被粘上。但寝室的蚊虫居然不见少,有的还钻进蚊帳里!积肥的结果是每班没有超过百担,而且堆在河滩没有被送走,因为它是化工厂的排污泥!
灭雀运动只忙乎了一天。那时全闵行总动员,每块地都有人把守。工人爬到房顶和烟囱上摇旗呐喊!我被分在”追击兵”,拿着脸盆边敲边跑。校外农田里,佈满了我们的同学,那场面,真像古战场。但从早上到响午,我却没见到一只麻雀!
终于消停下来,师生全努力,补习拉下的课程。碰到俄语课,我们几个浦东小兄弟常常挨朱老师批,一个卷舌音,居然学了二个月还不利索。“星期天”的音节特别长,汉语拼音没学好,用中文注音搞不准!真是很头痛。嗨,俄语星期天,应该叫“袜子脱拉鞋子里”不就记住了?老伴笑着补充。快七十年了,一个穿越,我们还记起这些事!对不起,跑题了。反正,俄语老师不看好我们,上课只是应付着,保及格万事大吉。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我们刚完成期末考试,整理行装准备回家,却突然接到通知:高中班的全体同学,开赴农村扫盲。全班同学 立马背起蚊帐席子,来到黄浦四队的院屋里,由生产队长分配任务。村民中妇女文盲最多,识字的没几个。女同学的任务特别重,三个人承包一个,把带孩子和家务活全部包掉。队里还给文盲们记工分,因此,社员们主动积级。可惜我的脚背感染,疼痛难忍,红肿低烧,加上蚊虫猖狂,整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吴如菊和薛传玉二位女同学十分关心,商量着回校想办法。这来回20多里我无法动弹,只能颠着一只脚对付一个半文盲。直到傍晚,她们二人汗津津地带来了药膏,酒精和纱布,把我的肿脚包扎起来。后来才知道,学校医务室没有人,吴如菊设法从家里搞到了消炎药。整整十天,扫盲完毕,我的脚正好消肿伤愈后,已能走着回去。时隔64年,恍惚犹在昨天...
扫盲结束,课程也告一段落,我又回到周浦。正好是种二季稻季节,我正在秧田里拨秧,给社员们讲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喧哗声,水花声融合在一起,使大家忘了疲劳。大哥从田埂上过来,叫道,“阿四,到汇龙桥送秧去!大队后浜有船”。于是,我往大队部去撑那条死狗般的水泥船……。
那年夏季真辛苦,我的情况还算好,偷空能往镇上跑。从镇北到镇南,从南八灶到东八灶,兜了一个大圈子,画友们一个都碰不到。大街虽热闹,商店却关了门。私人商贩取缔了,供销社也上了门板!转到原来菜市场,只见炼铁的高炉在燃烧,不一会,通红的钢水流出来,围观的市民鼓掌欢呼,抬起冒烟的铁块,敲锣打鼓到镇政府去报喜了……
又接到返校开学通知,並要求公社对你假期表现有鉴定。不得已,到村里开了一张证明。到学校才发现,很多人没有开证明也报到。学校在搬家,寝室在整理,终于可以离开压在头顶的大烟囱了。我随大伙一起,扛起课桌就往新校跑。
新老校区间没有公路,只有田间小道相通,雨后道路泥泞,搬运很是艰难。好在人多腿勤,往返频繁接力,不久安排就绪。初中班先前就在那里,高中班在新楼落成后才开课;食堂变成瓦房,简易洗澡房修起来,宿舍在后面二層楼,早晚自修书声朗朗。操场大多了,标准的400米跑道,紧临着沪闵公路和街道交叉口。國旗升起来,一所象样的完全中学!比周浦中学气派多了。但食堂伙食没有好转,不象公社那样吃饭不要钱,七元伍的伙食费每月提前交,八人围着四方桌,集体大锅菜。大家一脸菜色,饥肠辘辘。趙福官时常牢骚,怀疑肥胖事务长中饱私囊。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闵行中学第一炉钢炼成了!新班主席朱金荣有办法,大塔车里装满了一车生铁和耐火材料,金国义他们冒雨推进了学校;学习委员蒋之雄的一篇“炼钢逞英雄”战斗诗,在班级牆报上刊登。我被分配在耐火材料组,和秦之江、张运等同学一起,从原校区的烟囱下搞到了一车耐火砖,在礼堂里将它敲成粉末,提供给秦泽良他们砌补土高炉。整个炉前操作我只参加了一次。因为我已经病了,不参加晚自修,常在寝室里练习气功,兴趣开始始转移,到处尋找百草,理想着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或郎中……
美国佬不安宁,派兵侵占黎巴嫩,中国提抗议,我们也上街游行,从新街到老镇,打倒美帝的口号此起彼伏,吴水章把嗓子都喊哑了:“搞建设要钢,钢铁就是力量!“纸老虎”千万吨,英国佬千万吨,我们铆足了劲一百万吨。五亿人口齐上阵,赶英超美争上游,形成了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壮观场面。农村搞深耕密植,亩产十万斤登大报。村民吃饭打冲锋,干活开始磨洋工。那年水患旱涝刮台风,食堂开锅吃力。大哥家年终分配倒扣六十元!幸虧老爸给他补平了窟窿。他辞去了民兵队长职务,成立了农机排灌站,固定了工分补贴。但二哥在上海药厂被定为“指标右派”,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这一打击,令父母寝食难安,思想不通。全家最光荣的是老三,在东北海城当砲兵,他是最后一批志愿军,提防美国佬捲土重来。因此,我家的门棚上,也有《光荣人家》一个牌。
我的病不见好转,父亲专程骑车到学校,给我订了三个月的鲜牛奶,又叫二哥伴我到上海医院检查,查不到什么,倒是牛奶起作用,使我的胃肝部不适逐渐消失。直至一九七二年,旧病复发。检查怀疑有血吸虫病,找到从医老同学,在血防站检查后结论:曾经感染过血吸虫病!上海地区普查时,很多农村出去学生和军人漏检了!在当时的上海郊区农村,活下来也不容易!
时间已到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平静没多久,新的花样又来了。先是到北桥乡帮农民深翻,师生浩浩荡荡,要挖地一公尺!农民不积极,学生做实验。班长弄来了几把铲子,众人象挖壕沟一样把土翻上来,整整一天,一堤地也没完成。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慢吞吞地走回学校。几天后,各班把操场北边的空地划分了,我班分到沙坑大小一块,大家象土拨鼠一样挖了一米多深!凌铿、陆中琴等女同学抱来青蒿野草,男同学挖来人真肥,然后盖土撒密种,大家焦急地等待发芽。雨后,各班试验田郁郁葱葱,好看!城里学生很开心,我却泼冷水。他们说,“鲁四老爷促退派”。小麦长得一尺高,土里开始冒热气,”烂根了”!我对秦之江说。几天后,叶子烂了,麦杆倒伏,没等麦穗抽出,全部伏倒死光,白费了二斤种粮!这些我们都反对,知道,但老娘大哥都顶不住,我们学生能反对?
学校基建还在扫尾,一些工人在修补,中午躺在礼堂乒乓桌上,打着赤膊露着腿,横七竖八,睡相不一。我赶快拿来速写本,从头部或脚部开始画躺势,观察人体透视变化的规律。他们睡得很熟,好几次都没有被发现。不能丢掉速写本,这个本事对学医也有用。
这一年,发现了陆寿君也喜欢画画。他常提起上海的名画家,谈到蔡一鸣的画怎么了得。后来才知道,蔡一鸣是他同乡,擅长连环画。陆寿钧以前不露声色,这下找到了知音,二人常在一起讨论,一起听上海画家讲座,一起画大跃进的墙头画……。
一九六0年的春夏,闵行中学从梦幻中苏醒过来,毕业和升学就在眼前,各课老师拼命赶进度。高考分类的志愿已统计,三个类别里,理工科志愿者最多,文科和医科人数相当,符合我国人才发展的需求。同学们拼命复习,气氛十分紧张。我的志愿在医科,而且是中医类,因此,加紧复习人体解剖生理学。
大概在五月份,我从街上回校,路过传达室,听见里面在喧闹,进去一看,是上海艺术招生办的人员在宣传,陆寿钧和王汉杰已在那里咨询和活动,很多初三年级的同学在取表格,初中文艺部长何芳仙也在那里,气氛热闹非凡。陆寿钧和何芳仙见我进去,过来对我說:“你是文艺部长,你要为我们这些考生和学校交涉,校部不同意我们报考,说影响升学考试”。这本身是件大好事,我爽快的答应,转身就出门,陆寿钧却拉住我:“你不是画画吗?你应该带队,伴我们一起去考!”
随即向招生组的人介绍,並拿了表格给我填。我想也是,艺术高考和普通高考相差二个月,相互不冲突。随即填了表格,到寝室取了照片,交了上去。在报考志愿上,我只填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可以填报多个学校和专业)我又跑到老师办公室,碰到外语朱老师管事,他坚决不同意。又刚好新分来的、扎着二个小辫的助理班主任朱老师,她说:“这是好事啊!走,找韓老师去!”
韓老师把我带到教务处,我谈了情况,並郑重地说:“我是代表学生会提出要求,保证不影响升学考试。”教务处同意了。並叫大家积极备考。
我立刻给吴进才写了一封信,叫他以同等学历去报考。听说这傢伙唱戏入迷,已经成了镇上的名角,崇拜沪剧名牌王盤声。他回信说以后再考虑,但叮嘱我作好准备,说估计会考石膏像,提出了考试中的注意点。
我们重视起来,找到初中美术老师。他把道具室的钥匙交给我,叫我自己去挑选。道具室里乱糟糟,二个小石膏像积满了灰,我从体育道具堆中把它抽出来。这里转身都困难,更谈不上作业。就把模型搬到寝室,放在窗台边练习.画得实在不理想。不知道陆寿君是怎么复习的,我们不在一个寝室,各自想办法。一个星期后,我还是复画静物,将同学的茶缸、水瓶、书本做样子,又到文具店去买了一盒12色的水彩颜料和羊毫筆作淡彩练习,总共花了一个月时间,艺术高考时间就到了。由于人数较多,大多是初中部考舞蹈的,学校包了一部客车,把我们送到了上海戏剧学院。
上戏在华山路,校园里热闹非凡,考生们围在窗外观看练功。初中部的女孩子们,被练功房内的基础练习迷住了!那整齐的举腿、旋转和腾空翻跳,使她们激动不已。晚上,我们住在木地板的教室里,一张席子,一条被单,舒展身子躺下来,感觉象到了天堂一样!
第二天开考,上午素描。进入考场,已有十多人在动手,考位是围绕式,显得很拥挤。模特台上是一组静物:醬油瓶、洋葱、黄瓜和瓷碗。教室偏暗,顶上一盏普通电灯。大家的画位光线比较均等。我观察二分钟后打轮廓,花去二十分钟,就开始涂明暗。发现瓶子的本色最深,除了高光外基本呈墨色,就用软铅铺排开来,比较着逐一画到黄瓜、洋葱和瓷碗,总体上把它们拉开对比。一看手表,过去了一半时间,就画细部,包括瓶颈开口的细节,基本上没有用橡皮。再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想到曾经讨论过,素描不能画得过细,过光,会给人一种发腻感,就停筆交卷,离开考室,转到主樓看舞蹈考试,看到一位老师在测量考生的小腿。舞蹈演员对身材和腿的粗细十分严格,这是重要的关口。身材不合,其它免谈。
下午考色彩,来到考室时,发现有人背着油画箱。这下糟了,我从未接触过油画,也没有油画工具。不想监考老师說,不收油画考卷,因为无法等干,只用水粉和水彩考试,而且纸是统一发的。背画箱的人着急地在走廓里徘徊。
考试是原来教室,原来的静物,原来的光线,原来的画位,只需把它画成色彩的。思前想后,我只帶了水彩色,而且水彩极少练习,怎么办?淡彩,对,素描淡彩,保证了形又有色彩。就迅速动起手来。由于上午画过素描,复画就快多了,画到七分深浅时开始上淡色。尽量不用粉质色,以免盖住深色。中间歇了二十分钟等纸干.然后用铅笔加強一些重点。这种方法我在速写中进行了多次。吴进才在应急时候甚至用口水将未干的钢筆墨水化开。这次我第一个交卷,因为多涂了会发糊。
出了考场,长吁了一口气,这是初试,等待发榜。榜上无名者,不需复试。陆寿钧考中央美院,不在一个试区。听说上海美校也设考场,考生真是不少,我的准考证是二千七百多号了。
三天后发榜,我抽空到父亲那里去汇报。老爸工厂在法华路,已去过多次了。我在传达室打了电话进去。他出来拿了宿舍钥匙交给我,叫我在宿舍里等他中午下班,並给我带饭来。我就躺在父亲宿舍给吴进才写信,告诉他考试的过程。
中午父亲帶了一盒饭,里面一块大排红烧肉,吃在嘴里暧在心,望着父亲油腻的工作服,不禁眼眶溼润。五个儿子,他都要操心关照,多大的压力啊。父亲特别看重我,我若升学成功,这是鲁宅第一个大学生!
我这老爸,技艺高強,抗战前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技师推行新农具,师父是美国人和德国人,有的机器另件都用英语。他为中國空军修飞机,松沪会战时是红十字会的,在槍林弹雨中救死扶伤。家里的杂用工具都是自己做,还教会了我们一些技能,使我们兄弟们都有较強的动手能力。那一年,父亲从外婆家的客堂里,把三十年前的洋抽水机运来,经他修理后重新发动,为生产队防旱抗涝起了大作用。大哥也在这个基础上,转到农灌站工作。
下午下班,同样带了飯,父亲的工友兼室友也进来了。交谈中,那位师傅说:“你父亲培养出个大学生,真是不简单啊,将来毕业出来起码当个‘那摩温’!喔,不对,是个领班工程师,高工资!”父亲笑笑,”现在还不知道呢,大学学技术,将来谋个饭碗!”
回到上戏,已是晚上了,洗了澡,倒头就睡。第二天,到上海交大去“侦察”。因为听说闵中的统考地点设在交大。门房放了我进去,里面世界确实不小,真不负名牌大学的盛名……。
第四天早上,听说初榜已公布,我到主楼侧墙观看,只见人头攒动,几百人在围看,根本挤不进去,我只能先去散心。九时后,返回公榜处,只有几十人了,挤了进去,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和考号。看初试录取人数,一共四十一名。这是全国四大美院“中美”、“浙美”、“广美”、”鲁美”在上海考点初榜的总人数,接下来,还可投考各类美术专业院校。上海是个艺术人才的集中地,全国招生的院校都设点,考生机会很多。
碰到陆寿钧,他说考上了上海电影学校美术系,而且一榜就命中,令我很是羡慕,他可以不离上海就读大学了。
复试就在初榜第二天,科目是创作、语文、外语、口试,都是相关院校自己设立的,与大学统考不相干,无可预习,大家都毫无准备。
第一天是命题创作,考桌之间有距离,不准交谈商量。考题是《最有意义的一天》,发了一张铅画纸和一张草稿纸,时间三个半小时。考室鸦雀无声,连手表走声都听得到。画什么?这个命题不具体。想高中生活:学习、劳动、歌咏比赛、上街游行、消灭四害、义务劳动,喔,对啦,义务劳动!闵行建设中,参加多次义务劳动,一切历历在目。勾草图时,发现自己从未画过群像!这憑空画出群众场面有多难!干脆到正稿上起筆,在画面中部偏右画上一个扛木头的青年作主角,根据近大远小的原理,在他左右画上挑土、挖土、搬物的人物,画面活跃起来,顿时添了信心。再在地平线处添上锯齿形的厂房,把主角的轮廓线加深。画手部姿势时,用自己手比划参照。感觉差不多了,就给人物和背景施加了薄薄的淡彩。
时间过去了二个半小时,站起来交卷。看后座,正对着白卷在叹气!我赶快离开考场,在空地上对天长吁:这创作,实在太难了!画得我出了一身大汗!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虽不在普考的复习大纲之内,但难度不大,也没有离谱。沒有作文,只有一段读后感,做得很快,也提前交卷。下午是外语,真有些麻头。少量的语法造句之后,就是一长段俄语译成中文!高中俄语课本上从未见过,词汇又生疏,又没帶词典,这下卡了壳。责怪美院不按常理出题,只能硬着头皮跳着词汇翻,感觉到似乎描写像列维坦一样的画家的写生经历,连蒙帶猜地写了一些。这之中,还碰到了音乐、奶酪、烏鸦等词汇,无法联接。干脆交卷算了!
第三天是面试,大家很早来到试场外等候。有些人在议论,说口试很难,教授问题很刁钻,会狼狈不堪。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只看到应试者出来,谁也不理地走了。大家安静下来,听着叫号声……。终于叫到我了,进入一间小试教室,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位年轻女士。想必老的是教授了。
我整襟端坐。老太太看了一下表格,问了我的名号就发问:“你为什么喜欢学画画?”我一怔,(因为她是一口杭州话,把学画画说成学哇哇。)但听懂了她的话,想到和茅新友他们讨论过文学和绘画功能差别,只等了二秒钟就答道:“因为画画能夠刻划和表现出具体形象,文学描写再复杂,也不会在纸上出现形象,所以我喜欢画画!”老太太笑了,显然比较满意。紧急着又问:“你喜欢世界上哪几个哇家(画家)?”这个好答,我从列宾、苏里可夫,希施金,列维坦到中国的徐悲鸿、吴昌硕……老太太招招手,”可以了,夠了。”我停住,其实我就知道那么多,我不提达芬奇等文艺复兴三杰,因为那是初中美术课本上都有的。
从考场出来.我立马收拾行李,搭乘徐家汇的客车,直接回到了闵中。离高考还有一个月,大家拼命复习,我还动员陆志明和我一起投考第二类,着重复习生理学……。一转眼,考期巳到。老班长和吴水章定了留校,他俩已在为考务奔忙,包了二部大客车,浩浩荡荡开进了上海交通大学。下午,我去了上戏艺术招生办,询问美术录取情况,他们很热情,说是正在评卷选拔过程中。叫我留下考点和考号,安心参加普考,有情况会及时通知。高考很顺利,没有刁难题,老师吓我们,搞得大家紧张。最后一门生理课,我正在答题,门口突然进来一位老师,喊到我的名字和考号,叫我听传达室电话。我走出去,他也跟着我,二人一起奔到大门口的传达室,我拿起电话就报名。从对方的口音上,听得出是接待我咨询的女士,她说:“恭喜你,你已被录取在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考虑到你在参加大学统考,现在你决定,如果你读浙美,我们就把你的高考名额划棹,如果放弃美院,我们就把你的名额让给别人。”
这是大事,得报告父亲大人!我回答说:“等二十分钟行吗,我得考慮一下回答你。”她同意了。我立马给父亲厂的传达室打电话。五分钟后,父亲声音:“什么事”?从听筒里的喘息声,知道他是跑来接电话的。我简短地谈了情况。父亲略等了一下说:”既然你已经录取了,那就去读吧!杭州环境好,对你身体有利;四川南京太远,回家不方便。你说呢?”“爸爸意见有道理!”我回答。然后我拔通了上戏招办的电话,把读美院的决定告诉了她,她說:“好,那你回家等录取通知。”我掛上电话,转身对监考人说:“回考场,我把卷子做完行吗?”他没有说什么。因为沒有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以前,我得防着点,以备将来可查。
离开了考场,我卷了行李回到了闵中,弟弟已在学校等我了。他说:”爸爸回家了,妈妈叫他帮我搬行李”。校园静悄悄,巳经放假了。我们兄弟二人商量从老码头乘船,他想看看黄浦江的风景,並希望能夠看到江猪(一种白鳍豚)。但很可惜,船到杜家行江湾处,没有见到江豚,只三年,这种景观消失了。
回到周浦,见爸爸请了二天假,买了一只蓝色的人造革手提箱,二件宝蓝色的翻领汗衫(现在叫T恤),妈妈请了老裁缝,替我们兄弟几个做衣服。我穿了母亲手织的格子服,在二哥婚房的衣镜里照,发现自己的形象不差,有老爸年轻时的风度。怪不得宅邻以为我考了电影演员!
公社食堂停了,各家自己起伙。市场供应紧张.开始实行票证。一场大雨以后,老爸从河边的水沟里抓了一篮泥鳅,说上海人很喜欢吃,营养丰富。但浦东乡下人一般不吃。买不到肉,我们第一次吃这野味,发现味道鲜美极了,一点都不亚于黄鳝!七月份,正是双抢季节,大哥已调到排灌站搞水利去了,生产老队长吴根林,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拼命抢收抢种。公社已对各队定了指标、要完成水稻、棉花、蔬菜的上交计划,否则就要扣掉留存!上海的供应计划达不到,农村跟着受累!农民都知道这种相依关系,就必须与老天拼命!
接到正式通知以前,我不去找画友,闷头帮母亲为生产队出力,拿起镰刀扁担,参加搶收搶种.。给棉花喷农药,挑蔬菜到收购站交指标。今年的冬瓜长得好,可收购价格很便宜,一担冬瓜伍角钱!忙碌中碰到了初中同学陈宝兴、沈林川,他们都已成为队里的生力军。林川已任生产队会计,向我诉苦社员争工分难弄,参加农业生产是國家对初中生的号召,农村需要小知识分子。他个子小,身体弱,做得很辛苦,还想考出去。为了回报父母,只有埋头苦干,分配什么,毫无怨言。插秧,割稻,挑谷,送肥,小队长一个号令,我二话没说。得到宅邻和哥嫂婶婶们的称赞,一直到八月初,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大哥拿着一个信封说,通知书在大队里耽搁了三天,他们忙昏了,我去了才发现。我赶往周浦文化站,正好吴进才在,打开通知书,盯了我半天,激动地说:“想不到你这个黑赤赤的乡下人,考取了浙江美术学院!而且是油画系!”我说,“全靠师傅们栽培”!他高兴起来,向站長龚文龙介绍,搞得围了很多人。吴进才说,回头我通知大卫、懋初他们到你家里来洗尘,谈谈报考情况。
没几天,他们来了,大卫还带了一只琵琶,在我们弄堂里坐定。婶婶他们一看,来了一个沪剧明星,在众乡亲的要求下,吴进才唱起了滩璜。真有点像沪剧名角王盘生的味道。妈妈说,进才阿弟唱得好,四乡五邻都知道!进才说,周浦剧团解散了,我正在找工作呢!众人叹惜,遂渐散去。我就讲述报考的过程。当我谈到“你为什么喜欢学哇哇”杭州腔的时候,大家捧腹大笑。吴进才拿起速写本,对着我画起了速写;张大卫抄起琵琶,拨动琴弦:《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在老屋的弄堂中传响。一曲弹完,紧急着是急风暴雨般的马蹄声:《十面埋伏》!众人振奋起来,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把浦东的美术事业进行下去!吴进才叮嘱我,到美院要依靠秦健军,把功夫学扎实为浦东周浦争光!
就这样,我终于踏上南去的列车,奔向美术学子们想往的艺术殿堂……。
文字校对/周浦晚睛书画会/王力勇
2022/9
编辑/排版 家灵
坚持是一种信仰,转发是最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