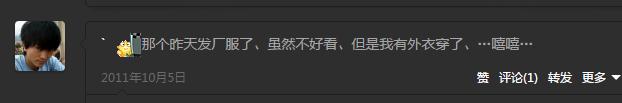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病魔如同风暴,占据着我们的生活。在疫情改变了大多数人日常节奏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既往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回归。比起疫情刚暴发时的惶恐和不安,响应日趋严格的封闭式管理措施,尽量不出门成为每一个人为这场灾难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宅居在家中的生活,其实是“不安心”与“安心”的胶着并存。正如唐史学者冯立君所言,“不安心是因为疫情严峻,担心亲朋好友的安全;安心是你根本出不去,只好读书写作。”这场不同于以往的严峻疫情,那种“距离很近的压迫感”,让冯立君一度“全天总是盯着微信和新闻”。
也许是因为疫情期间的紧张心态,和先前半年的高密度节奏,眼下,他的阅读和写作也有一种进入疲劳阶段的感觉。冯立君说:“学历史的人,面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常常迷失,所以文学作品是个补偿,希望能够找回历史学者的清醒。”
“学者没有什么节假日”是冯立君的坚守,他将自己的生活分为读书和读书之外的事情。他希望将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推荐给更多读者,这是一本知识性很强的书,写作范式也很值得学习,特别是关于病菌那一章,写法十分精妙,“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种阅读快感”。

冯立君,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东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唐代文化史学会(西安)理事、韩国百济学会海外会员等职。研究方向为中国中古史、中外关系史、中国民族史。著有《唐朝与东亚》,译著有《古代东亚交流史译文集》《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等。主编《中国与域外》集刊。
阅读时常常忘却眼前一切,进入历史世界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如何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读书和写作呢?
冯立君: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们有一个教诲,我一直遵守,就是学者没有什么节假日(包括春节),每天都不能释卷。香港凤凰卫视制作过一期节目,耿世民先生除夕除了和家人吃饺子的那个时间,其他时间和平时一样,看书、做研究。我不敢向前辈们效颦,但也基本在读书、写东西,当然也陪家人和孩子。
春节期间,本身是大学寒假的延续,没什么不一样。除了父母都来到身边,其他如常。加上疫情,更是居家读书为主。我的节奏是上午脑力较好的时候进行深度阅读和写作,这是长期自我摸索出来的,一旦午饭之后就开始犯困,除非特别令人兴奋的论著和题目,一般效率都会下降,只好稍事休息。所谓休息,其实就是读书写作之外的任何事儿,比如陪儿子玩耍,看看电视,甚至包括吃水果——一个痴迷学术的人的生活,除了学术就是休息。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选择这些书?它们给了你什么启示?
冯立君:今年的春节期间,因为之前的半年写作和阅读非常高密度,所以进入了一种疲劳阶段,相对阅读和写作都慢下来,当然这也和疫情期间的心态有关。
啃读了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这本著作。和当下没有关系,因为是既定的工作内容。要做精细的阅读,逐字逐句,查核史料,并做翻译。这本书是一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与东亚世界二者关系的演变史,特别是形成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思想与实践历史。我以前既反复研读韩昇先生翻译的堀敏一先生作品(比如《隋唐帝国与东亚》),也编辑引进过堀先生其他作品(《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等),但这本有所不同,它既具有完整性或曰系统性的知识,也具备理论的张力,对我的启发在于学术写作的精心结构,同时也有具体内容的新知,阅读过程感觉很充实、很幸福。常常忘却眼前一切,进入历史世界。

《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堀敏一著,岩波书店1993年版
我手中同时有日本原版和韩文译本,对照阅读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日语和韩语都属于和汉语截然不同的阿尔泰语系黏着语,彼此之间的语法在我看来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因为东亚之间天然的历史联系,二者都有海量的汉语借词。所以,在面对这样一本讲述东亚古代史的论著的两种语本时,我的阅读快感也成倍增加。而且,我常常劝掌握了韩语或者日语的学生们,最好兼通日韩两门外语,这比兼通日英或韩英要容易得多。当然,要是兼通日韩英就更佳了。
其他的都是专业功课,就不说了。
人类的很多麻烦,历史上都有类似的例子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吗?
冯立君:最开始比较喜欢看北京卫视新上映的《新世界》这部剧,剧情也算紧凑,最喜欢的是台词比较讲究,比较有内涵,可见编剧有生活观察和高超还原。这种感觉,在多年前看《大明王朝1566》和《北平无战事》时更为强烈。可惜,这部剧后来的剧情多少有点虚,或许和我不耐烦有关?
后来主动看了《日瓦戈医生》,三个小时,大半夜自己安静地看,还是很震撼的。学历史的人,面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常常迷失,所以文学作品是个补偿,希望能够找回历史学者的清醒。
又重新看了《大秦帝国》第一部(以前读过小说),拍摄手法比较传统,但节奏和呈现是很棒的,看了一整天,因为太太要在家工作,我只好边陪孩子,边放着这个剧。对我要写作的一个题目,突然有了启发,哈哈。而且,嬴渠梁和卫鞅第三次谈论强秦国策时也令人非常激动。原作者孙皓晖是西安一所大学的教师,后来干脆辞职去写这部鸿篇巨制,很令人佩服,这也是我愿意看这部作品的一个原因。它是一个写作者用生命去写就的佳作。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冯立君:特殊时期的写作,没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心怀天下,同样会既不安心又很安心:不安心是因为疫情严峻,担心亲朋好友的安全;安心是你根本出不去,只好读书写作。历史上,被流放的知识分子最后一件幸运的事儿就是可以安心读书,因为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位黄永年先生,他在“文革”期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逆水行舟,很是令人钦佩。
新京报: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冯立君:持续关注,紧密关注。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多年来一般不记琐事,但最近我也写到了。非典时期,与现在不同,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在北京工作期间,禽流感等也没有现在这种距离很近的压迫感。但我从初五开始,摆脱了全天总是盯着微信和新闻的紧张状态,开始以读书写作为主,定时翻阅一些公众号的信息发布。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是否有什么政策建议?
冯立君:我是做历史研究的。人类的很多麻烦,历史上都有类似甚至相同的例子。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相信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只是个时间问题。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冯立君:最近我还看了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我手中是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老版,读了病菌那一章,他的写法精妙,接着又读了关于汉字的那一章,对于理解我关心的古代中外交流史颇有启迪。以前做编辑时,特地调查过这本书,它的译本不仅众多,而且也都高居畅销榜前列。所以,他的写作范式很值得学习。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
关键是他的书知识性很强,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种阅读快感。在全国抗战疫情的时期,读读这本可以划入所谓“科普”类的畅销书,绝对是值得。至于有助于精神安顿的,那就见仁见智了,经过人类数千万人口检验、数百年淘洗的经典都值得挑选阅读。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徐伟、徐悦东
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