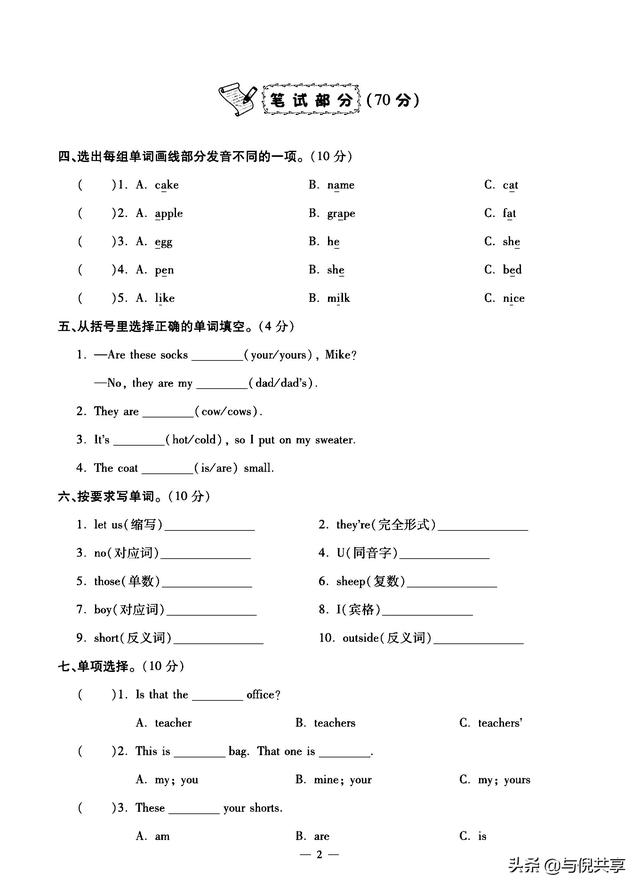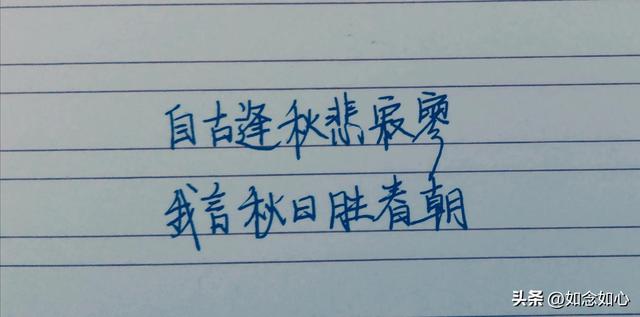文|卞文志
早些年,芒种一到,躲在乡村场院一角闲了一个冬春的“碌碡”们又开始忙活着登场了。
用大青石雕琢成滚圆型的“碌碡”们,是帮生产队碾麦子的,社员们将田野里金黄的麦子收割回来,摊在几亩地大圆圆的场院里。
经过阳光暴晒之后,社员们五人一组扯起绳索,拴在已安装好木廓子的碌碡上,喊着劳动号子拉起几百斤重的碌碡,脚底下踏着厚厚的麦穗,在圆圆的麦场上一圈圈碾压着。
十几个“碌碡”吱吱咛咛的声音此起彼伏,与社员们的劳动号子交汇一起,在场院里汇成一支震天动地的丰收乐曲!

曾经看过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老农民》,剧里有很多陈宝国带领乡亲们拉着碌碡碾麦子的画面。可是,他们拉着碌碡碾压的是春天田野里青青的麦苗。
看了这些情节,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在我们鲁南地区,碌碡是用来压麦子脱粒的,他们怎么碾压起春风中正在蓬勃生长的麦苗呢?难道是编剧或导演搞错了,还是剧情发生地就是这样的农事?
反正我相信,碌碡是用来脱粒的,不是用它碾压青苗的。
从前,农耕条件落后,既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用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也没有现在的收割机,那时候熟透的麦子上场后,只能用人拉动的碌碡脱粒。
记得当时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将割下来的麦子用肩膀挑到卖场上后,用铡刀将麦穗铡下来,然后铺在光光的场院上,经过烈日暴晒后,再用杈耙翻动上几遍。
当麦穗发出金属般的声响那便是干透了,之后便是五个人齐心协力拉起一只碌碡,十几个碌碡在宽阔的卖场上转着圈子,碌碡吱吱咛咛地压着饱满的麦穗,姑娘们嬉笑着用杈和耙在后面翻动着,加上男劳力的劳动号子声,在村头的场院里此起彼伏地汇成一支支交响乐曲!
麦子经过碌碡许多遍的碾压,麦粒就从穗子上全部脱落下来了。老年社员和姑娘们把麦穰挑到一边,把与麦糠掺在一起的麦粒扫成堆,然后打扫出一片干净的场面,让有扬场手艺的社员用木锨迎着风口一锨锨地扬。

经过几遍反复扬场后,麦粒就与里掺杂着泥沙麦糠分离了,扬场的社员赤着大脚丫,踩在脚下金灿灿的新麦中,一种收获感油然而生,他们光着膀子,用浸满汗水的毛巾抽打桌满脸满头的麦糠和泥土,一边跳跃着,一边哼唱着。
那一刻他们似乎成了夏收麦场上的王,人们扬着收获后幸福的笑脸,倾听着他们的歌唱,在大片金灿灿的麦粒映照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闪烁着感恩收获的光芒。
扬场不仅是个力气活,而且还是祖传的手艺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体劳动时,社员谁会摇篓、扶犁、扬场,谁就是农技能手,生产队不仅给的工分高,而且还是农家的座上宾。
那个年代,家家都有生产队分的自留地,秋天种麦子,夏季种高粱,农家都要请他们摇篓播种,几个农技能手很难请到手。
生产队和农户为了抢农时,麦收后的地里都要急着中高粱和大豆,农技能手们白天在生产队忙完了,傍晚或天不亮还要帮着左邻右舍播种。
有些农户为了不误农时,就腰里揣着三两包一毛五分钱一包的“普藤”牌香烟,给农技能手送上门去,恳请他们挤点时间帮着将收割后的麦茬地里播上大豆或高粱。

那年回老家,村子西头那片打麦场已经不重要了,场院里建了几处农舍,村子里到处都是光光的水泥马路,可是在父亲居住的小院里,却还保留着打麦场那样的场景。
老父虽已驾鹤西去,他遗留下来的杈筢扫帚和扬场锨依然陈列在农具棚的一角,门外,是一片十几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靠墙边放着一只磨得光滑的碌碡。
几年前,父亲是那样执着于他的那方场院。那些直接进入场院水泥地上的麦子,被父亲那双骨节暴露的大手精心地侍弄着,仿佛他在侍弄着自己的孩子。
他用双手拉拽着碌碡来回滚压着,脱粒后,再用扫帚一遍遍扫去麦粒间夹杂着的麦糠,直扫到不见一星杂秕。然后再用那只陈旧的竹筢子给那些麦粒翻身,篓起一条条的小垄,好让阳光和风可以尽情地去抚摸那些金色的麦粒,把麦子中的水份带走……
就是因为这些记忆,父亲走后,我依然保留着父亲在时收获麦子时的情景。每次回老家,看见父亲使用过的杈筢扫帚扬场锨,我就会想起一生艰辛务农的父亲,同时也让这些古老的农具留在心里,在我们这一代的记忆中不被失传。
壹点号 人文齐鲁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