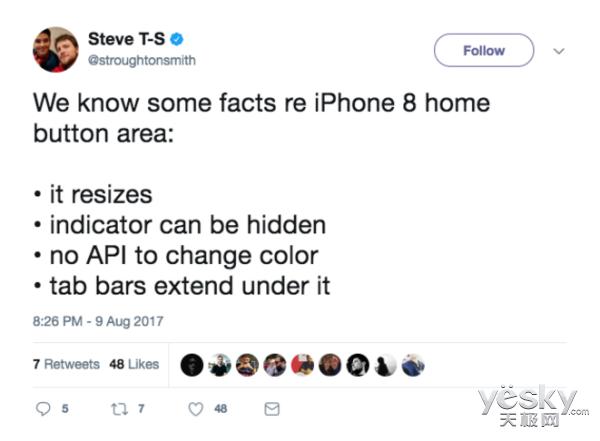这是为一本新著撰写的前言,一孔之见,就教方家。
在笔者此前出版的三部著作即总书名为《探索自然之谜》之上册《天地自然》,中册《生命起源》,下册《地震成因》中,对许多重要自然现象做出了不同于教科书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主流观点之所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答案,根本原因还在于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化学理论仍不完备,甚至存在致命问题。
毫无疑问,自然界的诸多奥秘都深深地隐藏在微观世界中。要破解大自然的深层奥秘,微观世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因为宏观自然现象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微观物理过程中。
我当然知道,现今微观领域的研究已经是理论高大上,仪器高精尖,门槛极高,高不可攀。非普通人所能染指。何况由于个人经历的限制,我对数学工具的掌握使用完全无能为力,故对物理学、化学一直心存敬畏,不敢问津。然而,直觉告诉我,必定存在能够解释复杂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理论,只是人们还没有找到而已。我何不顺着自己的思路,去做一下尝试呢。
后来看到一本加拿大人马克·麦卡琴写的《终极理论》一书,其中披露了现今物理学中存在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谬问题,才鼓起勇气到微观世界中去探头探脑。
真正深入进去也发现,这些微观领域里的高精尖理论远非那么完美无缺,令人只有敬仰的份儿。即使一个普通人也能看出其中不乏罅漏。
摸索数年,自觉获益颇多。也收获了一些新认识,新观点。由于视角不同,路径选择不同,得到了一些不同于教科书的结果,看到了一幅全新的物理图景。因此就有了这样一部探讨微观世界奥秘的著述。
实际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条,不同的道路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主流科学只是选择了其中之一而已。
自从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取得巨大成功以来,“定量描述才是科学”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数学描述成了物理学追求的首要目标,被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物理学研究唯数学的马头是瞻,对自然真相的探究都被一些高度抽象的方程式垄断了,物理机制研究反倒退居从属的地位。
物理学研究仿佛就是“一切为了计算”。非数学,不物理。一切有关物理问题的研究,如果不用数学语言加以定量描述都是不被接受的。数学俨然成了人们寻求物理真理的唯一源泉。把物理学研究变成了“透过数学看本质”而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使人们忽视对现象本身的深入分析,转而在数学描述上下功夫,使许多本可以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分析而得出的正确认识无从形成。致使物理学研究中数学描述有余而机理探讨不足。如此本末倒置的结果就导致了物理学的畸形发展。在基本事实、基本原理尚未厘清,基本方向尚不明确,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就急于追求定量描述,往往会使其物理本质得不到正确反映。也导致了对物理学研究的战略性评估的缺位。比如,当人们对加速器中粒子对撞产生的大量碎片运用标准模型进行了定量描述时,就妨碍了判定这些撞击物其实都是粒子碎片而不是粒子的正确认识的建立。
有所专精就往往有所偏废。把抽象的数学概念当成物理真实,把工具和手段当成目的。本应该是“机理为王”的物理学却变成了“数学为王”的“数理学”。本应该“向大自然要真理”却变成了“向数学要真理”。
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路径吗?其实未必。甚至也不是最佳的方式。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能够深刻揭示自然真理的科学研究方法才是正确的可取的方法。科学研究应该不拘一格,广开言路。
数学只是一种描述工具,由于数学本身的不确定性,既可以为正确理论提供描述工具,也可以为错误理论提供华丽的包装。数学公式究竟是反映了真理还是谬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使用。用对了就反映真理,用错了就反映谬误。在现实中,不顾及事物自身的特性,随意地、不适当地使用数学工具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在广义相对论中,采用黎曼几何作为研究引力的数学工具,然而几何学只适合描述宏观物体的形状,不适合描述微观粒子的作用机制。而万有引力明显属于微观粒子的作用,不属于宏观物体的几何问题。所以用黎曼几何来描述引力是用错了工具,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就像用一把尺子去测量一个物体的温度,是不明事理的蛮干。而爱因斯坦对此并无知觉。(这说明,科学研究也需要明白人。)
由于黎曼几何是一个高难的数学工具,世人在这样的难比天书的知识盲点面前只能噤若寒蝉,将其奉若神明。用错了工具的爱因斯坦又依据这种错误工具将引力解读为“时空弯曲”,从而使引力本质的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误入迷途。
唯数学化这种人为编织出来的藩篱,把人们圈在了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跳不出这样的藩篱,就发现不了大自然的深层奥秘。人类不可自废武功,对那些暂时无法用数学语言描述的复杂自然现象,允许先以语言描述、逻辑推导突破。
科学研究犹如攻克堡垒,什么武器得心应手就使用什么武器,唯数学化倾向却规定人们只能使用一种武器,使物理学研究成了单腿走路的瘸子。
数学符号与现实世界中的微观粒子或宏观事物并无直接的对应性,因此数学公式并不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机理。即便获得了经过实验验证的数学公式,物理机制仍然需要人为猜测、推导。比如我们可以利用数学运算精确地计算某个物体以某个固定的速度在某个时间内移动了多少距离,但我们并不能根据这个计算判断出是什么动力推动了这个物体,要想知道是什么动力推动了这个物体,必须借助观察或分析推理,舍此无二。
所以即便有了方程,能定量计算,也未必能揭示事物本质。数学方程中的字母或符号究竟代表了什么,是完全不确定的,本身没有明确的物理含义,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同一个字母或符号,在此方程中代表的是此事物,在另一个方程中代表的就是另一种事物。这与周易用8个或64个卦象来指代事物没有什么两样。
在数学方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物理学是“非本质物理学”,这样的物理学中的许多理论也都是近似理论。如著名的固体导电理论“能带理论”就是一种近似理论。而要揭示事物本质,就必须采用非数学的逻辑思考。
其实一切物理、化学理论都不过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物质结构、运动、变化状态等现象的某种理解。而一切物理问题都要从数学这架独木桥上通过,也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一种立场。
唯数学化的研究方式总是试图先推导出数学公式,再根据数学公式去猜度物理机制。由于对现象本身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工作没做扎实,常常导致对实验事实或自然现象做出错误解读。
唯数学化倾向不是从自然现实出发而是从数学模型出发,试图让自然真实从属于数学模型。而且只关注实验现象,却对许多难以用实验模拟的自然现象视而不见。以致现有的物理学还缺乏对复杂自然现象物理机制的领悟、理解。虽然描述微观世界的物理学已经抽象、复杂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但对许多自然界的复杂物理现象的认识却未入其门。未能把握住自然界那些根本性的东西,不能合理解释诸如雷电的起因、狂风暴雨、冰雹、火山、地震、海啸等等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更不能解释雨土、雨沙、雨石、雨(下)各种动物这些奇异自然现象。元素起源理论不能解释矿物的产状,地学理论的苍白更是惨不忍睹。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物理学研究之路再这样走下去,一万年也破解不了这些自然奥秘。
畸形的研究方式,导致了大量碎片化的非系统性理论出现,不能对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系统性、逻辑性的深度分析,而深度分析对发现和认识事物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极端的数学化也使科学家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构造、求解数学方程,而没有用于思考物质、能量运行的机理、机制。导致现今的物理学基本上是从数学角度看世界的,数学以外的领域或数学尚未覆盖的领域几乎是看不到的,是空白区。但可能恰恰在这些空白区中隐藏了大自然的重大奥秘。
有些物理问题虽然数学描述是精确的,机理猜测却是错误的。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展示给人们的仍是一幅模糊的、懵懂的物理图像。无论是宏观世界、微观世界还是宇观世界,真正能够说得清、讲得明的事物,没有几件。比如人类对电磁学的研究应用已经得心应手、登峰造极,但对于发电、导电的原理等仍然说不清道不明:诸如发电机发电究竟有没有电荷产生?导体中的电流究竟是外来电荷还是自带电荷?等等。浑浑噩噩,语焉不详,如读天书。以致到了后来的量子力学、相对论,已经不可理解、无法讲说了。科学真的如此怪异吗?或许这并非科学的本来面目,只是人们构建的科学理论走了形、变了样而已。
许多极端复杂的事物,是极难求得数学模型的,因为数学模型并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适于用数学工具描述的自然现象可能只占一小部分,数学描述并不具有普适性。比如数学尚不能解决三体问题,那么是不是世界上就不存在三体运动了呢?显然不是。必须正视数学的这种局限性。数学不是一切。对复杂自然现象只要通过逻辑推导,率先弄清了物理机制,即使数学描述缺位,同样可以解决问题。
许多物理问题和自然现象是不可数学化的。比如元素起源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数学公式存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现它,只要找到这样的数学公式,元素起源问题就不解自破,这是不可能的。要解决元素起源问题只有通过理性分析、推导,才有可能阐明它的物理、化学机制。
物理学研究采用数学描述是必要的,但把数学描述绝对化、极端化,数学至上,排斥一切非数学描述的讨论,则是狭隘的、偏激的,有害的,是典型的作茧自缚,自断言路,搞“闭关锁国”,严重阻碍、延误物理学的发展。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学人意识到了这种倾向所产生的严重弊端。
物理物理,求物之理。不求其理,言何物理?物理学应该是“机理物理学”,应该把探求机理放在首位。物理机制应该是第一性的,数学描述应该是第二性的。物理机制是主干,数学工具是从属。
有人说:“物理学只有找到了物理现象背后内在的物质作用机理,才算真正揭示出了物理现象的内在本质。”(黄德民语)
物理学要摆脱停滞不前的局面,必须开拓一条新的研究之路,必须建立一门新的“分析物理学”或“逻辑物理学”,即通过对事物全部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分析以推求其机理为主的物理学,才有可能揭示这些复杂自然现象的本质。
物理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以物理机制为本”的本位上来。研究方法应该回归到以逻辑分析为主,数学推导为辅的本位上来。数学推导应该从属于逻辑分析,为逻辑分析服务,而不是凌驾于逻辑分析之上。
本书以及《探索自然之谜》三部曲就是对复杂自然现象作出逻辑解读的一种尝试。
实践表明,唯数学化的研究方式尤其不适用于复杂自然现象。如果不改弦更张,就永无可能揭示大自然深层的奥秘。如地震、火山成因,台风、龙卷风成因,乃至普通的风暴、降雨、降雪、雷电的成因,天雨土、雨沙、雨石、雨各种动植物……的成因;山的起源,湖海的起源,沙漠起源,土壤起源,空气起源,天体起源,恒星能源等等,以及所谓神秘现象,“超自然现象”等等,现有的科学研究模式“数学建模 实验”是基本无效的。既不可能建立一个复杂得无与伦比,包含大量参数的模型,也难以做出规模巨大又极端复杂的科学实验。而要想认识一种自然现象,首先应当充分、全面地搜集、了解、掌握各种现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现象,并通过对这些现象进行归纳、演绎、分析、推理,把这些现象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充分地“吃透”,对它有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深入的了解,抓住主要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推演出现象的物理机制,然后再去寻找描述这种物理机制的数学工具,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事半而功倍。
同时,也要对人类已经掌握的相关的科学知识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掌握,这是破译自然奥秘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本书运用这种以分析推理为主的新的研究方式,对微观世界的一些重要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推导,成功地建立起了物体导电的大统一理论,探讨了常温超导材料的制造方法;追溯了引力之源,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基本作用力的大统一。虽然这样的逻辑推理,可能并不全然合于科学研究的规范,但它仍然是走向基本作用力大统一的必由之路。并尝试对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做出回答。可见这样的探索,岂徒然哉!
大自然崇尚简单,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简单的原理,未必不能揭示大自然最深刻的真理。自然界的法则都是极简法则。象则甚繁,理则甚简。真正的物理学应该是能用大白话说得清道得明,人人都能看得懂的。
科学将向何处去?科学需不需要向更高的层级发展、跃升?是循规蹈矩、抱残守缺、裹足不前,循着目前的正统的、规范的科学范式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地继续走下去,还是师法自然、发扬蹈厉、革故鼎新、涅槃重生,深究自然现象的本质面目,在未被破解的自然奥秘中寻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进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科技新境界呢?这就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抉择。